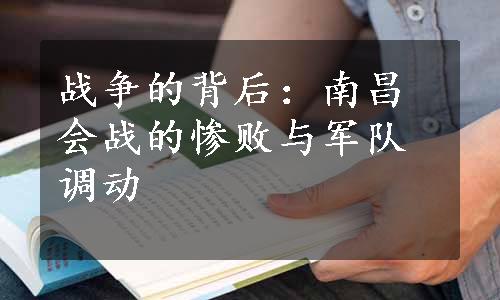
南昌会战,仅仅10天便以惨败收场,损兵失地,举国哗然。
重庆,蒋介石大为震怒。战争时期,如无严明的军纪和士气,如何守土、谁来保国?军事作战会议后,首先被拿来开刀的是原东北军49军。军长刘多荃由中将降为上校留任,开国军上校军长之先例,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调离原职,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整治之惨,甚至带有几分羞辱的味道。
说句公道话,49军虽然打了败仗,但应负首要责任的并不是他们。在19集团军同时参战的5个军中,阵地首先被突破的是79军的76师。当时,日军万炮齐轰,炮弹中又夹杂着大量的烟雾弹与毒气弹,一时间天昏地暗、地动山摇,我军官兵好似陷入了地狱一般,炸伤、中毒者不计其数,部队很快丧失了战斗力。蓄势待发的日军立刻渡河攻击,我军防线当即崩溃。而左翼的49军仅为拥有两师的乙种军,其中仅有105师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并且武汉大战之后元气还未恢复,以如此疲弱之师怎能挽救整个战线的崩溃?
刘多荃自然万分委屈,暗自感叹命运不济。想他在东北军时是何等的风光,做张少帅的卫队团长,亲身参与诱杀杨宇霆、常荫槐的行动。后晋升105师师长,全师装备、训练、官兵素质均为东北军之冠。1936年“西安事变”,他正是捉蒋行动的总指挥。没想到,这最后一次风光却给他埋下了无尽的祸根。
张少帅被软禁,纵横中国数十年的东北军刹那间灰飞烟灭。军队被整编的整编,移防的移防,换血的换血,几番下来,东北军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
而刘多荃一介武夫,在东北军失去主心骨后,一错再错。尤其是其至交王以哲被东北军少壮派暗杀后,他一味复仇,先是将促成张学良与中共联合的高福源旅长秘密枪杀,后又把枪杀王以哲的连长于文俊剖腹挖心给王祭灵,同时还扣押了许多左翼军官。此举既扩大了东北军的分裂,也招致东北军上下对他的怨恨。1937年4月29日,一个卫兵趁他洗脸时突然拔枪行刺,被他妻子发现,卫士被其妻拦腰抱住,他才逃过一劫。
毫无疑问,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此后,众叛亲离的他只得向蒋介石靠拢,积极配合蒋介石实施对东北军的编遣方案。蒋介石开始时也很够意思,任命他为49军军长,下辖105、109两师。哪知道这不过是欲擒故纵的计策而已。恩归恩,怨归怨,可惜的是,他不了解蒋介石睚眦必报的个性。领袖熟知陆、王心学,服膺的是曾、胡诸公,专会在“忍耐”二字上下功夫。西安被囚是蒋介石一生的奇耻大辱,刘多荃是祸首之一,他怎会忘记?只不过内忧外患,正是用人之际,蒋介石暂时放过了他。
淞沪恶战之后,刘部伤亡惨重,其109师几乎伤亡殆尽,急需休整和补充。刘多荃和109师师长赶去武汉上下活动,走了不少门路,花了不少钱,总算调来全部徒手的预5师进行补充。补充归补充,但事情还留了个尾巴:预5师团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虽然很不乐意,但是没有办法。之后,刘多荃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张学良当年遗留的一批武器搞到手。至此,109师补充完毕,全师满员,面貌一新。每连6挺捷克式轻机枪,营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连,真是脱胎换骨一般,羡煞了周围的许多兄弟部队,心说:“刘芳渡(刘多荃,字芳渡)真他娘的命好,他啥时候拜老蒋做了干爹啊!”
刘多荃当时也是志得意满,对蒋介石是心存感激,“都说老蒋心狠手辣,有仇必报,惯于排除异己,现在看来也不尽然”。心里时时盘算着如何效忠领袖,战场建功。
很快,他就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1938年年初,第109师奉调徐州前线,可4个团长全部告假,部队无法开拔。蒋介石得报后,不仅不处理那几个违令不遵的团长,反而把师长赵毅撤了,改任中央军的李树德为师长,接着大批原东北军军官被撤换。不久,109师又被调往开封,划归第一战区刘峙的指挥序列。第49军被肢解,只剩下一个残缺的105师。
刘多荃又急又气,忙活几个月花光了家底,原来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老蒋这做法也太卑劣了吧!无奈东北军势力已经瓦解,新的靠山也无处寻觅。他第一次体味到丧家之犬的无奈和悲哀。
更没想到今天,蒋介石竟又拿他泄愤。军衔由中将降为上校是当众打他的脸,整高鹏云、王铁汉等原东北军将领是断其臂膀。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蒋介石的手段刘多荃算是彻底领教了。失望之余,刘多荃在日后的政治倾向上便与国民党渐行渐远。直到1949年8月,在香港联合黄绍竑等通电反蒋,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投入到新中国的怀抱中。
当然,这是后话。
重庆,蒋介石内心的苦闷、焦虑并不因处置了刘多荃而有多少缓解,借抗战剪除异己不过是既定政策的一环而已。可他心里明白,各路诸侯保存实力,临敌避战,照这样败下去,长沙不保,宜昌危险,士气、民心必受重创,重庆最终也将无法成为他的栖身之所!
更令他气馁的是,大的战略形势并未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他在4月2日的日记中哀怨甚至愤恨地写道:“倭寇不欲参加欧洲战局,亦不敢与俄国开衅,计在妥协列强专事侵略我国,乃其最毒之政策。”
心绪烦乱,蒋介石离开屋子,步出了林园。
落日的余晖洒满整个山头,向阳的山林现出一片浑黄的亮色,背阳的山坡则已暗沉下来。蒋介石身着披风,缓步行走在山间小道上。他没让卫士们跟来,身边随行的只有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侍从副官远远地跟着,几十名卫士立于远处,警戒外围。
冷风微起,松枝轻轻摇动。脚下的松针腐植日久年深,累积很厚,踩上去有些柔软。松涛林海,幽径绵延,在傍晚的余晖下,显得十分深远。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
蒋介石随口轻吟晋人左思的诗句,转向陈布雷:“彦及(陈布雷,字彦及),山城这夕照晚景如何?”
相处10余年,陈布雷太了解蒋介石了。当下正是蒋内心纠结无以排遣的时候,断无闲心谈风月胜景。借景言事,他知道当下最让蒋介石揪心的恐怕就是汪精卫和日本人。
“晚景甚好,怕是有些丧家之犬已受用不到这些了。”细声细语之中有几分尖刻,一反陈布雷谨言慎行的常态。他刚刚得到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的报告,汪兆铭自3月21日遭遇暗杀而侥幸逃过一劫后,已彻底放弃流亡法国的打算,就要赶赴上海与日本人合流了。
陈布雷揣知这才是蒋介石当下最关心的事,他深知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叛逃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汪精卫一向以孙总理的正统接班人自居,在声望、才情、风度上都超他蒋介石一筹,在政务、党务上也能与蒋介石抗衡。有他在,蒋介石时时感到芒刺在背,手脚不得自由施展,尤其令蒋不能容忍的是每次倒蒋行动他几乎都是主角。“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拿这句话来形容蒋汪关系怕是再合适不过了。如今,汪精卫即将沦为汉奸,蒋介石痛心之余,反倒也有几分释怀。一个身败名裂的汉奸哪还有什么资本再来和他争锋?
害怕的是,日本人如果不负前言,真的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汪精卫一旦得志,张发奎等地方诸侯必定会相率倒戈,叛他而去。到那时,树倒猢狲散,他就无力回天了。不过,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器小易盈,贪婪无厌,是一个无法产生伟大战略家的民族,他们还没有魄力做出真正的让步,以实现其扶汪倒蒋、肢解中国的策略。
关于这些,他正要问策于陈布雷,没想到陈布雷却先他说起了。
“汪兆铭背叛总理,背叛革命,背叛党国,自甘堕落。当年他刺杀清人时,举国若狂,将他捧作英雄,那时他何其得意。看他今日所为,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人世!”
蒋介石给过汪精卫机会,劝其回来,不愿回来甚至出国留洋也行,可汪精卫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靠日本人。每想到此,蒋介石的心中便忿忿然。
“汪兆铭诚然不齿于民族,不过任他扑腾,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花。张发奎他们首鼠两端,事未见机,眼前如果没有切实的好处,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陈布雷知道蒋介石最看重的就是枪杆子。
说话间,两人步入一座石亭。坐下后,蒋介石说道:“张向华(张发奎,字向华)他们倒也不足为虑。只是日本人的底牌还无法摸清,彦及怎么看?”
陈布雷扬起干瘦的脸,缓缓说道:“今年又是个好年景。据云、贵、川、湘诸省的报告,风调雨顺,人心稳定,支撑明、后两年的抗战是没有问题的。而日本方面,据戴雨农(戴笠,字雨农)他们的情报,其工业生产力已使用到最大潜力,战争能力正在下降。中日对比,日本的底气已经不足,而我愈战愈勇,士气不衰。如国际形势一有变化,转机就会到来。”
蒋介石似乎另有所思,轻声问道:“和谈呢?”
事实上,他正要派出军统特务曾广冒名宋子良和日方接触。宋子良是宋子文的亲弟,日本方面一定会感兴趣的。
陈布雷略略思考后答道:“日本方面底气不足,借和谈摸摸他们的底也好。军部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今井武夫好像对和谈很有意思。”
日本军部的少壮派认可的是手握实权的蒋介石,作为军人他们更为相信实力,很多人甚至对汪精卫不屑一顾,就是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高层对此也颇有微词。日本的舆论也不看好他,纷纷说他无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曾表示:“汪精卫不足以把握支那(中国)四亿民心,此时组织中央政府甚为危险。”日本评论家吉冈文六在《日本评论》上说:“汪精卫是一条伸缩多变的蚯蚓。”“汪的性格实在柔弱,他的声音好像猫一样的柔嫩,写的字像女人的字。”
看来做汉奸不但要招致本国国民的唾骂,连日本主子都会瞧不起。想起在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劝说无效后,自己又前赴河内劝汪回心转意,汪竟一口回绝,陈布雷真是感慨万千。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有如此英雄气概的人怎么会一夜间变为汉奸呢!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www.zuozong.com)
两人一时无语。此刻,正是晚霞最为浓重的时候,远处的山头被染成了绛红色,归林的鸟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此刻却渐渐安静了下来。陈布雷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口说道:“据说,日本人正在运动北洋遗老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吴子玉(吴佩孚,字子玉)等人。”
“哦……”蒋介石欠了欠身子,表现出了兴致。
“拿徐菊人来说,日本人看中他的声望,找了两个满族人来敦请他出山。没想到一言不合,徐菊人竟和他们对骂了起来。”陈布雷出身报界,向来对晚清、北洋的这些人物有所关注,因而说起他们来头头是道。
徐世昌,本是北洋系的客卿,历任尚书、总督、军机大臣、国务卿、大总统等晚清和民国的重要职务,为人圆滑,八面玲珑,门生故吏遍天下,声望甚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如此经历的恐怕只此一人。日本人正是看中了他的资望,拼命拉拢,请他出山。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派出徐的老友曹汝霖见他,说:“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来压制日本,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和中国打仗。总统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即可撤兵。”
徐世昌以年老婉拒。曹走后,徐世昌告诉门房:“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此后,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以徐世昌的亲侄徐一达与其秘书长柯昌泗是儿女亲家,便托柯由徐一达转告徐世昌,称:“日本军方的意思,请徐世昌担任华北的领袖。如徐允出山,即以北京市长给一达。”
徐一达听后当即谢绝。
无奈做了汉奸的人,脸皮就是厚,潘毓桂仍是一再催促徐一达。被逼无奈,徐一达索性将前后经过都告诉了徐世昌,徐世昌嘱咐他躲开一阵,徐一达因此逃往上海。
次年,武汉会战前后,日本军方为了实现其由军事到政略的转变,急需扶植一批汉奸政权,他们又想到了徐世昌。
先是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约徐世昌见面,徐托病未见。
继而,徐世昌的两个满族门生金梁和章梫见徐,金梁说:“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要来拜见老师,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俟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徐世昌还是以年老体衰、不堪任事为由,全力推辞。
金梁见徐世昌不为所动,便露出了小人嘴脸,威胁道:“我们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老师的晚盖,人人都有个晚盖,还请老师有以自见。”(“晚盖”一词出自《国语》,意思是早年作恶后来能够掩盖弥补。)
没想到金梁小人得志,竟然出言不逊,指责徐世昌背叛清朝、服侍民国。徐世昌听后,哪受得了这个,愤然斥责:“你太浑。”
金梁索性撕下脸面,反唇相讥道:“老师才浑哩!”
徐世昌听后,潸然泪下,叹道:“想不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一场。”说罢,拂袖上楼。金、章两人自讨无趣,也不辞而别。
撇开徐世昌的历史功过不说,为了保持气节,80多岁了还能如此忍辱负重,实是难能可贵。
同时,日本人还拉拢过曹锟、吴佩孚、靳云鹏、袁克定等人,但都被一口回绝了。尤其是洪宪朝的“太子”袁克定,由于拒绝和日本人合作,在出入北平城门时,曾多次受到搜身的侮辱。
当时,袁克定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穷困潦倒时,单靠一个忠于他的老仆人,到街上捡白菜帮子,蒸窝窝头充饥。每次老仆人端上饭菜,他仍不改故态,戴好餐巾,用西洋刀叉把窝窝头切成片,就着咸菜进餐。
华北沦陷后,土肥原贤二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影响。袁克定那时候生活已经很艰难了,但在民族大义面前,说再穷也不能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听了陈布雷关于徐世昌、袁克定等人的讲诉,蒋介石面色凝重地说:“北洋诸老真是可敬,长我中华志气,比汪兆铭之流不知强上多少倍。”
说话间,薄暮已从四面围了上来,寒意渐生。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已是昂然走近,来人正是刚刚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的林蔚中将。
“是蔚文(林蔚,字蔚文)啊!我正要回去,咱们边走边说吧!”
林蔚和陈布雷一样,是蒋介石内廷的左膀右臂,蒋介石对他们信任之重,一时无二。当时,除了宋美龄和两位侍从副官外,能够直接进入蒋介石内室的也只有他二人而已,即便是蒋经国、蒋纬国兄弟有何请托,也经常找“林叔”“陈叔”代为帮忙传话,可算得上真正的帷幄近臣。
林蔚虽受倚重,但却能谨言慎行。在蒋介石面前,他表现得精明强干,任劳任怨,从不揽权结党,搞个人圈子,同时又工于心计,对蒋介石的重要意图常能预为窥测,所以遇机一拍即合,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在众人面前,他态度温和,喜怒不形于色,显得深沉平和,不但与胡宗南、汤恩伯等浙江籍统兵大将关系融洽,同时又能取信于陈诚,正所谓八面玲珑,滴水不漏。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统治体系内,一个人能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他凭借做幕僚的丰富经验,不仅工于谋人,而且善于谋己,懂得见风使舵,预留退路,常能左右逢源。人们常说,蒋介石精于权术,无人可及,事实上林蔚和他相比,并不逊色。
一个月前,因长沙大火一案丢了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回到重庆,蒋介石便有了个一石二鸟的安排:林蔚调任军令部次长兼桂林行营参谋长,腾出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之职由张治中接任。
此次蒋介石调林蔚做桂林行营的参谋长,明眼人都知道有监视白崇禧的意思。桂林行营设立于1938年11月的南岳军事会议,由白崇禧任主任,统辖第三(顾祝同)、第四(张发奎)、第七(余汉谋)、第九(薛岳)战区,以拱卫重庆,保卫大西南。桂林行营配置了国民党军的大部分精华,时间一长,如果被白崇禧瓦解控制,那还了得!况且他也了解白崇禧的性格,一向是敢作敢为,让人十分忌惮。眼下只有调去他最为信赖的干将,蒋介石的心里才踏实些。
今晚匆匆过来,林蔚正是辞行的。
蒋介石打量着林蔚,穿戴整洁,精神饱满,根本没有50岁人的老态,不由得面露悦色。漫步间蒋介石问道:“蔚文,准备得怎么样了?”
“已经和白主任、陈部长及各战区长官疏通过了。陈部长、顾长官、薛长官都很理解委座的安排。桂林行营那边大小官佐,我当尽力笼络,晓谕领袖之意图。”
虽然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薛岳等人并没有林蔚资历深、资格老,但是林蔚还是恭敬地称他们为主任、部长、长官,显然是早已体察到蒋介石不愿近臣官阶过重难以驾驭的用心。侍从室的参谋,调入时为上校中校的,必定要降一两个军阶使用。这种办法正是从明太祖那里学来的。明太祖设内阁学士,虽参与枢密,职权很重,但是只授四五品的官阶,使用起来在心里可不把他们看作大臣,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可省去许多心理上的障碍。林蔚深知此道,因而处处小心,不敢稍有差池。
蒋介石对林蔚的回答很是满意,却担心林蔚能否协调好与地方势力的关系。福建、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广西的白崇禧、黄旭初,云南的龙云,湖南的薛岳,盘根错节,纷繁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林蔚虽然心思缜密,经验丰富,毕竟这样大的局面还是第一次经历。因而,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道:“蔚文,须知桂林那边水也不浅哟。”
“委座放心。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张向华他们即便心生异志,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他们各有所图,部下又有地域之争,很难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所谓逼之则吴越同舟,缓之则自相夷戮。只要中央操之不急,自然有水到渠成的时候。”
蒋介石听后,宽慰很多。心说林蔚的识度、能力确实不凡,却又能淡泊名利,甘为人下,真是难得。于是欣然说道:“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说完,回过头对陈布雷说:“彦及,回去啦,今晚一起为蔚文送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