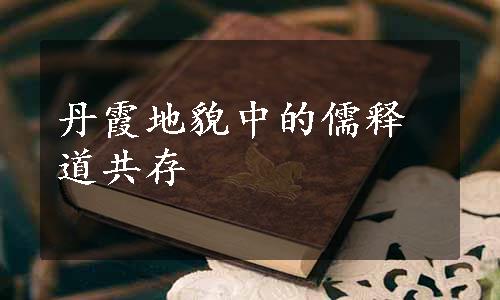
农耕文明下,中国人把诗和远方寄托在了山水间。道教在山水间寻洞天福地悟道修仙,佛教在山水间结庐参禅,儒家也在山水间旷达淬炼仁与智。尤其是在丹霞地貌上,三家都能寄宿其上长久流传。公认的几个道教发源地及道教名山,江西龙虎山、四川青城山、安徽齐云山、甘肃崆峒山、福建武夷山等均为丹霞地貌。千丘万壑,峰岩嶂叠的地方最符合道教崇尚隐逸、避世修行的需求。碧水环绕中忽而拔地而起丹霞峰林的景象,符合道家对仙境的印象。丹霞山岩的密度、硬度适于进行石刻造像,佛教利用它塑造了不少石雕大佛。南宋时期,书院建设兴起,喜在山水中传道授业解惑的儒家,也全都选址于丹山碧水地。
在武夷山这个三教并立的丹霞山岩碧水流转之地,儒释道各自以此为道场修炼参佛讲学。而另一个令三教有共同语言可谈的便是茶了。作为一种可令人思绪通达的饮品,茶被三教的先贤们饮用,且赋以它丰富深沉的诠释和表达。甚至其数量和质量都可谓所有茶类之最,武夷茶因此才有那么多人文掌故,才有了美和哲的丰富延伸。
武夷山是道教推崇的洞天福地之一。道教将天分成三十六层,并在人间找到了相连空间,即为三十六洞天福地,也是可修道升天之地。这些地方多是人迹罕至、景色秀丽之地,武夷山便在其中,被归为第十六洞天。吕洞宾游武夷山时写到:“武夷山,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种茶。”武夷道人中,南宗五世祖白玉蟾留下的大量诗文里,随处可见其生活场景中经意或不经意扫过茶的“镜头”。“钝置诗盟酒约,只自焚香吃茶”,“淡酒三杯,浓茶一碗,静处乾坤大”,“饮到如泥卧石鼓,醒来瀹茗自闲适”。除了诗文,这位嗜茶道人还留下了被后世珍视的茶品种,据传四大名丛之一的白鸡冠便是白玉蟾在止止庵道观培育的。
重重山岩围出的鬼洞,被认为是武夷山茶的天然基因库
明清时期,武夷山制茶的主力是寺僧,有“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茶出于僧制者价倍于道远”的说法。最核心的岩茶山场都在寺院周围,慧苑坑、大坑口、九龙窠、天心岩、牛栏坑,这些今天被认为最为核心的正岩产区的茶过去都是寺庙出产。四大名丛铁罗汉、水金龟、白鸡冠、大红袍,每个茶都有些奇闻故事,这些故事又都无一不直接或间接与寺庙关联。武夷山僧人制茶事茶还有明确的分工,有种茶僧、植茶僧,有专司管理的茶头,还有专门给香客、施主、游人施茶的施茶僧。盗走武夷山茶的英国植物学家福琼(Robert Fortune)甚至认为武夷僧人重茶事多过佛事,他在游记中写道:“实际上,这儿的和尚们看上去更关心种植茶树和加工茶叶,而不是他们的佛事。我注意到,寺庙前面到处都搭着一些竹架子,架子上放着筛子,这些筛子全都是用来晾晒茶叶的。”(www.zuozong.com)
儒家惯以山水为寄托,与道佛相互影响作用后,儒士开始将书院建在山水间,南宋时期,这种状况在江西、浙江、福建、湖南这些广布丹霞地貌的地区达到了高潮。武夷山晚对峰有一处摩崖石刻,上书“道南理窟”,用来概括理学在武夷山所结出的累累果实。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年少便在武夷生活,钟灵毓秀的武夷影响着他。隐屏峰下九曲溪之五曲处有块丹岩大石,上书“茶灶”。据说朱熹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围炉于此,以九曲溪水烹煮武夷茶。朱熹诗云“客来莫嫌茶当酒,山居偏与竹为林”成了涉茶诗句中被传颂最广的,以茶待客之道从文人士大夫传到了民间,成为民间一种普遍的朴风良俗。朱熹还亲自栽茶做茶,在书院“武夷精舍”周围曾植有茶圃两处,种茶树百余株。“携蔬北岭西,采撷供茗饮”的诗句描述了他种茶采茶,享耕读之乐。
三十六峰、九十九岩
“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素以三十六峰、九十九岩闻名。武夷山的岩体是由色砂砾岩组成的低山丘陵,山间岩体千姿百态。据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记载:九曲溪沿岸有28座,山北有8座,共36座,如三仰峰、天游峰等。池宗宪在《武夷茶》中详细记录了九十九岩的名称,如位于二曲溪南的虎啸岩、七曲溪北的老君岩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