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然顿月杰的宗教态度是兼容其他教派的,为何却获得了“崇信苯教,仇视一切佛教”的名声呢?这与在1640年固始汗进攻康区过程中,顿月杰对“萨迦、格鲁、噶玛、竹巴、达隆巴等派僧俗领袖”进行监禁有关。对此事件,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记:
庚辰年(1640)十一月二十五日,白利土司及其属下虽已逃至边远稳固之处,但福威强大之铁钩,如磁石吸铁,仍将其全部勾回,交法庭制裁。从此诸种不得安宁之祸根则消除罄尽。凡昔日萨迦、格鲁、噶玛、竹巴、达隆巴等派僧俗领袖限于囹圄者,皆尽出,各送还本土。[19]
那么,顿月杰从兼容和尊崇藏传佛教各教派,到固始汗进攻康区过程中拘禁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其宗教态度的这一骤然改变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是宗教原因还是政治原因?是顿月杰个人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变化,还是政治局势使然?这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从藏文史籍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窥见发生此事的脉络。《五世达赖喇嘛传》记:
早在木鼠年(1624)除夕,在举行施食法事时,从噶尔巴的辖区送来了到拉萨的人,并声称如果甘丹颇章不能保证蒙古人不向康区进兵,那么,我们不让他们到上部来,这次是看尚敦噶巴的情面才放行的。[20]
“噶尔巴的辖区”,系指白利土司控制区。[21]文中所言“如果甘丹颇章不能保证蒙古人不向康区进兵,那么,我们不让他们到上部来”,是顿月杰带给甘丹颇章即格鲁派上层的一个传话。需要注意的是,传话的时间是1624年。其时,占据青海的是蒙古土默特部,由于土默特部与格鲁派关系甚密,故顿月杰特向甘丹颇章提出此要求。可见,早在1624年顿月杰就曾以阻断康区通往卫藏的道路为条件,要求格鲁派“保证蒙古人不向康区进兵”。
从16世纪起,因明朝国力衰退,蒙古部落开始入据青海。1578年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晤,揭开了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向蒙古地区大规模传播的序幕,也为蒙、藏之间基于宗教信仰的政治结盟开启了大门。明后期青海蒙古对康区的影响日益加大。[22]俺答汗时期其势力曾向康区渗透,《明实录》记:“俺答子宾兔住牧西海,役属作儿革、白利等诸番。”[23]宾兔为俺答汗之子,是土默特部在青海的实际统领者。可见,白利早期曾受蒙古土默特部役属。明末清初,白利土司常与蒙古人作战,并且难分胜负。《四世康珠活佛的传记》曾这样描述白利土司的状态:“由于十分凶猛残暴,这些军队间发生许多战事,霍尔、林、琼部、色嚓等许多部落发生动乱,从中得到许多的土地。”[24]正因为白利土司是在蒙古势力的夹缝中逐渐兴起,当其占据了中部康区大片区域后,如何防范青海蒙古即成为其最大的忧患。这正是顿月杰传话给格鲁派,要求其“保证蒙古人不向康区进兵”的背景。
格鲁派可能未把白利土司的传话当一回事,同时也没有材料显示1624年以后蒙古土默特部发生过向康区进兵的情况。但1632年,出现了一个使青海局势发生根本改变的事件——由却图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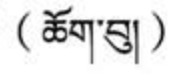 率领的另一支蒙古部落南下青海,击败土默特部,控制了青海蒙藏各部落。却图汗袭据青海,使土默特部落四散逃走,其中一些部落逃入白利土司辖地。《安多政教史》记:“土默特是蒙古喀尔喀部
率领的另一支蒙古部落南下青海,击败土默特部,控制了青海蒙藏各部落。却图汗袭据青海,使土默特部落四散逃走,其中一些部落逃入白利土司辖地。《安多政教史》记:“土默特是蒙古喀尔喀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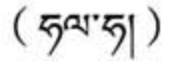 一支,起初居住在青海湖边,却图汗来到湖边时,他们逃至丹科
一支,起初居住在青海湖边,却图汗来到湖边时,他们逃至丹科 地区。”[25]丹科即邓柯,邓柯一带时为白利土司所控制。这些进入白利土司顿月杰辖区的土默特余部可能给当地带来一些侵扰和破坏,并可能同白利军队发生过一些接触和交战。
地区。”[25]丹科即邓柯,邓柯一带时为白利土司所控制。这些进入白利土司顿月杰辖区的土默特余部可能给当地带来一些侵扰和破坏,并可能同白利军队发生过一些接触和交战。
或许是慑于却图汗势力的威胁以求自保和争取有利发展空间,或许是格鲁派的冷淡使顿月杰感到失望,总之,1634年白利土司顿月杰已开始同反格鲁派的却图汗结成联盟,共同阻断了康区通往卫藏的道路。
白利土司所控制的中部康区一带为打箭炉通往卫藏的咽喉要道。《五世达赖喇嘛传》记:“(1629 )由于察哈尔汗在蒙古发动战乱,北路不安全,达温达尔罕曲杰和扎尼温穷二人经汉地驿路至打箭炉,又经过中部康区来到拉萨。”[26]因此道既是汉藏的门户,又是康区乃至安多通往卫藏的一条捷径,故被藏人称作“汉藏黄金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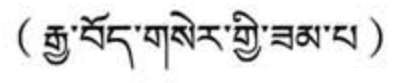 或“金字道”。《安多政教史》记:“察哈尔人、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汉藏黄金桥’,安多的一些有魄力的人们,绕道内地,经打箭炉转中康地区前去卫地。”[27]
或“金字道”。《安多政教史》记:“察哈尔人、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汉藏黄金桥’,安多的一些有魄力的人们,绕道内地,经打箭炉转中康地区前去卫地。”[27]
白利土司顿月杰与却图汗阻断“汉藏黄金桥”的时间是1634年,《五世达赖喇嘛传》记:
(1634年9月间)在此时期,察哈尔人、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黄金之桥,各个高僧和施主的成千上万的礼品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寄过来,因此(工布噶居巴的熬茶献礼起了很大的作用)。[28]
可见,该道路的阻断对格鲁派的影响甚大,使格鲁派与康区地域各施主和寺院的联系陷于中断,“成千上万的礼品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寄过来”。尽管顿月杰与反格鲁派的却图汗结盟可能主要是迫于其威胁,但其与却图汗共同阻断“汉藏黄金桥”,却标志着白利土司与格鲁派双方正式交恶。
与却图汗结盟给顿月杰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解除了却图汗“向康区进兵”的威胁,从而为其进一步扩展势力提供机会。1635年,白利土司控制了类乌齐、芒康、昌都、玉树、巴塘、理塘、中甸等大片地区,实力大增。类乌齐寺扎巴坚赞的传记中记:“猪年(1635)春天,白利迎请,见面十分愉快,此时正是白利领土范围大增之时。”[29]《教法惊奇海》记:“多康地方的忽然出现并迅速壮大的白利,权力极大,能与魔王相匹敌,将康区下部绛王(木氏土司)的领地逐渐纳入其治下,将绛王、蒙古等人赶出康区,如疯象、无疆的狮子般的六水五岗属民无人敢违抗他的法令,卫、后藏、康三地的商人路经玛康地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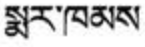 )时如进了阎王殿般小心翼翼。”[30]
)时如进了阎王殿般小心翼翼。”[30]
1636年当却图汗之子阿尔斯兰由西藏返回青海途经康区,在白利辖区大肆抢劫财物之时,白利已能凭借精兵与之对抗。[31]藏文史料载:“据说下路康区被蒙古人沿路抢劫。那时,白利因为精良的士兵未能被摧毁,却图汗之子阿尔斯兰是军队的首领,由于臣属间的不和而被杀掉。”[32]《五世达赖喇嘛传》也写道:“正当阿尔斯兰被征讨白利土司时所劫获的财物弄得昏头昏脑之时,阿尔斯兰及其随侍三人同时被杀。”[33]四世康珠活佛自传亦记,“此时,与蒙古小王阿尔斯兰的蒙古军队相遇,激战三日,杀死了阿尔斯兰弟弟图巴崩为首的主仆十一人”,蒙古军队因此返回。[34]按此记述,白利土司顿月杰的精兵同阿尔斯兰的蒙古军队发生了激烈交战,不仅将后者驱逐出康区,甚至还杀死了“阿尔斯兰弟弟图巴崩为首的主仆十一人”。这显示实力壮大后的白利土司已能在一定程度上与青海蒙古势力相抗衡。(www.zuozong.com)
不过,1637年青海局势再次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另一支蒙古势力即固始汗统领的和硕特部在格鲁派召请下,南下青海,以精兵一万击溃了却图汗的三万部众。却图汗兵败被杀。
格鲁派的同盟者固始汗和硕特部占据青海,无疑使白利土司陷入尴尬和被动处境。在此情形下,顿月杰曾试图修复和改善同格鲁派的关系。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大约在1637年,“拉萨附近的吉雪地方的格鲁派行政长官第巴吉雪巴索南群培来到绛顿,皆因固始汗欲前来参观此圣地”[35]。格鲁派第巴索南群培亲自来绛顿为固始汗参观打前站,可见此事对格鲁派关系重大。这也说明此前白利土司虽与却图汗结盟阻断“汉藏黄金桥”,但格鲁派与白利土司之间还尚未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本来这是白利土司与格鲁派改善关系的一个天赐良机,但出人意料的是,主持绛顿宗教事务的噶玛丹培未向白利土司顿月杰请示,以绛顿面积狭小、人口拥挤为由,拒绝了格鲁派第巴索南群培的要求,索南群培悻悻而回。但随后噶玛丹培就为他的拒绝感到后悔和惴惴不安,预感自己闯下大祸,他立即派出信使前往拉萨和固始汗处,企图加以挽回。[36]同时也派几位使者向顿月杰通报此事,顿月杰闻知此事勃然大怒:
他呵斥喇嘛们一直在做错事,下令鞭打使者,并剥掉了他们的衣服和鞋子。不给任何解释的机会,使者们便绕道返回。[37]
顿月杰的激烈反应,不难看到他对噶玛丹培“对新的政治与权力环境还认识不甚清楚”[38]而做出的愚蠢决定是多么痛恨。这件事导致了顿月杰与噶玛丹培关系的彻底恶化。此后,噶玛丹培虽派人携带一封信和礼物前往白利,试图消除他与施主之间的嫌隙,但无效果。他又请绛顿行政长官和顿月杰夫人从中斡旋,但二人终未达成和解。此事对噶玛丹培打击巨大。“不久喇嘛便卧床不起,或者与上述事件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藏历四月的第一天,可能是公历1637年4月25日,噶玛丹培喇嘛圆寂。”[39]
从顿月杰对待此事的极端恼怒程度可知,其显然意识到,噶玛丹培的轻率决定断送了他同格鲁派之间达成和解的最后一线希望。
我们不知道索南群培前往绛顿为固始汗参观进行接洽的准确时间,但可肯定是在噶玛丹培圆寂以前。固始汗南下青海击败却图汗的时间是“牛年正月”即1637年初[40],也就是说,固始汗提出到绛顿参观应在1637年1—4月之间。如此看来,固始汗入据青海后即提出前往绛顿参观的要求。这不排除其有前往白利土司辖地一探虚实的企图,也表明固始汗入据青海后已有觊觎康区之心。
1637年秋,固始汗率一千多人前往拉萨,与五世达赖为首的格鲁派上层进行广泛接触。固始汗与格鲁派上层的会晤,似乎主要是双方互赠封号,并提出邀请五世达赖前往蒙古地方传教。[41]但固始汗此次访问拉萨显然有更重要的意图——这就是为其入藏和进兵康区做准备。《五世达赖喇嘛传》只说双方“商议了今后的事务”,但具体为何事务却未提及,说明固始汗与格鲁派上层显然决定了更重要的事情,只因条件不成熟,双方对此讳莫如深。有学者认为固始汗此行与格鲁派上层达成了进兵康区消灭白利土司的默契[42],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大,但因为缺乏材料证据,仅是一种推测。
从后来的事件发展看,固始汗在进攻白利土司的行动上却表现得相当独立和主动。五世达赖喇嘛这样记叙了固始汗对康区的进兵:
龙年中此处应指1640年)盛传蒙古军队开到中部康区的消息。其起因是……代表团回到青海后,将其所见所闻向固始汗作了汇报,汗王闻言大怒,旋即挥兵进藏,途中折向康区进攻白利土司。[43]
从该记载看,卫藏方面是在1640年中才得到固始汗进兵康区的消息,且固始汗是“挥兵进藏,途中折向康区进攻白利土司”,这说明固始汗进兵康区时并未通知格鲁派上层,而是单独且突然采取了行动。固始汗对白利土司发起进攻是1639年5月,直到1640年11月擒获顿月杰,战事前后持续了一年半时间。[44]可见战事较激烈,并非一蹴而就。固始汗在发动对白利土司的进攻后,曾派使臣要求格鲁派“为用兵白利举行法事”,这或可视为一种正式通报,而格鲁派的回答是“我们要求彻底消灭白利土司”。[45]
其实,固始汗1637年底自拉萨返回青海,可能已开始作进兵康区的准备。因感到蒙古人进兵康区迫在眉睫,顿月杰的情绪变得愈加焦躁和暴戾。有迹象表明,1638年顿月杰已在其境内采取迫害格鲁派僧人的行动。[46]这种将蒙古人进兵康区的巨大威胁迁怒于格鲁派的暴戾情绪,在顿月杰于1639年初写给藏巴汗的信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土兔年(1639)除夕,在举行施食法会时,白利土司给藏巴汗寄去一封信,内称:“在神山上已插置神幡。由于甘丹颇章没有能保证蒙古人不进攻康区,明年我将带兵到卫藏。那座堪称觉卧仁波切的铜像是招致战争的根源,应当扔到河里去。把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破坏以后,应在其废墟上各垒一座灵塔。藏巴汗应当与我亲善起来,一同供养卫藏和康区的佛教徒和苯教信徒。”[47]
此信的时间正值固始汗进兵康区前夕。顿月杰显然已预感到蒙古人进兵康区不可避免,战事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从信中我们不难看到顿月杰恼羞成怒及其对格鲁派的极端仇恨。仇恨的原因,诚如信中所言,是“由于甘丹颇章没有能保证蒙古人不进攻康区”。值得注意是,顿月杰在信中并未仇恨一切佛教徒,而是说“藏巴汗应当与我亲善起来,一同供养卫藏和康区的佛教徒和苯教信徒”,这清楚地表明,顿月杰仇恨的主要是以五世达赖为首的甘丹颇章。这封信显然使白利土司顿月杰与格鲁派关系彻底恶化和决裂。正如五世达赖在引述此信后所言:“这个白利土司十恶不赦,他是应该进行诛灭的主要对象。”
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顿月杰仇视格鲁派并非缘于信仰,而主要是政治的原因,是“由于甘丹颇章没有能保证蒙古人不进攻康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