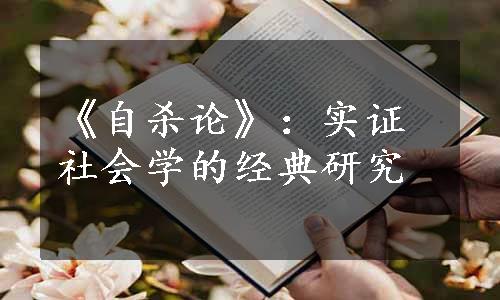
《自杀论》是社会学研究方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从它开始,社会学和哲学真正分离开来了。通过具体分析自杀现象,涂尔干展示了他提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原则的作用。
涂尔干一贯的理论兴趣是社会团结。自杀研究与社会团结的状态有关:自杀率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团结状态的变化,自杀率的上升是社会危机的一种反映。涂尔干认为,人类的幸福正在日渐减少,这从自杀数量的增长趋势上可以得到证明。在这里,涂尔干用了“平均幸福”的概念——社会普通成员享有的幸福即平均幸福或幸福的平均程度。“如果我们把所有个人因素或局部因素从个人的幸福中抽离出来,只保留某些普遍因素和共同因素,那么剩下的便是我们所说的平均幸福。”[67]。涂尔干指出,从平均幸福的演变趋势上看,“我们的幸福并没有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得到增长,在劳动分工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有效而又迅速的发展的时候,幸福反倒以惊人的比例在不断锐减”。[68]这是涂尔干研究自杀问题的一个动机。另外的动机在于,他想通过对某个社会事实的研究,来证明社会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是独特的、科学的,能够和心理学、哲学等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证明社会学方法论基本原则的优越性。“因为社会学一日不摆脱政党的争论,一日不摆脱浅俗的思想,一日不摆脱普遍概括的解释,则社会学就永远也离不开用感情和臆断去从事自己的专门研究,也就难以指望社会学的提高。诚然,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路途尚远;但是为了这个目的,社会学者必须从今日做起。”[69]《自杀论》的副标题就是“社会学研究”。
一、关于研究对象的几点说明(导论)
涂尔干指出,关于自杀研究的第一个任务是:确定我们打算在自杀的研究范围内进行研究的社会事实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对自杀的社会事实进行研究。
涂尔干认为,日常语言中的概念和科学的概念不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是模棱两可的,后者是严谨的。依据社会学研究中下定义的客观原则,涂尔干给自杀下了定义:“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70]那么,社会学对于自杀的研究,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呢?涂尔干做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一般人们会把自杀看做是纯粹个人的行为——根据自杀者的脾气、性格、经历、个人历史上的大事件来解释他的自杀选择,而且自杀这种行为也只对个人产生影响,自杀貌似只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但是,研究自杀现象不仅仅只有个人这一个层次,还可以有社会的层次——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这就是自杀率。“事实上,如果不把自杀仅仅看成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开来考察的特殊事件,而是把一个特定社会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自杀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整体不是各个独立事件的简单的总和,也不是一个聚合性的整体,而是一个新的和特殊的事实,这个事实有它的统一性和特性,因而有它特有的性质,而且这种性质主要是社会性质。”[71]自杀率或自杀死亡率通常以一百万或十万人中的死亡人数来计算。涂尔干强调,社会学对自杀的研究并不是要开一张尽可能包括一切可以算作个别自杀起因的完整清单,而只是研究决定社会自杀率高低的条件。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也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关于自杀研究的根本区别。社会学对个人自杀现象不感兴趣,只是考察自杀率产生的条件即可能影响群体而非可能影响个人的原因。在自杀的各种因素中,社会学家只关心“那些使整个社会都感觉到它们的影响的因素。自杀率是这些因素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因素”。[72]涂尔干强调,自杀当然会表现出取决于个人固有性格的个人方面的特点,“每一个自杀者都给他的行为打上个人的印记,这种个人印记表示他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特定环境,因此不能用这种现象的一般社会原因来解释。但是这些社会原因也必然给它们所引起的自杀打上一种特殊的印记,一种表示这些原因的特殊标志。我们所要找的正是这种共同的标志。”[73]当然,这种寻找只能做到大致准确,因为它只是选择最一般和最明显的特点。
在《自杀论》导论中,涂尔干说明了全书的结构,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说明非社会原因对于自杀率的“影响”——“我们将会发现这种影响根本不存在,或者十分有限”[74]。第二部分对于影响自杀率的社会原因做详细的探讨——探讨社会原因对自杀率产生影响的方式,社会原因和个别情况的关系,个别情况与不同类型的自杀的关联。通过查阅1835至1890年欧洲主要国家2.6万名自杀者的档案资料、统计数据,并对资料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整理、比较、分析,涂尔干驳斥了当时对自杀的一些流行的、非社会因素的解释,得出了社会因素决定自杀率高低的结论。
二、非社会因素与自杀率的“关联”
在《自杀论》的第一编,涂尔干对自杀的非社会因素的解释进行了驳斥。
涂尔干首先分析了自杀与心理变态的关系。人们通常会认为,自杀是由于精神错乱引起的,是个体性的疾病,包括躁狂性自杀、忧郁性自杀、强迫性自杀、冲动性或不由自主的自杀等形式。他批评这种流行的观点说:“所有精神错乱的自杀都没有任何动机,或者是纯粹想象的动机所引起的。然而,许多自愿死亡既不属于这一范畴,也不属于另一范畴;其中大部分都有动机,而这些动机并非没有现实的基础。因此,不能把任何自杀者都看成是疯子,除非滥用名词。”[75]换言之,有些自杀不是精神错乱引起的,而且这种类型的自杀为数不少:“这些自杀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这种慎重考虑的各种表现并不完全是出于幻觉。……既然精神错乱者的自杀并非所有类型的自杀,而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构成精神错乱的心理变态的普遍性并不能说明集体的自杀倾向。”[76]当时涂尔干所掌握的所有的统计资料都证实,在精神病院里,住院病人中的女性略多于男性。例如,1855年,挪威,每百名精神错乱者中的女性为56名,男性为45名。1847年,丹麦,每百名精神错乱者中的女性为55名,男性为45名。1891年,法国,每百名精神错乱者中的女性为52名,男性为48名。这说明,精神病患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如果用共变法来验证因果关系——分析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法国、丹麦、英国等国家19世纪30—70年代男性和女性在自杀总数中所占的份额,结果则排除了心理变态对自杀率的解释:女性的自杀倾向并不超过或者等于男人的自杀倾向,“自杀碰巧基本上是一种男性的感情表现形式。有1个妇女自杀,就平均有4个男子自杀。因此,男女都有某种明确的自杀倾向,这种倾向对于每一种社会环境来说甚至是固定不变的。但是这种倾向的强度丝毫不像心理变态因素那样变化”。[77]例如,在奥地利,1873至1877年自杀的绝对数为:男11429人,女2478人;每一百名自杀者中男性为82.1,女性为17.9。
其次,涂尔干分析了自杀与正常的心理状态——种族、遗传、榜样的感染力等因素的“关联”,对自杀的种族论解释进行了驳斥,证明了种族、遗传其实和自杀毫不相干。因为,同一种族内各民族之间的自杀倾向差别很大。克尔特—罗马族包括比利时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各个民族。法国每百万人中有150名自杀者,意大利在同一时期只有30名,西班牙则更少。在所有日耳曼诸民族中,德国人强烈地倾向于自杀。涂尔干列出了瑞士各州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国人、法国人的自杀率[78]:
天主教德意志人自杀人数87 新教德意志人自杀人数293
天主教法兰西人自杀人数83 新教法兰西人自杀人数456
涂尔干指出:在天主教徒中,德、法两国、两个种族的自杀率之间差别不大,但在新教徒中,法兰西人的自杀明显多于德意志人。由此证明,种族、民族与自杀率的关联不是必然的。关于遗传对自杀的影响的观点,涂尔干认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子女从父母那里遗传的是某种一般的气质,这种气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使他们倾向于自杀,但并非一定是这样——各种形式的神经衰弱,丝毫不能说明自杀率的差异。关于仿效,涂尔干的解释是:在互相模仿而自杀的事例中,强迫观念难以抗拒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因为一旦引起自杀念头的东西消失,自杀就停止了。例如,在1772年一段很短的时间内,15名残疾军人相继在残疾军人院阴暗过道里的同一只钩子上自缢身亡,钩子被取走后,自杀现象也消失了。总之,“一方面,那些最有利于说明自杀的遗传性的情况不足以证明这种遗传性的存在;另一方面,这些情况毫无困难地适合于另一种解释。”[79]而且,如果遗传对自杀有影响的话,那么因为遗传是不分性别的,它应该同等程度地对女人和男人的自杀率有同样的影响——自杀本身也不应该有性别的差异。但是,女性的自杀率低于男性。
随后,涂尔干又分析了自杀与自然因素的“关联”,对天象论进行了驳斥。涂尔干掌握的资料表明,气候和季节性气温与自杀率有共变关系:欧洲的南部和北部自杀人数最少,自杀人数最多的是中部——这个地区恰好也是欧洲气候最温和的地区。那么,是否可以得出气温决定自杀的结论呢?显然不可以。“自杀和某种气候非但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任何气候下都时有发生。今天,意大利自杀的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但在帝国时代却是很多的,当时罗马是文明欧洲的首都。同样,在印度灼热的天空下,某些时代自杀的人也很多。”[80]涂尔干强调,应该从一个地区文明的性质,从这种文明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布状况而不是从气候的神秘力量中去寻找不同国家人民具有不同自杀倾向的原因。至于统计数据所呈现的自杀率从1月到7月越来越高,涂尔干的研究发现:“这不是因为炎热扰乱了人的机体,而是因为社会生活越来越繁忙。毫无疑问,社会生活之所以繁忙,是因为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和气候状况等等使社会生活比在冬季更容易展开。但是,直接刺激社会生活的不是物理环境;影响自杀人数多少的尤其不是物理环境。自杀人数的多少取决于社会条件。”[81]
三、影响自杀率的社会原因探究
在《自杀论》的第二编、第三编,涂尔干直接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论对自杀的社会原因作了探讨。
涂尔干先将自杀作了分类。他指出:“我们可以确定自杀的各种社会类型,不是直接根据事先描述的特点,而是根据产生这些类型的原因来加以分类。我们不必费劲去弄清这些类型为什么彼此互不相同,而是立即探索决定这些类型的社会条件;然后根据这些条件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把这些条件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哪一种特定类型的自杀和哪一种类别的社会条件相对应。总之,我们的分类是一种病因学的分类,而不是形态学的分类。”[82]涂尔干认为,这种分类方法并不是一种下策——如果我们知道一种现象的原因,就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这种现象的性质。在这种分类中,“我们撇开作为个人的个人、他的动机和想法,直接考虑自杀是随着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宗教信仰、家庭、政治团体、行业团体,等等)发生变化的。只是在这之后我们才重新回到个人,研究这些一般的原因是如何个性化而引起它们所导致的自杀后果的。”[83]
(一)对利己型自杀的研究
在对利己型自杀下定义以前,涂尔干先考察了欧洲宗教信徒的自杀分布: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这些纯粹的天主教国家,自杀很少,平均每百万居民中自杀数为58人;而在普鲁士、丹麦等新教国家里,自杀是最多的,平均每百万居民中自杀数为190人。考察其他数据也表明,各地新教徒中的自杀人数都比其他宗教的信徒多。涂尔干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原因时发现,“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唯一的基本区别是,后者比前者在更大的程度上允许自由思考。……天主教徒自然而然地接受它的教义,不加思考。他甚至不能对它的教义进行历史的检验,因为人们所依据的原始经文禁止他这样做。为了使传统不致发生变化,巧妙地建立了一整套权威的等级制度。一切变化都是天主教思想所厌恶的。相比之下,新教徒却是他的信仰的创造者。《圣经》掌握在他的手里,任何解释都不能强加于他。甚至这种改革过的宗教信仰的结构也使这种宗教个人主义状态不可忽视。”[84]于是,涂尔干推断:新教徒的自杀倾向一定与推动新教产生和发展的、动摇了传统信仰的自由思考有联系。新教不太重视共同的信仰和实践,所以,它比天主教允许更大个人思想的自由。“一个宗教群体越是受个人判断的支配,这个群体就越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更没有内聚力和生命力。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教徒的自杀比较多是因为新教是一个不像天主教会那样非常整体化的教会。”[85]“宗教是一个社会,构成这个社会的是所有信徒所共有的、传统的、因而也是必须遵守的许多信仰和教规。这些集体的状态越多越牢固,宗教社会的整体化越牢固,也就越是具有预防自杀的功效。”[86]随后,涂尔干又对家庭关系因素、政治动荡因素与自杀率的关联进行了考察,发现: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宗教社会、家庭社会、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
在对利己型自杀进行了上述考察之后,涂尔干对利己主义自杀或利己型自杀下了定义:“个人所属的群体越是虚弱,他就越是不依靠群体,因而越是只依靠他自己,不承认不符合他私人利益的其他行为规则。因此,如果可以把这种个人的自我在社会的自我面前过分显示自己并牺牲后者的情况称之为利己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产生于过分个人主义的特殊类型自杀称之为利己主义的自杀。”[87]简言之,利己型自杀与社会整合度成反比。在这种自杀类型中,“把人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之所以松弛,是因为把人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松弛了。”[88]
(二)对利他型自杀的研究
涂尔干首先分析了原始民族中的自杀形式:开始衰老或得了病的男子的自杀,妻子在丈夫去世时的自杀,被保护者或仆人在其主人去世时的自杀。他指出,这些自杀,不是因为自杀者有自杀的权利,而是因为他们有自杀的义务。如果他们不履行这些义务,就会受到侮辱或惩罚。“如果他坚持要活下去,公众就再也不会尊重他:在有些地方,人们拒绝给他举行一般的葬礼;在另一些地方,等待着他的必定是某种比坟墓还要可怕的生活。因此,社会逼着他去自杀。”[89]在此基础上,涂尔干对利他型自杀下了定义:利他型自杀是由于社会过分使个人从属于社会而造成的。利己主义状态指按照个人的生活而生活、只服从自己的自我感觉状态。利他主义与此相反,它表示的是:自我不属于自己,他要么和自身之外的其他人融合在一起,要么他行为的焦点在他自身之外的、他从属于其中的某个群体。“因此我们把某种极端利他主义所导致的自杀称之为利他主义的自杀。”[90]涂尔干还考察了军队中的自杀率,他指出:军队是一个严密的清一色的群体,“是大多数取决于利他主义情绪的自杀的舞台;没有这种利他主义情绪,也就没有军人气概了”[91]。涂尔干发现:随着服役年限的延长,士兵的自杀率会逐渐增加。因为士兵自我克制倾向、对非人格化的爱好是在比较长期的训练中才能发展起来的。从职阶的角度看,士官比军官更容易自杀,“是因为军官没有在同样的程度上要求养成服从和被动习惯的职责。军官不管多么守纪律,他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主动性,他们的活动范围更广,因此个性也更成熟。因此,有利于利他主义自杀的条件在他们身上不像在士官身上那么完全得到实现;因为他们更强烈地感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不太倾向于放弃生命。”[92]
社会整合度高,决定了利他型自杀率高。这是涂尔干关于利他型自杀的研究结论。
(三)对失范型(反常型)自杀的研究
涂尔干认为,“社会不仅仅是以不同的强度引起个人对它的感情和活动的客体,它还是调节个人感情和活动的一种力量。在这种调节活动的方式和社会自杀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93]
涂尔干首先探讨了经济危机与自杀率的关联——经济危机对自杀的倾向有严重的影响。但问题是:“这些危机靠什么产生影响呢?是不是因为这些危机在使公共财富减少的同时增加了贫困?是不是因为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所以人们更自愿地放弃生命?这种解释因为简单而吸引人,而且符合流行的自杀概念。但是这种解释与事实背道而驰。”[94]实际上,贫困不是引起自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经济动荡所带来的失范、反常——社会规范化程度与自杀率有反向的关系。社会规范对人的行为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经济波动、社会失范状态会促成自杀率的提高。这时的人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可能做到的或不可能做到的;什么是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什么是合理的要求和希望,什么是超过了限度的要求和希望。“因为斗争不受约束,还因为竞争更加激烈,所有的阶级都被卷了进去,因为再也没有固定的阶级区分。因此,在作出的努力变得更加毫无结果的时候,却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活下去的愿望怎么会不减弱呢?”[95]于是,工商界人士的自杀率高于从事农业的人。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混乱是经常起作用、引起自杀的因素。涂尔干指出,这种类型的自杀不同于利己主义自杀和利他主义自杀,因为它不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方式,而取决于社会管理个人的方式。失范型或异常型自杀产生于自杀的人的活动失常并由此受到损害。
此外,涂尔干还界定过一种宿命型自杀的类型:面对无能为力的规则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改变性,有的人会采取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宿命型自杀是因为过度的社会控制造成的。
总体而言,涂尔干的《自杀论》有一个完整的理论结构:第一,论证了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自杀率,排除了各种非社会性的解释;第二,在社会性因素方面,涂尔干用社会整合与规范作为自杀率高低的解释项;第三,涂尔干对自杀率变动提出了如下的解释:社会规范及其效力影响着社会的自杀倾向。他指出:“社会自杀率只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在任何时候,决定自杀人数多少的都是社会的道德规范。”[96]社会道德作为一种“集体的倾向有它自身的存在,这是一种和自然力同样实在的力量,尽管属于另一种性质;它同样从外部作用于个人,尽管通过另一些途径。使我们能够肯定前者的现实性不亚于后者的现实性的,是前者以同样的方式,即以它的影响的稳定性,证明它自身的存在。”[97]利己主义、利他主义、一定程度的失范或反常在不同的社会中会按照不同的比例组合,它们是典型的道德的体现。涂尔干的自杀研究建立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在方法论上诠释了实证主义的研究立场和范式。他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自杀,说明自杀主要是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杀人找不到凶手、杀人于无形。在此基础上,涂尔干得出结论:要减少自杀,就必须改造社会,使之朝向消除或减少自杀社会成因的方向发展。但究竟如何改造社会,却不是很好回答的问题。例如,镇压手段和教育对预防利己型自杀的效果非常有限,只有强化集体的整合性才能有效地预防利己型自杀。在《自杀论》的最后,涂尔干指明了社会学研究者的使命:“社会的现实不是很简单的,我们还不太了解它,所以不能预料到它的一切细节。只有和事物直接接触,才能使科学的各种学说具有所缺少的确定性。一旦确定了弊病的存在、内容和原因,如果我们因此而知道了补救办法的一般特点和应该何时使用这种补救办法,那么重要的不是先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而是果断地行动起来。”[98]
涂尔干的《自杀论》是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典范,在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脉络中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也启发和推动了后来的越轨社会学研究。
总体来看,涂尔干坚持研究方法上的实证主义立场,研究对象上的对社会事实的客观分析,理论取向上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社会团结情结,在社会学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社会学确立了社会整合、社会秩序这一基本的研究主题;提供了社会学独特的、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观察社会的视角;制定了后来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整套指导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完整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地位;在经验研究方面为后来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经典性的研究范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考验,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以及在许多具体问题方面所提出来的那些基本概念、命题和思想已经深深地渗入到现代社会学当中,成为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之一,对人类的思维散发着经久不息的影响,值得我们反复地去加以研读和思考。”[99]但是,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忽视了社会微观层面的现象,忽视了阶级、阶层的区别及其斗争,是不全面的。对于社会变迁及其机制的说明显得单薄、缺乏说服力。但是,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意义在于:“一种思想之所以会有生命力,并不是因为它可以通盘解决各种问题,而是因为它为后人铺陈了各种活生生的问题。就此而言,涂尔干社会思想对今天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他所确定的各种概念、假设和命题,更重要的是,它始终蕴含着‘必要的张力’,为人们思考他所切身感悟的各种问题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100]
思考题
1.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2.涂尔干所划分的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各具有哪些特点?
3.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是如何运用其方法论原则进行研究的?
4.以《自杀论》为例说明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意义。
5.如何评价涂尔干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注释】
[1]〔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4页。
[2]渠东、汲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编选说明”,见〔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3]〔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4页。
[4]〔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实用主义与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5]〔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6]〔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7]〔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8-309页。
[8]〔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9]〔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6页。
[10]括号中的英文来自S.A.Solovay and J.H.Mueller于1938年的翻译本,以及1966年由纽约The Free Press重印的英文翻译本,下同。
[1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2]〔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页。
[13]〔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7-308页。
[14]〔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2页。
[15]〔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页。
[16]〔英〕杰弗里·亚历山大编,戴聪腾译:《迪尔凯姆社会学——文化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7]〔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7页。
[18]〔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9]〔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页。
[20]〔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23]〔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4]〔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5]〔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6]〔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7]〔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11页。
[28]〔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29]〔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30]〔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3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3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www.zuozong.com)
[33]〔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34]〔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5]〔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1页。
[36]〔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37]〔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38]〔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39]〔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43页。
[40]〔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4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4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43]〔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44]〔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45]王小章:《经典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46]〔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47]〔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48]〔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1页。
[49]〔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1页。
[50]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51]又译压抑性法律。在这类法律下,犯罪者做出的任何举动,如果被社会看做是违背当时强大的集体意识的,就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偷猪者可能会被砍断双手,亵渎神明者会被割下舌头。
[52]又译恢复性法律。在这种法律之下,人们不会再因为触犯集体意识的事情而被严厉惩罚,而是会被要求顺从法律或对那些被其行为所伤害的人提供补偿。比如,偷猪的人可能会被要求在被偷者的农舍工作一百小时,或者被关进监狱接受法律制裁。
[53]〔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页。
[54]〔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16页。
[55]〔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6页。
[56]〔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7页。
[57]〔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2-153页。
[58]〔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97页。
[59]〔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页。
[60]〔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页。
[61]〔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页。
[62]〔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0页。
[63]〔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13页。
[64]〔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17页。
[65]〔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0页。
[66]谢立中:《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67]〔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05页。
[68]〔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06页。
[69]〔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70]〔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10页。
[7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7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页。
[73]〔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0页。
[74]〔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页。
[75]〔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页。
[76]〔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页。
[77]〔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页。
[78]〔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4页。
[79]〔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5页。
[80]〔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2页。
[8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0页。
[8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7页。
[83]〔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2页。
[84]〔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9页。
[85]〔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1页。
[86]〔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3页。
[87]〔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5页。
[88]〔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1页。
[89]〔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6-197页。
[90]〔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9页。
[9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6页。
[9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2页。
[93]〔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0页。
[94]〔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1页。
[95]〔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5页。
[96]〔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9页。
[97]〔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8-289页。
[98]〔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73页。
[99]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100]渠东:“译者序言”,见〔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