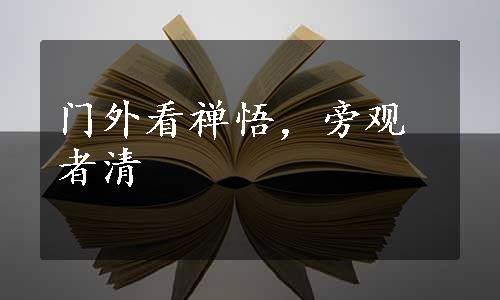
禅悟之境难言,但终于不得不言(包括无声的形相),除非不想与己身之外的人通。这,南宗的禅师们有惯用的办法,多用机锋、棒喝之类。可是我们不能用,因为我们的要求是“常人”能够了解。禅悟,在禅林的门内看,是超常的;在门外谈禅悟,是以常对付超常。这有困难,有人也许认为不可能。对待这样的困难,显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知为不知;另一条是勉为其难,虽然站在门外,还是要张目细看。当然,我们只能走后一条路,因为谈就是想了解。这里的问题是,在门外能否看见门内。说能,近于大话,不好;那就无妨说,可以试试看。这样做也不无理由。其一,可以请《庄子》来帮忙,《秋水》篇末尾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象注、成玄英疏都认为,这场辩论,庄子得胜,是因为惠子反驳庄子时候,早已承认此可以知彼,据自己的此可以知彼而驳他人的此可以知彼,当然站不住脚。这再放大或加深一些说,就是知识论所显示的:不管你怎样富于怀疑精神,总要承认“能知”。其二,缩小到本题,禅悟带有神秘性,被繁琐名相(包括现代式的)包裹的时候更带有神秘性。科学常识的精神是破译神秘性,如果这种努力是常常有成效的,则站在门外看禅悟也许不无好处,那是旁观者清。其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在禅林里也未能免俗,因为见桃花而悟的所得与听驴叫而悟的所得,虽然都是冷暖自知的事,我们总可以推断,那是二,决不能是一。禅林内不得不容许不同,我们当然也可以利用这种容忍精神,说说我们的所见,对,即使不容易,算作聊备一说也好。这说来话长,先说为什么要这样求。(www.zuozong.com)
这来源,前面已经说过,是佛家觉得人生有问题,而且想解决。专就这一点说,圣哲与凡夫没有什么区别;至多只是量的,圣哲钻得深,凡夫只是星星点点。区别来于把什么看成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在佛家的眼里,人生是苦,而且灵魂不灭,死后要轮回,所以是无尽的苦。这种看法,常人不会同意;或者虚其心,实其腹,根本不在这方面费心思。常人感到人生有乐,并且尽力去营求。但只是这一点还不能驳倒佛家,因为对于人生,人人有提出并坚持某种看法的权利,何况人生过程中也确是有苦。这苦,来于想什么不能有什么,如富厚、恋情之类;更难忍的是不想有什么而偏偏有什么,如饥寒、刑罚、病死之类。这是就常人说;佛家就更严重,因为还相信有六道轮回。对付苦,不同的人,更明显的是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态度和办法。积极的是改,消极的是忍。见诸实际,绝大多数人是改和忍兼用:能改就改,改不了就忍(包括被动的)。这样处理,不管效果如何,总不能与苦一刀两断。佛家怀有最高的奢望,并决心以“大雄”之力,与苦一刀两断。怎么办?苦,来于物、我不能协调。山珍海味好吃,要去买,买要有钱;红颜翠袖可爱,想得,要征得人家同意;更难办的是,花花世界复杂,不管你怎样修身谨慎,也不能绝对避免天外飞来的横祸;最后,即使如秦皇汉武那样,力大如天,长生不老还是可望而不可即。不能不死。协调,中道,难;理论上,免苦还有两端的路。一端是屈物伸我,就是把“想什么不能有什么”和“不想什么而偏偏有什么”变为“想什么有什么”和“不想什么就没有什么”。这要强制外界如何如何,可是外界不会这样听话,何况所谓外界还包括千千万万与自己类同的人,会冲突。屈物伸我是外功,路难通;只好试试另一端,内功,屈我伸物。这是不管外界怎样可欲而不听话,我只是不求;不求,自然就不会患得患失。可是不求,说似乎容易,做就太难,因为“人生而有欲”,“率性”是顺流而下,不率性是逆水行舟。佛家,就算戴着有色眼镜吧,睁眼看见的是苦,闭眼想到的是灭苦;为了彻底灭苦,是一切在所不计。或者说,他们打过算盘,计的结果是,灭苦,外功必不通,内功可通,甚至必通。这内功是灭欲(解脱并度人的大欲除外)。而说起欲,质实,活跃,很难对付。可是因为它与苦有不解之缘,为了灭苦,一切在所不计,也就不能不树立对欲,连带的对外界,对人生,对一切的一反常情的看法。这看法的树立显然不容易,一方面要能知,确认一切常识的所谓可欲并不可欲,所谓真实并不真实;一方面要能行,真就成为无欲。这内心的变革,佛家最重视,所以称未能变革者为迷,已变革者为悟,或禅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