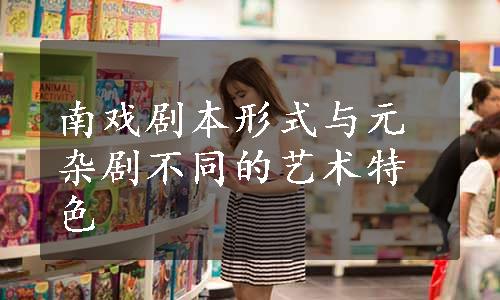
宋元南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它所继承的艺术传统,都与元杂剧不尽相同,因而它的剧本形式有着与元杂剧不同的艺术特色。
元杂剧因为音乐结构的限制,形成了特有的“四折一楔子”的剧本体制,南戏则采取了一种更灵活的分场形式,所谓分场,就是以人物的上下场为界线,把剧本分成若干段落,每一段落各成一场,我们上文介绍的剧本中,《张协状元》分为五十多场,《宦门子弟错立身》是经过节略的本子,只有十几场。很显然,作者据剧情需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并无元曲那样明确的形式规范。这种分场也长短不一,交待人物和衔接、过渡剧情的场次往往轻描淡写,一带而过,需要集中刻划人物、表现强烈戏剧冲突的场面则多施笔墨。如《张协状元》中,张协上京赶考一场,就用一支【望远行】一笔带过,而贫女上京寻夫一场戏则有七支曲子,中间还穿插进对白、独白和动作表演等,就显得比较复杂细致了。
在场次安排上,南戏剧本开头照例有一段介绍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叙述故事梗概的开场戏,这种形式为后来的戏曲继承和保留,叫做“副末开场”。比如,《琵琶记》中开篇一支【水调歌头】就表明作者“不关风化事,纵好也徒然”的观点并大致交待了剧情。在前几场戏中,男女主角和主要配角要先上场与观众见面,在故事展开过程中要照顾到脚色行当的劳逸、大小场子的安排和冷热场子的调剂,这样一来有利于观众欣赏,二来也利于演员的表演。
在每场戏里,剧本又用歌唱、念白及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这就是杂剧和南戏共有的曲、白、科(介)(元杂剧称科,南戏称介)相间的文学剧本形式。南戏的体制不同于元杂剧的人一主唱,而是各种角色行当均可以唱,这就给曲、白、科的综合运用提出了有利的舞台条件。多种演唱形式和念白动作的综合运用,对于塑造人物性格,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是极为有利的。
总之,早期南戏剧本反映生活的范围、深度和能力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毕竟还是我国较早的一种戏剧形式,还存在着相当的缺陷。比如,从分场结构来看,《张协状元》的分场就很琐碎,一本戏长达五十几场,人物的上下场显得很匆促,而且还有累赘之处;对于戏曲表现手段的运用还略显单一,不够成熟,歌唱时,很多抒情叙事的唱段发挥得还很不充分,也很少出现细致刻划人物心理的唱段,念白较杂芜,插科打诨常常游离于剧情之外,这是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乐的基本形式在南戏中的残留物,使得结构散慢冗长。
南戏的这些早期特征在同北杂剧交流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以“荆、刘、拜、杀”四大传奇和《琵琶记》为代表的成熟的南戏,为后世的传奇体制奠定了基础。(www.zuozong.com)
后期南戏剧作家们对于南戏的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互相调协的问题比较注意,而且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们结合剧情发展而合理安排一套曲子中的曲牌,把琐碎的场子集中为用套曲子唱的一场戏,剧情集中了,戏剧性也就随之加强了。比如《琵琶记》共四十五场,差不多每一场都有单独的任务。这种以套曲的起迄而划分出的场子,后来叫作“出”,或“折”。南戏的“分出”和元曲的“四大套”的形式是不同的,不仅可以在一出戏里安排两套曲子,而且每一套曲子的曲牌数量也不象杂剧那样固定。在过场戏里使用的组曲,往往又不在套曲之内。这种过场戏既可以合并到大场子里合为一出,也可以独立成出。所以,后期南戏在结构上虽已逐渐走向严谨,但它仍然保存了早期南戏的灵活性。
后期南戏的另一大发展是各种艺术手段的有效运用。在北杂剧艺术的影响下,特别是元末南戏作品中,由于描写悲欢离合的内容增加了,回忆、思念等关目几乎每本戏都有,所以大段抒情性独唱运用十分普遍,这样就有利于表现人物心理,刻划人物形象。
插科打诨的场次也不再游离于剧情之外,而是与剧情有机结合起来,为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服务,剧本结构起伏有致,密而不乱。
虽然后期南戏较之早期南戏有很大发展,但有一些问题是它始终没有解决的。如一本戏动辄数十出,结构不免庞大松散,再则由于音乐结构日趋严密,音乐结构和戏剧结构往往发生矛盾,有时为了适应音乐结构不得不调整戏剧结构,出现人为痕迹,影响剧情的发展。这些不足之处到明代昆山腔、弋阳腔剧本中,才逐步得到改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