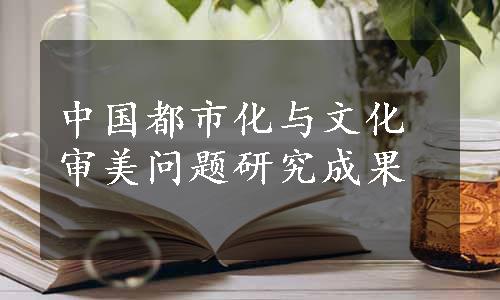
在古典形态的文化都市中,尽管城市文化在结构与功能上已形成较大的规模,甚至在某些时期与阶段会出现惊人的繁荣景象,但由于在人口与空间规模、生产方式与经济总量、交通设施与通信技术、意识形态与文化生态、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巨大的历史差异,它与都市化进程中迅速崛起的文化都市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这两种具有渊源关系的“家族城市形态”进行深入的比较与分析,既可以使文化都市的当代性内涵得到充分的再现与展示,同时也可为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国城市揭示一条正确的文化发展之路。
在学术层面上看,古典文化都市基本上可以文化地理学的“文化城市”来指称与标示。文化城市是“以宗教、艺术、科学、教育、文物古迹等文化机制为主要职能的城市。如以寺院、神社为中心的宗教性城市:印度的菩陀迦亚、日本的宇治山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阿拉伯的麦加等;以大学、图书馆及文化机构为中心的艺术教育型城市,如英国的牛津、剑桥等;以古代文明陈迹为标志的城市:中国的北京、西安、洛阳等,日本的奈良、京都,希腊的雅典和意大利的罗马等。文化城市是历史的产物,虽然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功能,但伴随文化发展出现人口集聚、市场繁荣、交通发达等趋向时,这类城市的商业、旅游服务及运输、工业等职能也应运而生,这就使一些文化城市向具有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发展或向其他主要职能转化。”[24]由此可知,文化城市的基本特征可表述为二:一是丰富的文化资源,二是必须有特色文化,前者表明文化城市是人类生产与创造的结果而不是大自然固有的,后者则意味着它们是不同民族、地域及文化的具体表现而非千篇一律的。除了特征,更重要的是文化活动对城市发展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知,文化城市不是一个实体概念,或者说与城市政治、经济等实体性的城市空间与功能结构毫不相干;它的本义在于对城市已有的资源与空间进行文化再生产,使文化功能更多地渗透到城市结构与社会的各层面,使一个不同于城市政治与经济结构的文化空间生产出来。从城市空间功能演化的角度看,文化城市突破了政治与经济两种实用形态,它的突出特征是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功能成为推动城市形态演进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机制。如定义中所列举的那些城市,在其繁盛时期既是某个时代的文化中心,同时又创造了更为辉煌的文化成果,并因为它巨大的文化创造使城市本身的存在化作了不朽的城市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以文化城市来界定与理解古典文化都市及其现代命运是十分恰当的。
在以文化功能与精神活动为城市核心凝聚机制方面,文化都市与文化城市是家族类似的;由于时代背景、现实机遇与发展水平的差异,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可以从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与性质等角度加以认识。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25]这说明城市化进程早在原始时代末期就已萌发。但实际上,在具有浓郁乡村风格的古代世界中,城市化的进程很难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与人口的回应。这正如芒福德所说:“直到近代城市化时期以前,城市还仅只包含了人类很小的一部分。”[26]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不断加速的态势,但它真正走上“高速公路”却不过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对此需要借助我们提出的“都市化进程”理论来理解。都市化进程是城市化进程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是20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都市化与城市化最大的共同之处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从自然向社会、从农业地区向城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而不同之处则是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速度相对均衡、规模相对有限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不同,都市化进程意味着人口、资金、信息等社会资源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高速流动与大规模聚集,这既在时间上表现为节奏越来越快,同时在空间上也呈现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新特点。由于聚集了全球的最优质的人力资源、最有活力的经济财富与最发达的文化资本,都市化进程使整个人类都被卷入自己的滔滔洪流中,构成了影响当今世界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这在深刻与全方位地影响现实世界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当代都市的形态、结构、功能与性质。无论是深入理解当代文化都市的结构与性质,还是正确分析与阐释它与传统文化都市的本质差别,都要从都市化进程以及当代城市在这一进程中的巨大变化入手。
首先,都市化进程直接表现为城市人口与空间的巨大增长,推动了城市在结构与功能上的更大发展与升级,使当代文化都市所依托的都市形态与传统大城市有了重要区别。不同的城市形态对城市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如李翰(Richard Lehan)指出:“近三百年来,城市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命运——它也与我们个人和民族的命运不可分。作为启蒙的产物,都市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中心。”[27]在都市化进程中,城市的最高空间表现形式已不再是单体城市,而是由若干发达的大城市通过更高层次的组织与联系而形成的大都市群。尽管都市自古就有,形态也十分丰富,如两汉赋家写到的“两都”“京都”“蜀都”,如斯宾格勒提到的“首邑城市”,但它们与当代世界级都市群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由于依托城市在规模与性质上的巨大差异,使两者呈现出鲜明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具体说来,古典文化都市一般都是历史上的都城或大城市,是倾尽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的经济社会资源才成就的文化中心。但由于政治、经济,甚至是交通方面的偶然变化,它们往往要陷入残酷的“去中心化”的现实进程中。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未能及时更新升级的城市本身的衰微,丧失了强大支持的城市文化也只能接受“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的凄惨命运。一方面,城市固有的文化生产功能逐渐衰老与退化,丧失了吸收、同化与创造新文化的精神机能,另一方面,是曾经繁花似锦、威仪天下的壮观文化景象,由于人口的离散与城市的破败而转化为只能听任后人瞻仰与感慨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都市的命运与城市的结构与性质密切相关,当代世界中为数众多的“旧国旧都”,都可以充当这方面的典型与范例。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是建构当代文化都市最重要的现实背景,而古典文化都市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有这种可以使自身充分发展的“硬件”。(www.zuozong.com)
其次,城市的规模扩大与版本升级,直接改变了城市文化再生产的规模与性质,导致两种文化都市在文化生产、城市文化功能等方面出现巨大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文化需要以及在需要的程度与等级有很大区别。如古代都城也有发达的娱乐业。“汴京市民们的生活环境,不是精巧雅致的书斋,清静秀丽的田园,而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喧嚣热闹的市场。在较快的生活节奏中,市民醉心于情节入胜的动人故事和满足感官刺激的热烈表演。”[28]但无论是娱乐业的规模、娱乐业的产值,还是娱乐业的品种与技术、参与活动的人群,它与当代都市的文化娱乐业都是无法相比的。而两种城市在人口规模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则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二是对都市生活的情感与态度有很大变化。与古代农民对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的敬畏与恐惧(如中国古代诗人最向往的是田园生活),以及现代人对主要作为经济中心的“大城市”的厌恶与憎恨(如西方现代诗人以“荒原”“恶之华”“恶心”等比喻都市生活或表达个人的生命体验)不同,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高度集中的当代大都市,给当代人带来的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文明中不可想象的重要机遇与发展空间,都市生活方式不仅不再是罪恶的象征,相反正成为人人向往的“文明中心”与“幸福生活的天堂”。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必然产生更丰富的文化需求,这就为城市文化功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城市的发展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城市文化生产力,以及提升或减弱城市文化功能在城市整体发展中的作用。以城市文化资源的再生产为例,古典文化都市一般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由于城市整体功能与水平的落后与不发达,如何使资源产业化成为它们普遍面临的最头痛的问题,以至于只能充当发达城市的生产资料产地。与古典文化都市不同,一个当代文化都市很可能没有什么传统文化资源,但由于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聚集起来的人口、财富与文化资本,因而不但可以把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都变为自己的生产对象,同时也很容易在文化资源与文化生产之间形成的良性循环生产关系。由此可知,对于当代城市而言,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拥有文化资源或拥有的数量,而在于它们所赖以存在、延续与发展的城市本身的结构与性质。这正是一些城市众多的文化资源默默无闻,更有甚者还会成为城市发展的沉重负担,而另一些城市却由于它自身固有或引进的文化资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的根源。
再次,城市文化生产力的水平差异,最终体现为形态不同的城市文化模式。城市文化是文化都市的直观表现与核心内容,文化生产力越发达,城市文化就越繁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相对加大。受城市规模、形态与性质的影响,“尽管与同时代的中小城市相比,传统都城已体现出相当丰富与多元的性格,但出于维护政治统治而必须严加控制各种社会文化与精神资源的现实需要,它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多元性都是相当有限的。”也就是说,它的文化空间与功能始终受制于城市的政治与经济结构。而当代都市与此有很大不同,“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当代条件下,随着城市内部各种要素流动的不断加速及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传统都市固有的封闭体系也必然要被打破,以政治需要为中心而构成的传统城市格局也必然要被当代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中心的多级、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所取代。……正是基于当代都市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开放模式,才使得当代国际化大都市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地理—文化界限、成为一种具有‘超文本’‘全称判断’‘宏大叙事’性质的都市新模式。”[29]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出现了我们所说的都市文化模式。与在内涵上相对朴素、在结构上相对简单、在形态发展上比较缓慢、在价值上相对保守的城市文化相比,都市文化模式表现出人类生活世界中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多元性、不稳定性与开放性。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所形成、创造出的都市文化模式,不仅直接冲击了传统政治型城市及其封闭的文化结构,使城市的文化空间表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异质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更深刻地参与到城市的经济生活与生产力系统中。如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当代都市与现代工业城市的根本区别之一。后者是现代工业文明要素高度聚集的结果,前者则是都市社会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这与都市化进程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大都市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30]此外,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母体的都市文化模式还迅速成为全球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主导机制与核心市场,“在大都市社会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扩散的新型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不仅直接冲垮了中小城市、城镇与乡村固有的传统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生态,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对当代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31]这些都是都市文化模式可以对当代城市产生强大影响,以及当代城市发展越来越倚重其文化功能的主要原因。
在当今世界,不仅城市文化功能已成为衡量其发展水平、创新能力、综合竞争力与社会和谐的基本尺度,同时以城市文化功能高度发达为基础与特征的文化都市也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与核心战略框架,如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伦敦在21世纪的发展目标就定位于“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及世界级文化城市”。与传统大城市对武力、财富或繁华的炫耀不同,对城市文化的高度重视与战略规划,是文化都市最终浮出历史地表的重要表征。可以相信,随着当代文化都市在全球化风雨中不断发展和壮大,人类城市聚落特有的文化本质与功能必将获得全面的发展,并有望使希腊哲人关于在城市中生活得更美好的古老理想成为光天化日下的现实场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