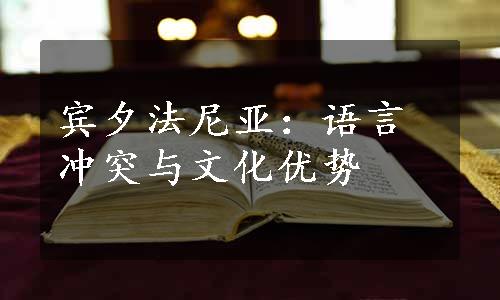
宾夕法尼亚居住区经历了类似的发展,但是德国和英国定居者之间在语言的使用上发生了主要冲突。在许多方面,宾夕法尼亚遭遇的问题预示着19世纪和20世纪关于学校语言使用的冲突。宾夕法尼亚也是殖民地政策如何把教育看成是确定一个种族优越于另一个种族的手段的最好例子。在这里,学校中使用的语言被认为是一个种族团体获得文化优势的手段。
宾夕法尼亚贵格会创立者威廉·佩恩主动地招募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上的被压迫者来到新世界定居。继最初英格兰贵格会和安立甘派定居之后是大量的德国宗教少数派,其中包括门诺派、震颤派和阿米尼派。阿米尼派和门诺派就学校教育问题与民事当局的冲突延续了整个20世纪。佩恩建立的殖民地内还居住着来自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和德国的其他宗教少数派。据本杰明·富兰克林估计,到1766年,殖民地人口共160000人,其中1/3是贵格会成员,1/3是德国人,1/3是来自欧洲其他不同地方的宗教少数派。[21]
英国对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两个殖民地之间的控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纽约,英国人力图使得殖民地的行政英国化,同时又允许文化和社会机构多元化。在宾夕法尼亚,英国人着手实行“文化英国化”的政策。[22]这一政策尤其直指德国人,因为他们在英国居民中引起了最大的恐惧。1727年一封写给佩恩的信就德国移民问题向他提出警告:“照此下去,要不了多久你在这里将会拥有一个德国人的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就像5世纪英国人从萨克逊所得到的那样。”[23]这种担心如此强烈,以致1727年宾夕法尼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责成所有德国男性移民宣誓效忠英国国王。
英国人的担心在于居民的文化和语言会成为德国人的。结果是出现了这样的建议:取缔德国人的出版社,禁止德文的政府文献印刷,以及禁止德文书籍的进口。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倡议建立英语语言学校。这些措施被看成是反抗和阻止德国文化传播的手段。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英语语言学校的主要倡导者和德国文化传播的反对者。他在慈善学校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类学校将被用做英国化的机构。这类学校最初是作为教育本地区德国贫穷儿童的宗教机构而设立的。对建校资金的需求传到了伦敦,1753年,慈善事业的狂热支持者威廉·史密斯宣称:“通过在同一所学校对英国和德国的年轻人施以共同的教育,他们通过玩乐会相知相识,建立起联系,并给各自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将学到英语和共同的行为方式。”[24]
1755年初,第一批学校建立起来了,并从富兰克林那里购买了印刷机。德国人社区立即开始攻击学校讲授的是虚假的德国文化,这种攻击导致了学校的失败。1759年在其鼎盛时,学校只有600~700名学生,其中2/3是德国人。到1764年这项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失败。[25](www.zuozong.com)
宾夕法尼亚努力使德国人英国化的简短历史在美国教育史上说明了一个永久的主题:使用学校作为扩大某种特定文化的工具,导致了组织化的学校体系与移民团体、土著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关系紧张。在19世纪,由于天主教认为公立学校系统是新教的学校而造成了宗教紧张局势,人们认为这也是文化差异的结果。
尽管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逐渐地变得英国化了,他们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仍保留着自己的德国学校和教会。结果是殖民地的教育体系变成一种依赖于学徒制、私立学校和由不同宗教派别开办的学校的混合体。通过慈善学校使德国人英国化的尝试是美国把教育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手段的首次尝试之一。
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许多宗教学校的教育目的和新英格兰学校的教育目的相类似。记忆、服从和权威都是教学和课程所强调的东西,《新英格兰读本》是殖民地通用的教材。然而,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教育体系发展的类型又与新英格兰和南方殖民地有着明显的不同。新英格兰把重点放在城镇学校的建立上,确保宗教价值观的永久化和对政府的服从。南部殖民地除了私立学校和种植园主阶层的家庭教师教育之外,对教育机构的发展兴趣不大。
这些地区差异是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一项功能。这些差异中最为持久的是南北之间的差异。在整个19世纪,南方在发展政府开办的教育体系的方面要落后于北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两个地区一直对种族隔离教育的问题持不同看法。一直到20世纪50 60年代,南北教育体系之间的主要差别才开始消逝。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