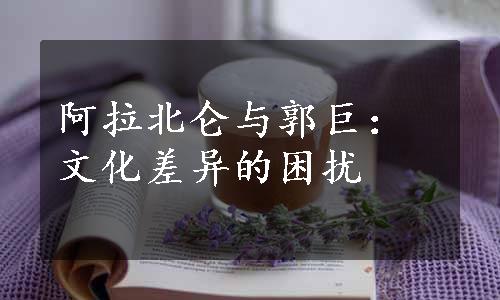
郭巨虽然隶属北仑,但只要一开口,别人就听得出你是郭巨人,因为郭巨话与北仑其他地方的话有较多不同。
就说郭巨两字,“巨”的发音就不一样。再比如说“我”字,发音也有较大差异,郭巨的发音更接近于“鹅”。
宁波话里,“阿拉”是个代表性词语,全国人基本都知道“阿拉”代表着宁波或上海。“阿拉宁波人”可以成为书名,可以成为电视节目,这句话更是宁波人的口头禅,其中的自豪与得意之情,可以与“阿拉上海人”相比肩。北仑更富有创意,把阿拉直接写进了歌词,几年前有首歌曲《让世界与我们共成长》,那首歌就是以阿拉开头的,“阿拉,阿拉,阿拉……东海边热土上,让我们播下希望……”从而让世界认识了阿拉北仑,让世界与阿拉北仑共成长。
比较尴尬的是,同为宁波人,郭巨却不讲“阿拉”,而讲“鹅拉”。也愈发显得郭巨有点格格不入。
因为这几个关键字的区别,常常让我觉得自己不是正宗宁波人。二三十年前,那时还是个孩子,打扮得清清爽爽去宁波城里白相(玩耍),不管行头多齐整,只要一开口吐出个“鹅”字,立马就露馅了,会招来某些城里人的鄙夷眼色,“原来是乡下头来的,下只角人。”
我倒也没觉得羞辱,或者生气,因为的确是大山里的孩子,不管走多远,我的根永远在乡下,在山里,在“鹅”们游弋的池塘间。
后来外出读书,班级里不少同学来自大碶、新碶、小港,开口即“阿拉”,都是正宗的“阿拉人”。他们辅导我打球,也辅导我学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我的发音,硬要我把“鹅拉”变成“阿拉”;把我那边的“肉”,变成他们那边的“肉”;把我那边的“虾”,变成他们那边的“虾”;把我那边的“泥猪”,变成他们那边的“鸟猪”。我卷着舌头说了几天,但一不留神,那只“鹅”就会跳出我的嘴巴。几天后,我彻底放弃,重新恢复我的“鹅”“肉”本色。
乡音是一个人身上最大的烙印。(www.zuozong.com)
毕业后上班了,当时那个单位里也有不少“阿拉人”。一次说话我用了个叫“贴创”的独门词语,他们显得很愕然,瞪大眼睛问我“贴创”是啥意思。我说是“如果”的意思。他们哈哈大笑,“那叫‘贴胖’,不叫‘贴创’。”后来,他们干脆就以“贴创”做我代号,见面不叫名字了,而叫我“贴创”。
还有个词语,也是柴郭地区独有,那就是对母亲的称谓“媪”。把母亲呼为媪,是古人叫法,《广雅疏证·卷六下·释亲》解释得很明确:“媪,母也。”此外,在《史记·赵世家》《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等史书里也都有明确记载。可见呼母为媪有着悠远的传承,柴郭地区的人不必以此为耻,柴郭以外的人也不必感觉惊讶。
媪,在郭巨土话里发音为“ou”,第四声。这个称呼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郭巨广泛流行,70年代后出生的人一般都叫“阿姆”“姆妈”,“媪”的叫法基本听不到了。原因在于,媪的发音与宁波话里“屙”(即屎)的读音接近,显得对母亲很不尊敬,所以这个叫法目前已被淘汰。
从前,郭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城,与外界互动流通不多。第一,可能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它处于宁波陆地最东端,要出来,得翻越好几座大山。第二,与它的定位有关。郭巨是一座城,一说到城,有些人会想到“围城”,所谓围城,就是城里的人想出来,但出不来,城外的想进去,但进不去。郭巨造城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让人们守住这座城。如何才能守住呢?只能寸步不离。所以它的土话自成体系,与原汁原味的宁波话就有了许多不同。
有个外地朋友曾经说起过:“郭巨话有点奇怪,初次来郭巨,听一小孩大叫‘哎呀’‘哎呀’,以为虐待儿童,转头一看,并无人打他。后来才明白‘哎呀’即爷爷的意思!”
说得我哈哈大笑。
我有不少跟我“出屁股长大”的同学,他们走出郭巨,走进北仑城区,在那里扎根定居,努力学说“阿拉话”,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阿拉人。追求改变应该不是件坏事。我也如此,所谓入乡随俗,有时跟人说话免不了带些“阿拉话”的色彩。只有回到了郭巨,不用再强迫自己说“阿拉话”,才觉得无须勉强、恢复本然真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