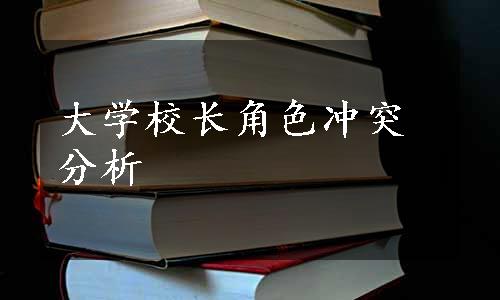
1.历史的反思
社会学家波普诺曾指出:“在每一次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互动中,社会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剧本’,用以指导分配给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同角色的扮演。”“当来自这些角色的要求出现对立时,置身于其中的个人就处于了一种角色冲突的状态中。”[23]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立足于教育发展的本质需求,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来协调大学、政府、社会等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角色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具有不同的行为要求,当这些行为要求产生各自的行为期待时,角色冲突时有发生。
民国时期的大学基本能分成三类,即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本文对教会大学不做研究。国立大学校长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其有义务按照政府的相关要求治理大学。虽然政府对大学的控制相对宽松,大学校长也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国立大学的校长毕竟从属于一定政治体制,他们有理由更有责任维护彼时的政治体制,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而且,这些大学校长为此能够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就私立大学校长来说,他们与政府的牵涉相对很少,但是他们又何尝逃得出政治控制的樊篱呢?胡适在中国公学不得已辞职不就是一种鲜明的体现。所以,很多私立大学校长为了长期、顺利地执掌大学,也不得不进行政治附和。然而,大学校长毕竟有其本职工作,管理大学日常事务、树立大学正确的发展目标、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完善管理体系等,这些需要建立在对大学的本质有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这种政治上的维护、靠拢乃至依附与学术的独立、自由必然会产生矛盾与冲突。
如前文所述,从民国大学校长的学术情况、高等教育经历、学位获得情况等方面来看,他们均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卓越的学术声誉。学者是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主要扮演的角色之一,否则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声望。作为学者,他们秉持对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将学术研究视为其本职工作。然而,作为执掌一所大学的校长,他们需要面对大量的行政事务,行使其管理职能,这必然会对其学术工作造成一定影响。而同时从管理者与学者两种角色的行为要求来看,这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政隶属关系,这是一种基于不平等而建立的关系,而不平等必然会带来冲突。作为管理者,其希望拥有对被管理者进行控制与支配的权力,而在实际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管理者的确拥有或多或少的支配与控制权力。而当管理者追求对学者的支配与控制权力时,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这组角色的冲突之中。例如,蒋梦麟在任职北京大学校长之前能够很好地秉持“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原则,然而他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提出的“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 的原则更加强调大学校长作为管理者对学术研究者的支配与控制。就此,可以从彼时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书信中得以体现。周鲠生在给胡适的书信中言及:“你离开国内学校生活多年,绝不能想到这几年大学制度变到这步田地!我们在北大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现在呢,学校已经衙门化,校长简直是待同属吏。” [24]
2.现实的思考(www.zuozong.com)
由于政治、经济、学术具有各自的“游戏规则”,三种游戏规则之间本身各不相同,而当今大学校长身处于这三种角色之中,必然会产生角色的冲突。首先,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同存状态给大学校长带来比较明显的冲击,从思想到行动,从价值观到人生规划,都发生极大的转变,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一方面,大学校长需要按照上级指示办事从而形成的“被动型”性格,另一方面大学校长又需要具备积极发挥能动性广开财路的“主动型”精神;一方面处于政治系统之下而对钱的热情并没有十分强烈,另一方面,为了学校利益的最大化而需要十分重视经济利益。[25]如今,这种角色的扮演与冲突已经从观念上转变为行为中,这可以从国家的教育政策规划之中得以体现,如国家倡导学校要改善办学条件,增加教学、科研中的基本建设,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办学效益等。然而,大学校长也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条件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完善乃至教授的聘任等都需要钱,而这些钱又从哪里来呢?挂着“985”“211”头衔的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在政府的财政划拨方面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不管如何,所谓不同类型的大学都需要向前发展,执掌不同类型大学的校长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政治人与经济人之间的种种冲突。
大学呈现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具有松散连接特征的文化组织。学科是大学的组成单元,大学是学科利益的联邦,这一组织架构使得大学权力基础本身明显缺乏强制性,它直接制约着校长权力对大学组织的实际渗透。[26]因此,大学校长虽然能够以其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在大学内产生一定的主导作用,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给校长的种种任务,如若违反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违背大学的本质,校长在政治人与知识人之间便会陷入尴尬的地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校长的行为指向和活动规律受利益支配,把经济利益作为行动需要的重要价值判断基础。这种行为无可厚非,毕竟生均经费不断增减,大学的运营成本日益增长,而面对大学经费的日益短缺与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颇为显著的矛盾,大学校长不得不对经济数字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毕竟,接受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需要利用大学提供给他们的逐渐紧缩的财政资助获得显现的与隐现的诸多支持,从而提高在职业分配阶梯上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位置。当然,大学校长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受教育者的“输出”问题,其他同样紧迫而且较为典型的需要财力支持的如人员经费、教学经费、基建经费等,哪一样活动的落脚点不是“钱” 呢。但是,当大学校长转身于学术建设中时,知识人的理念使得大学校长需要投入更多的教育情怀。他们以学术为志业,积极追寻学术的普遍价值。坚定的学术信念和学术理想使他们不会因为外部事物的掺杂以及外部力量的冲击而左右摇摆,更不至于陷入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而无法自拔。他们需要铸造大学的精神,培养大学的文化,最终实现大学的卓越。由此来看,经济人与知识人的两种思维路径与行为方式会让大学校长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冲突 不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