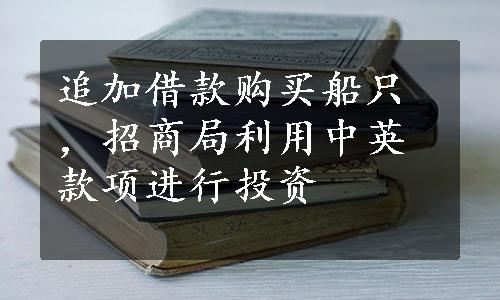
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看法:一是更新船只对于当时招商局的发展非常重要,而招商局自身又因为负债过重而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更新;二是国民政府当时没有足够强的动机与财政余力去帮助招商局进行船只的更新。在这样的背景下,招商局1933年利用中英庚款进行购买船只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关于中英庚款的来由,大体上源于1926年英国国会通过的退还庚款案。后来,英国于1931年比照美国的做法,成立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所不同的是,英国所退庚款叙明要用在建设事业上,以退还的庚款作为基金,通过借贷的方式提供建设经费,尔后将事业所得利息投入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事业。此外,还要求必须在伦敦设立一个购料委员会,凡铁路及其他生产事业借用资金,需购外洋器材者,则需交购料委员会在英国购买。因此,虽能有一部分资金拨补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但大多数的经费仍被作为拓展英国在华市场、开展英国工商规模之用。[16]
这些存在伦敦的庚款,总量约200万英镑,年息2厘。其分配标准,为2 /3铁道,1 /3水利。但因为须向英国购料,故水利名下的60万英镑,一直无法取用,必须“转借给国内需要英国材料之事业,方得变为现款”。而转借给招商局添购新轮,“俟该局将来偿还现款,即可举办水利事业”。所以,在时人看来,这项贷款的成立,“实为一举两得之事”。[17]
1933年5月,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中英庚款的水利部分,除导准外,所有存于伦敦不能动用之款,计36万英镑,借给招商局用于添置新轮。后刘鸿生以还需购置江轮6艘,尚不敷用为由,要求追加借款。所追加的4万英镑,于7月1日在中英庚款委员会议决通过。故实际借款400200镑,其中用于元、亨、利、贞四轮的费用为 349838.4542 镑(C.I.F.),按付款日汇率折国币5134128.37元。[18]
7月,刘鸿生与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曾镕浦等人进行了密切的函件往来,讨论的主要事项是关于用庚款购置海轮及江轮的料单事宜,以用于英国10月的造船招标。从函件看,这一料单的准备工作是较为仓促的,“虽漏夜工作”,“恐非三五日内可能竣事”。[19]而行事仓促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笔造船庚款借款的到来并没有在招商局的意料之中。8月,草签合同,规定所借钱款,完全用于在英订造海轮及江轮购买材料运华造船之用。并以所购或所造轮船的各宗收入为还本付息担保,年利5厘,由1935年7月1日前利息一次清付,7月1日后利息半年为一期,共分20期,限10年偿还。[20]
为了监督轮船的营造,招商局于是委派工程师伍大名和Scurr船长前往英国。四轮分建于两地,其中海元和海利在New Castle的Swan,Hunter &Wigham Richardson Ltd.Neptune Yard建造;海亨、海贞在Glasgow的Bareloy Curle &Co.Ltd.North British Engine Works建造。[21]
在随后约一年的督造过程中,除了官方的报告往来之外,在英国的伍大名和Scurr船长与在上海的刘鸿生之间还进行了频繁的私函往来,就造船的事宜汇报、商议并讨论解决方案。下面首先简单介绍这两位在英国的招商局负责人。
伍大名(T.M.Wu,1892—?),别号亮功,广东新会人,1909年广东黄埔水师学堂第十二期学生,1910年毕业。学习期间被选出,随同筹办海军大臣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前往英国,并留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舰船制造。1915年奉调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学习造船,1917年回国后被派往上海江南造船所,任至高级工程师。1933年8月,交通部聘其专办招商局新船设计事宜,[22]10月被交通部委派为交通部船员检定委员会第一次船员考验委员,随后赴英负责海元等四轮的督造工作。赴英前,伍大名的职务是交通部的一名科长。需要提到的是,伍大名还曾于1935年1月24日代替许建廷接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当时是隶属于交通部的一所航运学校,与招商局关系密切。
关于在英国督造船只的另外一个人物Capt.Scurr,在已有的关于刘鸿生招商局改组活动中所广泛引用的一条刘鸿生知人善用的材料中,大多会提到刘鸿生任用Acurr船长一条,追溯起来,这一说法来自刘鸿生四子刘念智的一段回忆:“一九三三年夏,宋子文拨出一部分由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给招商局,由我父亲派伍大名、刘××和技术顾问Capt.Acurr到英国订购了三千吨级的客货轮四艘,取名海元、海亨、海利、海贞,增辟了上海至青岛、天津和上海至厦门……”[23]但在刘鸿生招商局期间的刘鸿记账房档案中,并没有看到Acurr船长的记载,而Scurr船长则频繁出现。因此,笔者推测,很大的可能是刘念智的记述有误,误将Scurr船长写作Acurr船长,并导致后来的转引中以讹传讹。但是,档案中看不到Scurr船长更为详细的背景资料。
从1933—1934年刘鸿生与伍大名等人购船过程中的通信来看,伍大名除了表现出对招商局利益的维护,同时也体现出对中英庚款委员会专断做法的不满;刘鸿生则呈现出务实与变通的态度,行事作风极为目标导向。而在刘、伍等人口中的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英国方面,则更多地表现出对全局的掌控力及强硬立场。
这些态度与立场集中地体现在购船过程中的两个事件上:一是对四船的承建商招标的争议;二是对已经建成的海轮移交方式的争议。下面分别叙述之:
(一) 造船商招标的争议
我们先来看对这一事件的往来函件:
1.伍大名和Scurr船长致刘鸿生(1934年1月1日)[24]
尽管事先我们已经从中国发电报告知庚款委员会我们的到来,并且要求其推迟招标行动,等我们到英国之后再说。但看起来,庚款委员会的英国方面早在他们刚一收到购船计划和相关技术规格要求之后,就把相关资料交给了他们的顾问Sir John Biles公司,并即刻着手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推进这项工作。1933年11月10日,他们就已经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此次招标信息。而后,庚款委员会实际上已经将轮船的长度定为340英尺,并于12月12日就已经将它公诸众。
正如您将从我们的官方报告中所看到的,我们已经向庚款委员会提出质疑,质疑其为什么要这么快就做出决定,而不是等到收到至少三至四家竞标公司的标书后,审查其声誉是否良好,是否有能力按指定尺寸造船,是否有能力在装货量、速度和其他方面达到我们的要求之后,再作决定。
英国方面的态度表明,由于庚款委员会大多由商人构成,而这些商人多忙于自己的生意而顾不上庚款委员会事务,因此,他们把大部分的决策权交给了顾问Sir John Biles公司。对于这一点,如果造船合同中,有关我方的利益(我们正在审查合同中的有关条款与安排)得到了应有的考虑,我们当然没有意见。我们毫不怀疑庚款委员会及其顾问们的行动方向,正在努力确保招商局所要建的轮船将会是由著名船商操刀,品质一流。但是我们认为,可能由于委员会开展业务的方式,显得操之过急。在我们到达英国之前,事情不应该进展到签署合同这一步。这里有必要强调,我们最初发给他们的情况说明里包含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条款,要求其提供必要条件,使船舶建造委托方代表和建造商之间可以就建造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并且我们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进行细节磋商。很明显,这些磋商应该在合同决定之前进行,而不是等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再来做……
出乎我们意料的一点是,我们发现庚款委员会顾问的工资竟然是从招商局贷款中支出的,这些费用总数达新轮船合同价款的2%。我们认为,这种付款方式有失公平。像庚款委员会这样的专门机构,理应常年聘请技术顾问,顾问的工资显然应从委员会的公共基金中支付,而不应从我们这样的单笔贷款中开销。
2.伍大名和Scurr船长致刘鸿生(1934年2月28日)[25]
正如您所意识到的,我们发现这里的形势十分严峻(extremely difficult),并且我们与庚款委员会以及他们顾问之间的沟通,极需(vitally necessary)手腕与耐心。很多面对面的商谈,包括最近的一次,都令人非常不快(distinctly unpleasant)。虽然目前情况似有缓解的迹象。在我们极力去争取招商局利益的时候,我们也很庆幸背后能有您的支持。
总体来说,我们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轮船将按照招商局最初要求的规格进行实际建造。尽管这一目的达成了,但在签订正式合同之前,我们与庚款委员会就谈判的方式而言,仍是存在分歧的。就造船来说,相关的两家公司直到把合同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接到通知,目前,相关的文件还没有签署。另外,由于不了解中国沿海海事服务的具体要求,细节调整一改再改,并且由于在我们到达英国之前,庚款委员会对此事的处置过于草率,使得我们在这里浪费了至少1个月的时间。
我们今天已经得到口头通知,将与两家造船商签订合同,但愿不会再出现进一步的纠纷。我们急于看到新轮船的交付,也希望能够尽早回到上海,以免增加招商局额外的费用开支。
3.刘鸿生致伍大名和Scurr船长(1934年4月3日)[26](www.zuozong.com)
我已经收到你们2月28日发出的私函,从中我十分遗憾地了解到你们与委员会和顾问在沟通中所遭遇的困难。整个顾问委员会向并不了解中国沿海情形的顾问去听取建议,并且没有给予我方代表应有的重视,这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我十分感谢你们会坚定地维护招商局的利益。我也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和庚款委员会以及他们的顾问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和谐和密切,并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
4.刘鸿生致伍大名和Scurr船长(1934年5月1日)[27]
根据庚款委员会过去的一贯态度,我估计如果我方不作一定的努力,这样的愿望与要求就无法实现。因此为防万一,你如果发现你与庚款委员会及造船方的谈判进展不顺的话,请及时通知我,我会尽力调动各方资源,从中斡旋,以求达到我方目标。
从这4封函件中,不难看出,对于整个借款、造船、招标的过程,英国的庚款委员会及其顾问委员会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违背招商局的意愿,按自己的节奏进行船只的招标和合同的签订。对此,伍大名和Scurr则充分注意到了营造船只的技术细节和时间安排,关注的焦点较多放在合同的技术层面。而在伍大名要求英方对造船合同按事先约定,在造船程序和船只规格上作调整的要求,英国最终进行更正并作调整的结果看,伍大名等人的商谈是有效果的。同时,伍大名还尽可能地与上海的刘鸿生保持联系,以求获得必要的支持。而刘鸿生尽管十分清楚英国庚款委员会的姿态与立场,但仍然叮嘱伍大名与其搞好关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显然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二) 是否由中国船员驾驶新船返回上海的争议
1934年4月,招商局决定加派一支由两名船长、两名首席工程师和两名工程师构成的团队去英国学习与增援工作,增派人员均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挑选产生,费用则由招商局自己承担。除了学习与锻炼本国船员,刘鸿生的另一层意思是希望可以由这些船员驾驶新船返回上海,在实地操作中锻炼提高,熟悉新船,进而改变当时招商局的船长大量依赖外籍人士的状态。
1.刘鸿生致伍大名和Scurr船长(1934年5月1日)[28]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新轮船能由我们自己的船长驶回中国,这对招商局未来海洋事务的发展将十分有利。我很重视此事,并且希望你们能排除万难,加以实现。
8月份派到英国的船长中有一位马船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长期担任诸多海轮的船长。我希望你们能会同庚款委员会努力磋商,争取安排其中一艘新轮船由他驾驶回国。
2.刘鸿生致伍大名和Scurr船长(1934年6月29日)[29]
我非常想知道(very anxious)是否你们与庚款委员会以及营造商们,在关于新轮由中国船员驾驶回上海的沟通是否顺利。由于此事十分重要(of great importance),我希望您能够排除万难,努力达成目标。
3.伍大名和Scurr船长致刘鸿生(1934年6月19日)[30]
因此,虽然庚款委员会并不反对由招商局自己的员工来交付新船,驶回上海,但强调所有与交付相关的费用均需由招商局自己来负担。您手上的文件已经表明,建造商们所估计的轮船交付费用约为每艘3810英镑到5800英镑。庚款合同规定,这笔钱可以付给分包商,但是在把船交到他们手上之前,会发生各种费用,诸如码头费等等。而如果由建造商自己来交付的话,那么这笔钱就会由建造商来付。如果由招商局用自己的职员来交付船只的话,那么这些钱,包括船只在中国的注册费都必须由招商局来承担。如果这样操作的话,造船商可以省下一笔钱,因为这些交付的费用,庚款委员会事先已经作了扣除,即便招商局自己派人把船开回上海,所省下的钱招商局也拿不到。除了上述费用,招商局还要支付航行到中国途中的保险费。因此,算下来,我们估计一艘新船的全部交付费用至少要7000英镑。
4.刘鸿生致伍大名和Scurr船长(1934年7月25日)[31]
我已经收到你们6月19日的私函,得知我们让招商局自己的船员交付新轮船的计划,由于各方面的阻碍而流产,对此我非常失望。但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且事关巨大的费用安排,情势不由人,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尽人事而听天命。
显然,委派中国船员驾驶新轮返回上海的设想是刘鸿生期待已久的事,但招商局艰难的财务状况,庚款委员会在合同规定中占据的主动地位,使得这一设想无法实现,而伍大名与Scurr虽然作出种种努力,最终也不得不抱憾面对现实,当然,出于财务考虑而另择他法,也是一种更务实的姿态。
不过对于一年多的营造努力,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1934年10月8日,伍大名和Scurr从纽卡斯尔致刘鸿生的函件里写道:
我们所建造的这几艘船即便在英国的航运圈里,也属于公认的上乘的轮船。相信这几艘船在有序交接之后,能够良好运转。它们的速度、装货量以及耗煤量等均已达到了我们之前的预期。希望这几艘船到达上海之后,其技术性能能够得到您的首肯。[32]
庚款营造的4艘海轮1934年下半年陆续驶回上海,引为盛事,而见诸大小报纸版面。有了这4艘新船,招商局的船只结构也得到了更新,不只是船龄,新船的航速、载货量和煤耗量表现均更为先进。从表4中可以看到,1934年新船加盟后,招商局轮船的船龄结构得到了优化,旧船退役停用,新船更新补入,总载重吨位则在上升。
表4 招商局自有船舶各船龄段载重及占比情况
说明:根据表2、表3、《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和《二十四年航业年鉴》(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编,1936年版)整理得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