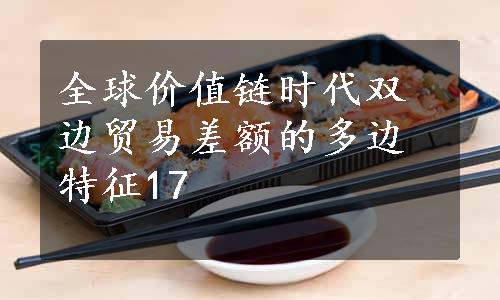
媒体在讨论美国贸易逆差时往往集中在总体赤字上。美国在制造业产品方面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但在农产品和服务方面却有贸易顺差(见图1.23)。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制造业产品贸易逆差急剧增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该数字加速增长,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间进一步扩大。

图1.23 美国几大经济部门的全球贸易差额(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可从网址https://www.bea.gov/在线获得。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对华制造业贸易逆差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其他工业化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向中国转移生产设施(表1.3报告了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在1990年至2017年间对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的贡献比例)。例如,在1990年,美国全球制成品贸易逆差的75%左右来自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但到2017年,其份额已下降到不足12%。同期,中国在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中的份额,从10%大幅增加至2013年的73%左右,此后一直在下降。换言之,随着中国成为日益重要的制成品来源,其他工业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见表1.3的最后一列),因为这些经济体中的许多企业,正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向中国转移其制造和组装设施。按所有权分类的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证实,尽管中国私营企业(PRI)近年来已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但中国与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外商独资企业(FIE)和合资企业(JOV)18。
与中国一样,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墨西哥和东盟国家,在过去二十年中也日益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其在美国制造业全球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也已提高(见表1.3)。这表明,在过去二十年中,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美国与中国制成品双边贸易逆差日益增长的基本驱动力之一。
表1.3 美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制成品贸易逆差比重 单位:%

续表

注:东盟九国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柬埔寨、缅甸和老挝。新加坡包含在“亚洲四小龙”中。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OECD)按行业和最终使用分类的双边货物贸易(BTDI*E),ISIC,Rev.4,可在线获取: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BTDIXE_I4。
为了研究全球价值链在美国制造业产品贸易逆差的转移中所起的作用,本节使用Koopman等(2014)提出的总贸易核算方法(详情参见专栏1.3),分析了美国赤字最大的三条贸易路线的增加值结构,即美国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贸易。
专栏1.3
辨识和测度双边贸易中的第三国效应
Koopman、Wang和Wei提供了一个综合的数理框架,用以追踪增加值并识别总贸易流量中的重复计算部分(KWW,2014)。一个国家的总出口可以分解为四个概念上不同的组成部分:(1)最终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即Johnson和Noguera(2012)提到的增加值出口(VAX);(2)出口(作为中间出口)后返回国内(RDV)的国内增加值;(3)用于出口生产的外国增加值(FVA);(4)由于中间贸易来回跨境而产生的被重复计算的增加值(PDC)。KWW进一步表明,出口总额中的这些组成部分,都与GDP统计数据具有特定类型的关系:VAX是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满足国外需求的部分,在这一类别下,总出口中所体现的相应要素成分至少跨境一次;RDV不是本国增加值出口的一部分,但却是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最后作为该国的最终需求,在国内被吸收,在这一过程中,国内要素成分至少跨境两次;FVA是其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出口中所包含的,同样也至少跨境两次的那部分要素成分;PDC未被计入任何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因其中的要素成分,已至少被上述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计入,并且跨境至少三次,但每个国家的海关在总贸易统计中都有记录。
通过辨识贸易总额中的哪些部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被重复计算,KWW方法提供了一种用增加值(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正确解释贸易数据的方法。基于国民账户体系标准(SNA),该方法还将总贸易统计和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两种现今最重要且最常用的经济统计)联系起来。Wang、Wei和Zhu(2014)将KWW的核算框架扩展到双边、部门和双边部门层面的贸易,并提供了一个效仿KWW(2014)的方法,且在不同加总层面上具有一致性的核算框架。通过将这四个大组成部分分解成更细的小项,第三国在双边贸易中所产生的作用可被清楚地确定和衡量,如表1.4所示。
表1.4 双边贸易总额的分解,以确定和衡量第三国在双边贸易中所起的作用(www.zuozong.com)

对双边贸易的详细分解表明,第三国在双边贸易中的作用可以通过上述8个细分的组成部分中的3个(蓝色字体)来衡量:DVA_IND、OVA和ODC。DAV_IND与总贸易的比率,可用于衡量贸易伙伴国家作为本国价值增值被第三国吸收的转移平台的重要性。该比率由本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共同生产安排以及第三国的最终需求决定。同样,OVA与总贸易的比率可用于衡量第三国要素成分对本国出口生产的重要性。这一比率由伙伴国的最终需求以及本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共同生产安排决定。最后,ODC与总贸易的比率可用于衡量第三国效应的复杂性。该比率由本国、伙伴国和第三国的生产安排决定。ODC仅指跨越国界至少三次的中间投入(企业使用来自一个国家的中间投入,在另一个国家生产用于出口到第三国的中间投入,该共同生产活动涉及至少三个国家)。
作为例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美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OECD-ICIO C30、32和33)净进口的增加值结构,分解结果见表1.5。第(1)栏为百万美元为单位的出口总值(以当前价格计)。第(2)栏为与这些总贸易流相关的增加值出口(VAX_G)。接下来的几栏报告了出口总额的主要组成部分:最终由伙伴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2a)DVA_DIR];最终由第三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2b)DVA_IND],这取决于第三国的最终需求;包含在出口中,但最终返回国内并在国内被消费的增加值[列(3)RDV_G],这是本国GDP和最终需求的一部分;双边贸易伙伴之间的循环效应[列(4)和列(5)的DDC和MC],总出口中第三国增加值[列(6)OVA]和源自第三国的纯重复计算[列(7)ODC]。
表1.5 中美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贸易分解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2018版OECD-ICIO表计算而得的UIBE GVC指数。
该分解结果不仅揭示了自总贸易统计计算而得的贸易差额所具有的误导性,而且还揭示了这种统计假象的来源。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出口增加值(VAX_G)仅占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总额的25%。此后该份额增加,但2014年仍然低于50%。在整个样本期间,来自第三国的出口增加值一直占中国这些商品出口的50%以上。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构成恰恰相反,因为在整个样本期间,VAX_G的份额一直占主导地位(65%~75%)。来自第三国的增加值成分(OVA + ODC)仅占美国这些商品总出口的不到20%,且该比例在2014年下降到仅8%左右。MC + OVA + ODC占中国出口的最大份额,中国利用美国和第三国的上游投入来生产出口产品;DVA_IND + RDV + DDC是美国出口的最大部分,该部分是中国进口的美国产品,并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中国对美国和第三国市场的出口。因此,中美双边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总贸易流中的第三国增加值。2000年,第三国占贸易失衡总额的80.3%,该数字在2014年降至53.1%。
国际和劳动经济学家经常使用双边贸易差额(净进口)来衡量进口渗透以及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当传统(最终商品)贸易主导国际贸易流量时,净进口足以准确反映盈余国向赤字国输出的要素成分。然而,当全球贸易由全球价值链主导时,贸易平衡总额不再是衡量进口渗透的可靠指标。如表1.5下端的数据所示,美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的净进口仅包含很小一部分的中国要素成分。2000年,中国的增加值(要素成分)仅占美国从中国净进口总量的7.5%。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该比例迅速增长,2007年达到30.8%,2014年达到41.1%。
中美出口增加值结构的差异反映了两国企业在这部门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凭借高端设计和整合能力,美国跨国公司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领先企业,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首要和中心位置。相比之下,中国企业自1992年放宽对外投资管制以来,才开始加入全球价值链,承担加工和装配任务,因此国内增加值与出口总额之比非常低;很大一部分价值来自国外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200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中的98.7%是加工贸易出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开始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移动。更多中国企业升级为一般贸易,而加工贸易的比重则有下降(从2007年的87.3%降至2014年的77.4%)。
美国从中国净进口的这种增加值结构并不少见。通过美国从德国、日本和许多其他贸易伙伴的净进口中,也可以观察到第三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图1.24显示了美国从德国的总净进口的增加值结构。与美国从德国进口(DVA_IND取决于第三国的最终需求)然后又再出口的比例相比,向德国出口的美国中间产品中的更大一部分,被再出口到第三国。因此在“再出口”部分中,美国实际上在增加值方面对德国实现了大量盈余,特别是在服务业方面。与美国从中国的净进口相比,美国从德国的净进口,包含了高得多的德国要素成分(约80%),但第三国供应商也占40%左右(第三国的最终需求占比为−20%,这意味着德国从美国的进口,更多地取决于第三国对使用美国中间投入的德国产品的最终需求)。这些都表明了净贸易总流量中涉及的复杂构成和抵消因素。
为了进一步说明第三国在不同双边贸易路线中的不同作用,图1.25比较了若干组双边贸易路线增加值结构的变化,即:美国从中国净进口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美国从德国净进口的运输和储存服务,以及美国分别从德国和日本净进口的汽车。

图1.24 美国从德国净进口的增加值结构
注:变量定义请查阅专栏1.3。
资料来源:根据2017版OECD-ICIO表计算而得的UIBE GVC指数。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对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的净进口量迅速增长,从2001年不到美国该部门10%的增加值(110亿美元)(图1.25左上图,刻度在右侧),到2014年的超过60%(1 410亿美元)。其中,来自第三国的要素成分在这一显著增长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远高于50%)。这反映了其他国家将中国作为装配枢纽,将其国内增加值再出口,以满足美国的最终需求。同样,第三国(主要是附近的欧洲经济体)对德国商品的需求,是美国向德国运输和储存服务净出口增长的推动力(图1.25左下图)。
从1995年到2014年,第三国的生产极大影响了美国与德国和日本的汽车贸易赤字。美国从德国净进口中的相当一部分(2014年超过美国净进口的四分之一)包含了来自第三国,主要是东部欧盟国家和中国的要素成分,而第三国的最终需求仅占该时期美国净进口量的5%左右(图1.25右下图)。在该时期的末期,第三国要素成分供应和第三国最终需求,在美国从日本净进口的汽车中的重要性有所增加,但仍低于德国。
这一分析表明,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总贸易流中包含的要素成分和最终需求的来源,在不同国家、不同产品的不同贸易路线之间差异甚大时,双边净进口不再是衡量贸易对伙伴国国内物价和工资影响的可靠指标。这也意味着双边贸易政策的任何变化可能对第三国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处理双边贸易问题时不容忽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