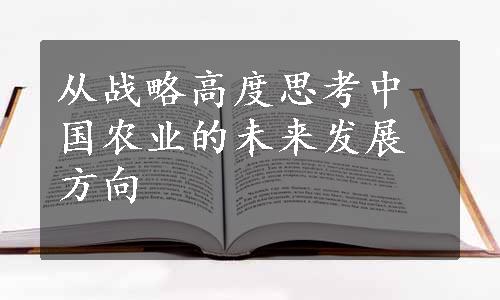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建立战时的经济体制,国民党政府对其经济领导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10]迁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1月1日根据颁布的《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将原有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全部划归经济部。翁文灏出任部长,钱天鹤则担任该部下辖的农业司长。这一职务也标志着钱天鹤人生旅程第二阶段的开始——由一位学有专长的农学家转为中央层级的农业行政主管官员。1940年7月,钱天鹤就任新设置的农林部常务次长一职直至1947年6月卸任。由于这一时期担任农林部长的陈济棠等人为行伍出身,身为常务次长的钱天鹤负有更多责任为战时中国农业发展及战后复员而殚精竭虑,这也给了钱天鹤从战略高度思考中国农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机会,《文集》中因此留下不少这方面的思考。
作为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海归学者,钱天鹤的观照视野较为开阔,他从世界历史的高度阐述农业与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后者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次第展开,而农业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来自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浸润,突出表现在“农具之改良”“新种之输入及传布”“农学之进步”“农田面积及售货量之增加”和“农民地位之增进”,这些因素又反过来推动了西方农业的现代化进程。钱天鹤在此看到的是西方农业在近代工业化大潮下实现了质的“蜕变”——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这一趋势在他看来不应独为西方国家所拥有,它也指明了古老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但当时的中国农业状况无法令钱天鹤感到乐观。
钱天鹤秉持科学家的真知灼见痛陈中国农业现况着实堪忧,并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棘手问题。首先是农民户口与耕地分配之间的矛盾。“此60年中(1873—1933)全国人口既增加如此之巨,而耕地面积几乎保持原状,故农民生活,异常困难;历年祸乱,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11],“故欲建设农业,必须注意人口问题,一切设施务宜顾到如何安置过剩之人口”[12]。如今看来,钱天鹤此番痛陈已经点出人口增长过快不仅将导致人地关系紧张,而且也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大要因,这一观点较之日后马寅初所提出的“新人口论”早了数十年时间。其次,农民的耕地面积既然如此之少,中国粮食供应也就很难自给,这影响到农民的基本生存和社会稳定。上述两方面问题的叠加使得中国农民生活于极端困苦之中,“全国食量,既属不敷,又加之天灾人祸,连年不绝”[13],中国农民不可谓不勤劳,但他们却又在这个国家中处于极度弱势的境地。(www.zuozong.com)
钱天鹤将目光投向了农业增产,试图通过增产来改善农民生活、提升中国农业水平,对于农业增产的重视在钱天鹤担任农林部常务次长后面几年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一时期也正值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大批军民迁至云南、四川和贵州。根据1943年《国民政府年鉴》的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43年间,后方各省共收容难民高达10 286 642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公教人员和学生、工人在内。[14]张嘉璈的估计更高,“到1940年,沿海各省逃往大后方的人民,从一亿八千万增到二亿三千万人”[15]。因此,解决大后方的粮食供应问题便成为中国抗战能否坚持下去的重要支撑。无疑,基于已有条件,努力提高粮食产量是当务之急。钱天鹤的增产建议得到了国民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并推广实施,1942年,水稻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分别由上一年的2 164.9万亩、1 261万亩增至2 553.2万亩、1 529万亩。主要粮棉作物的增产有力确保了抗战期间大后方军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巩固了抗战大局,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这也说明了钱天鹤的对策务实而高效,正中要害!
来自政府的扶持还仅仅是其中一面,粮食增产必须运用现代农业科技手段方能达成,这又涉及农学教育问题,“扩充农业教育,训练农业人材,实为当务之急,而训练成绩能否优良,尤为农业生产兴衰之所系”[16]。钱天鹤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科学农业,“总之农业问题,即科学问题,解决农业问题,非从科学入手不可”[17],而传统中国将农业视为一门经验性技术已然落后于时代发展,“我国旧有的农业技术,并非不优良,但只是局部的,非整个的”[18]。就此而言,钱天鹤的好友、同为著名农学家的沈宗瀚也有着类似论述:“四千年来中国农业,皆由于累积的经验而缓慢进展。至民国十年以后,科学农业始渐萌芽。”[19]相比于梁漱溟、晏阳初,钱、沈和另一位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可谓民国时期科学农学主张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个人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以科学兴农、发展农业生产为第一要务,这是否也契合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发展“铁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