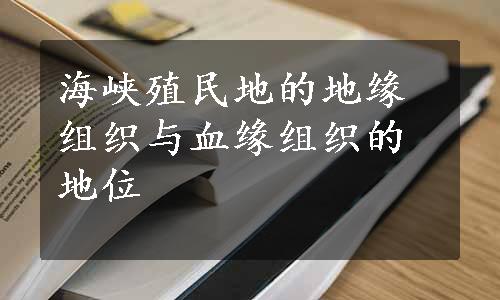
与荷属东印度情况不太一样的是,海峡殖民地的地缘组织(有些学者称之为方言组织)与血缘组织(或称为宗族组织)的地位似乎比半官方的华人甲必丹更为突出。据史料分析,闽粤移民的地缘组织比血缘组织出现得更早更普遍,以地缘组织为表征的地方色彩,甚至构成以后华侨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明清时期,尤其是17世纪以后,侨居海峡殖民地的闽粤华侨,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方言及业缘上的相同,培养了他们之间地域性的认同感。在侨居地,来自闽粤各地的华侨为了安全、娱乐和经济上、生活上的互助,操同一方言者便很自然地、和谐地聚集在一起。这就为海峡殖民地以及荷属东印度华侨早期的地缘组织——方言组织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而最早维系地缘关系的纽带,应属寺庙组织。来自同一方言群的华侨,从移民的开始就把故乡的神灵带在身边,以祈求海上航行一路平安。到了蛮夷陌邦后,移民们还需要家乡带来的神灵保佑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安全、生意顺利。因此,每到一地,只要经济条件许可,筹建寺庙、为自己的保护神寻找一个安身的“场所”便成了华侨社会的一件大事。这些寺庙既是同乡间共求故土神灵庇护之处,也是他们交换信息、互助联谊之所,有的寺庙还设有墓地,兼理同乡的丧葬祭奠事宜。马六甲的第一座华人寺庙青云亭就是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建立的。该庙除了奉祀观音的宗教功能外,还具有其他四种功能:第一,供奉华侨先民的牌位,供当地华侨祭祀祖先神灵。第二,主持办理客死当地的华侨的丧葬祭奠,并附设义山(坟场)。第三,设立议事堂、慈善堂,排难解纷,消弭争端,救苦恤贫。第四,附设义学,招收华侨子弟入学,传授中华文化。[14]
虽然,这些寺庙的组织形式不能算作正式的民间社团,但它们的运作,还是显示了此后华侨社会地缘组织的一些基本功能。
地缘组织的建立和扩展,主要表现为同乡会馆——以中国原籍地为地域基础的自愿团体的兴盛。据估计,1801年成立的槟城嘉应会馆应是在海峡殖民地最早建立的一间华人方言会馆。在一般情况下,方言组织在购地或设立会所之前即已建立。
首家方言会馆创建4年后,另外两个组织相继诞生,它们是马六甲惠州会馆和槟城中山会馆。马六甲惠州会馆建于1805年,它是由一帮来自粤东南惠州府[15]十县的客家人创建的。其创始人是李振发。
同年,槟城中山会馆建立。[16](www.zuozong.com)
随着1819年新加坡殖民地的建立,1824年马六甲的控制权由荷兰转移到英国手中,以及1826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第四大辖区的海峡殖民地的建立,马六甲沿海三个英国殖民地在行政上合并,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华人前来这里定居。[17]
这20年中,在这些方言会馆中处于先导地位的是马六甲应和会馆,它是由嘉应客家人于1821年建立的。[18]它的建立表明,在19世纪初期,马六甲的客家人口在增长,人口的增加使他们更加意识到需要一个组织,以提供集会场所,料理那些不幸客死异域的乡亲的丧葬事宜。[19]
紧接马六甲应和会馆之后的,有1822年建立的槟城惠州会馆和新加坡宁阳会馆,1823年建立的星洲应和会馆,同一年建立的马六甲茶阳会馆,1828年建立的槟城南海会馆,1833年建立的槟城宁阳会馆,1838年建立的槟城顺德会馆和新加坡中山会馆,1839年建立的星洲福建公馆以及同年建立的星洲南顺会馆。[20]
从上述可以看出,早期海峡三地闽粤移民地缘组织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是,人口较少的团体,方言会馆反而最多,1801—1839年间,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的14个方言会馆中,有13个属于客家人和广府人,而他们是当地华人社会中的少数派。以新加坡为例,1848年,新加坡华人数量估计39700人,其中6000人是广府人(澳门),4000人是客家人,而其余以福建人为主,在福建人中又以闽南移民占多数。[21]上述现象显然是由极敏感的地缘组织之间的关系引起的。早期的海峡三地中,闽南人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经商而致富。同时,来自马六甲的闽南人,不仅构成了早期新加坡社会金融力量的中心,而且还谙熟英语,与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譬如,陈笃生,一个出生于马六甲的闽南华人(祖籍福建漳州)领袖,是一个与欧洲人有广泛联系的富商。他被总督巴特伍瑟任命为太平绅士,成为获得这一殊荣的第一个亚洲人。另一个闽南富商蔡沧浪,为庆贺自己44岁的生日,以豪华的席宴招待岛上所有有影响力的居民,其中就有许多欧洲人。[22]此外,海峡三地的甲必丹制度使华人社会中人口少的群体感到不安。殖民当局倾向于任命人数众多的华人方言群体的领袖担任甲必丹,由甲必丹负责维持华人社会的治安和管理福利事业,在法律上,他还有权逮捕并审讯华人。据记载,在早期的槟榔屿,一位名叫辜礼欢的福建漳州人,于1787年被弗兰西斯·莱特任命为首任华人甲必丹。[23]在早期的新加坡,另一位漳州人即上文提到的陈笃生也成了华侨社会事实上的甲必丹。[24]他们两人均属闽南帮,在上述两个殖民地中,该帮都是占优势的地缘群体。由于严重的方言隔阂,华人甲必丹没有渠道知晓其他华人的问题和不满,因而倾向于仅捍卫本集团的利益,而其他集团的成员觉得,他们没有得到甲必丹足够的保护,并且在关键时刻不能依赖甲必丹。只有能集中操同一方言的地缘组织——方言组织,才能达到维护本集团利益的重要目的。因此,人口及经济能力相对较弱的方言群体,就较积极地组建方言会馆,成立地缘组织。
综观南洋华侨社会,几乎所有的地缘组织,其最初成立所抱有的宗旨一般都是“联络感情、敦睦乡谊”“互助合作、发展自己”“共谋同人福利”“赞襄社会公益”“推广教育事业”“维护传统仪节、习惯”“沟通海内外声气”“为桑梓服务”等等。[25]地缘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也主要是为同乡新移民——“新客”安排住宿、介绍工作、为其他同乡迎生送死、安排宗教祭祀、恤贫扶弱、赈济家乡、调解纠纷、抵御外侮、与殖民当局交涉、开办学校、安排节日庆典等等。这些活动使地缘组织实际上成了各地籍移民社会或大或小的领导机构、联络机构、福利机构、教育机构、仲裁机构等,[26]充分发挥了地缘组织在华人社会中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我们可以从槟榔屿三都联络局章程中得到证实(参见附录二)。
地缘组织广泛而持久的基础是地缘认同,这种认同是海外移民对祖籍地以及这一地区人文景观(宗教、社会习俗、方言、业缘等)的归属意识。孙谦博士认为地缘组织有四个特征,即:区域性、亚市场性、礼俗性和内倾性。[27]孙博士认为,地缘认同的前提是地理共同体的存在。它包括自然地理和行政地理概念,还包括语言、风俗相同的人文地理,即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范畴。而存在,既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存在,也包括在历史上曾经共聚、在现实中却已经分散但在心理上依旧相连的虚拟存在。因此,地理共同体区域方位的有形与无形纽带界限分明,构成地缘认同的地理学特征。其次,是亚市场性(或者称之为业缘性)。地缘认同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基础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其性质,孙博士认为是非市场型的。而闽粤南洋移民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手工业和小商品经济,尤其是在早期的荷属东印度和海峡殖民地更是如此,其资金、商品、劳动力市场都不是西方经济学概念的完全的市场型,地缘关系在谋生过程和经济运作中意味着人缘、物缘、资金、信用、利润,它是地缘认同得以强化的催化剂,所表明的是地缘认同的经济学概念。第三,礼俗性。孙博士以为,地缘认同可以看作是一种秩序,认同地缘实际上参与了地缘组织的秩序。而地缘秩序与社会秩序不同的是,后者依靠体现社会主导价值的法制维持,前者则依照约定俗成的流传下来的习俗和习惯维持。地缘群体在自身长期的活动中发展出整套的礼俗规范,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形态与各地的民间文化,具体有孝亲、睦邻、义气、地方宗教、勤劳、节俭、扶贫济弱、守望相助等等,[28]它们实际上强化了地缘群体的秩序,调节着群体成员的关系,成员也根据礼俗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可见,礼俗是地缘认同得以维持的调节器,所表明的是地缘认同的社会学特征。第四,内倾性或者称之为内聚性。孙博士进而以为,方言群体或称为地缘群体居住地的相对集中性,经济活动的自给性,学校教育的方言性,文化活动的地方性,导致了其思维方式的内倾性。长期的内求趋势,造成地缘群体与外部没有多少常规性联系,没有经济、文化、人际的广泛交往,有时反而酿成冲突,阻碍外部经济力量与信理力量的渗入,从而阻碍了群体的自我更新,甚至造成群体成员心理、性格、习惯上的守旧。显然,这种思维方式的内求是地缘认同的思想基础,反映出地缘认同的心理学特征。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方言群的这一特性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不同方言群华人之间的交流较之以往也会增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