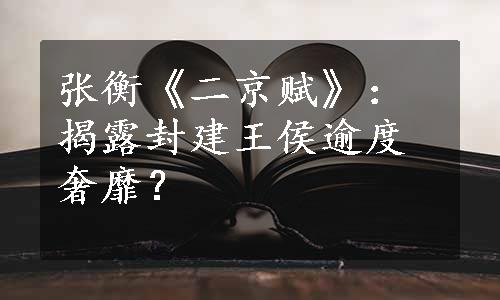
学习《张衡传》时,大部分学生对张衡所作的《二京赋》讽谏的对象,理解为“自王侯以下逾侈”之人,他们是根据上文语境来揣测的。原文为“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从上文来看,讽谏的对象应该是“自王侯以下逾侈”之人,他们的推测没错。而有个学生则认为是“皇帝”,缘由是初中所学《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讽”字,“讽”是“用含蓄的话暗示或劝告”的意思,既然张衡对当时奢侈的社会风气进行批评,那为什么不直言不讳,非得含蓄劝告呢?显然,有隐讳,古代臣子伴君如伴虎,讽的对象应该是皇帝。学生话音刚落,全班便一片哗然。既然学生有不同见解,就不能忽视,就要解决问题。查阅了教参,上面这样翻译:用它来(向朝廷)(此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讽喻规劝。教学参考书认为讽谏的对象应该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
那么,张衡作《二京赋》,到底想讽谏谁?
笔者听了一堂省级优质课,老师讲《阿房宫赋》,整堂课以“赋”的“铺采摛文”为切入点展开。杜牧尽其所能铺叙阿房宫的美轮美奂、秦始皇的骄奢淫靡,是为揭示秦灭亡的原因并警示当朝皇帝的。受这节课的启发,我感到:要解决《张衡传》中的问题,须从“赋”入手,因为张衡讽谏的凭借——《二京赋》——便是一篇赋。有了这个意识,去书店就会格外留意。一次,在书店偶然碰见了龚克昌所著的《中国辞赋研究》。其中《论汉赋》开篇即说:“汉赋的最大特点是几乎篇篇都在反对帝王的骄奢淫逸。”[1]为了论证这个观点,龚克昌列举了汉赋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关于班固的《两都赋》是这样阐述的:“(《两都赋》)强调的是法度,他一面赞扬东都天子举止的合度,一面批判西都天子行为的逾制。和西都天子比起来,东都天子已属俭约;可是作者还不肯就此罢休,他还要天子‘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班固拿‘法度’作武器来臧否人物,来约束最高统治者过分的奢华。”[2]班固在对东都天子和西都天子的一扬一抑中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讽喻帝王要节俭戒奢。张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的,“二京”就是“两都”,即东都长安和西都洛阳,两赋地点一样;在布局谋篇方面,《二京赋》也完全模仿《两都》,《西京赋》和《东京赋》构成上下篇;而写作的目的,两者都指向当时逾侈之风。既然这样,“张衡赋乃是针对最高统治者的淫奢而发的”是毫无疑问的了。“这里只说‘自王侯以下’,而不涉及皇帝本人,自然是‘为尊者讳’,其实最大的‘逾侈’只能是皇帝本人,赋也正是这样写的……其次才是剥削阶级中的富有阶层。”
《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先夸耀西京长安离宫苑囿华美壮丽、珍物罗生、焕若昆仑,如此瑰丽的宫殿,皇帝还是不满足,“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再写天子纵猎上林苑、水戏昆明池,无不纵情杀戮以为快事。作者张衡如此警告道:“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既定且宁,焉知倾陁。”然后又批判天子生活荒淫无度,“适欢馆,捐衰色,从嬿婉”;还直截了当地揭发汉武帝“采少君之端信,庶栾大之贞固”的好仙行为。其间还穿插商贾、游侠、角觝百戏、嫔妃邀宠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一幅繁荣富贵、穷奢极侈的京都景象。《东京赋》则假借安处先生,表达了作者对西京奢靡生活坚决否定的态度,“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张衡在《二京赋》中已清醒地认识到,在“承平日久”之时,如果皇帝不遵行节俭、体察民情,那么汉天下的倾覆便近在咫尺;至于剥削阶级中的富有阶层,也是上行下效,皇帝不恭俭,他们怎会节俭。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皇帝本身。
无独有偶,褚斌杰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张衡的《二京赋》……其基本体制和创作意图,都不出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轨迹。”[3]《子虚》《上林》赋假托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和亡是公的对话,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虽然作品以大量篇幅来描写和渲染,“而赋最后则以汉天子翻然悔悟,觉醒到‘此太奢侈’,‘乃解酒罢猎’做结。就作品的主旨说,作者显然意在讽谏封建最高统治者不可过于奢侈和淫靡。”班固评司马相如赋时也曾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4]《二京赋》也增加些变化,但创作意图仍沿袭《子虚》《上林》赋,来讽谏帝王。
从张衡其人其事中能否见其端倪呢?
张衡生活于东汉由盛转衰时期,经历了章、和、殇、安、顺五个皇帝。章、和时期政治清明,国力强盛。此时张衡创作了传颂一时的《二京赋》。《二京赋》与汉大赋产生时的社会状况非常相似,都是“承平日久”。西汉,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是国势最强盛时期,这在有些封建文人的眼中,是值得称颂的“盛世”,于是产生了歌功颂德的汉大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汉大赋的作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受功名利禄的诱惑,不能不歌颂美化皇帝;另一类文人,在对强盛局面感到鼓舞的同时,又有一定清醒的头脑,对皇帝的奢靡生活进行讽喻。张衡属于后一类。首先他淡泊名利,“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他写《二京赋》,其根本目的并不是来取悦皇帝;其次,张衡“世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其祖父品学兼优,受到光武帝的赞赏和重用,为政既仁且威,“仁以惠下,威以讨奸”。张衡受祖父的影响,有兼济天下的胸怀,当“政事渐损,权移于下”时,就“上疏陈事”,规劝顺帝“恭俭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谄慢,鲜不夷戮”;“时天下渐弊”,便“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把“太山”“美人”比作君王,寄托其伤时忧世的情怀。还有为官清明的政绩,“出为河间相”,“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由此看来,张衡绝非皇帝一文学弄臣,而有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对皇帝的肆意奢华怎能置若罔闻!(www.zuozong.com)
综上所述,张衡作《二京赋》讽谏的对象既不是“自王侯以下逾侈”之人,也不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而只能是皇帝一人。
【注释】
[1]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1.
[2]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4.
[3]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63.
[4]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6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