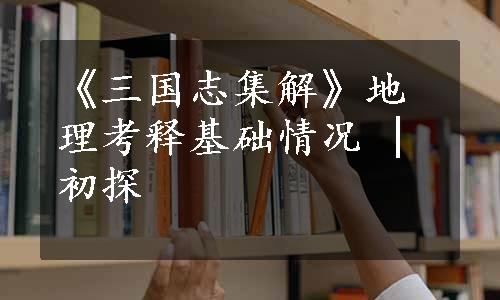
地理考释是《集解》一书学术成果最为突出的一方面,在迄今为止的各种专著与论文中均受到广泛的称美。然而,或许是由于《集解》卷帙浩繁,统计不便的缘故,古今学者均采取了举例说明的方法,对于《集解》地理考释的各项特点或成就,仅各举一两例而已,缺乏全面的统计作为基础。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并在全面统计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先将《集解》地理考释的数量作一统计。
《集解》地理考释数量与分布情况见表一。
表一 《三国志集解》地理考释条数及分布情况表
续表
续表
上表所列,是《集解》地理考释在全书中的数量与分布情况,表中条数,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钱剑夫点校版为据。由于《集解》的地理考释是与其他各类考释或辨正夹杂进行的,且《集解》常用辨地理的方法来考史实,因此往往在地理考释之後又有与地理相关或从地理引申出去的史实考证,这里说的“地理考释”,仅针对考释的对象为地名或地理问题的情况,而不包括由地名或地理问题引申出去的史实辨正,後者将在《集解》的史实辨正一章中有所涉及。表中所列之“地理考释条数”,系指有具体内容的考释,如在考释中仅只注出“某地见某纪传”“某地见某纪传某年”“某地见前(後)某年”而无沿革、今地、变迁或其他辨析、说明等具体内容,则不计入表的条数,以免重复。
从表中可以看出,《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除了第三十四卷即《蜀书·二主妃子传》一卷外,各卷均有考释,全书地理考释总计达2316条,其中单卷考释条数最多者为《魏书·武帝纪》,共有263条,最少者为《吴书·吴范刘惇赵达传》,仅有4条。而如果以国别作为标准来进行统计,则《魏书》地理考释共1404条,《蜀书》为339条,《吴书》为573条。由此可以看出,《集解》地理考释的数量在三书的分布情况与三书的篇幅大致成正比,而每一卷中地理考释的具体数量,则取决于更多的因素,如各卷原文与裴注的篇幅、传主的身份地位与生平经历,甚至包括各卷在《三国志》中的前後顺序关系。
原文与裴注相加篇幅较长的卷数,其地理考释的数量一般较多,因为行文越长,可能提及的地名及地理相关问题就可能越多,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传主的身份地位,也是决定地理考释数量的重要因素。传主的身份越高,或在历史上的地位越重要,则地理考释的数量可能越多,如《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和《吴书·吴主传》,地理考释的条数均为各自势力之最。按照《三国志》既为国别体又为纪传体的体例特点,蜀汉皇帝与吴国皇帝虽称传不称纪,但在《蜀书》《吴书》之中同样起着帝纪的作用,一切军国大事,包括巡行出游、出兵征伐、封赐爵位、变更行政区划在内的与地名、地理问题密切相关的史实均会在帝纪中有所体现,因此,上述三卷的地理考释条数最多,便是自然之理了。传主的生平经历,同样可以影响该卷地理考释的数量。生平经历越丰富,涉足地域越广泛,参与的军事政治行动越多,则传中可能牵涉的地名与地理问题就越多,《集解》予以考释的条数也自然越多。如第九卷《魏书·诸夏侯曹传》、第二十六卷《魏书·满田牵郭传》、第二十八卷《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等,就是由于传主经历丰富,参与了许多重大军事政治活动,因此地理考释条数较多。与此相反,第三十四卷《蜀书·二主妃子传》就是因为人物生平记载简略,亦无参与军事政治活动的记载而成为仅有的无地理考释的一卷。除此之外,各卷在《三国志》中前後顺序关系也会对各卷地理考释的条数产生影响。因为《集解》注释地理,常在某一地名或地理问题首次出现之时详细展开,而在其後再有出现时不再赘述,仅标明“某地见某纪传”“某地见某纪传某年”“某地见前(後)某年”等,以节省篇幅。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于全书地理考释的数量与内容均不会产生影响,而顺序在後的卷则可能由于某一地名已在之前的卷中出现并详注过而被省略,从而显得考释条数较少。
从内容上说,《集解》的地理考释十分全面,凡是《三国志》与裴注中出现的地理名词,包括州、郡、封国、县、都会、山岳、河流、关隘、沟渠、堤陂等,均有注疏,凡是《三国志》原文与裴注中出现过的地名,《集解》无不一一注疏,巨细靡遗,但在繁简程度上有所不同。
对于一般的州、郡、封国、县、都会等行政区划方面的地名,如在三国时代并无位置变更、疆域增损、分属两国等情况,也非战略要地,那么《集解》的考释就比较简单,一般只注出该地的位置、统属、治所与清时的名称,不注明该地的四至、接壤、境内名胜、风物等内容。而对于征战之区、扼要之地、疆域有所变动的地方及历史上有争议的地名,则考释较详,往往包括该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山川形势、建置沿革始末、疆域增损、治所变迁等。而对于山岳、河流、关隘、沟渠、堤陂等行政区划之外的地名,由于往往与军事行动相关,故而凡所出现,注释均较详尽。
从形式上看,《集解》地理考释有两种类型,一为集中注疏,即针对同一地名,所有的注疏均集中于一处。二为分散注疏,即对同一地名的注疏分散于几处。
集中注疏的地名,绝大多数都注于该地名第一次在《三国志》正文与裴注中出现的时候,无论是在行文叙述中出现,还是作为官职、封爵、人物籍贯的一部分出现或是以概称出现。这些集中于第一次出现时注疏的地名,在此後重复出现时不再详注,仅在必要时才标明“见前注”“见某纪(传)某年注”备查。
以“洛阳”“许”二地为例:
《武帝纪》:“(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1]《集解》注引《後汉书·郡国志》:“司隶河南尹雒阳。”[2]是注明洛阳当时统属。又引《大清一统志》:“洛阳故城,今河南省河南府洛阳县东北二十里。”[3]是注明该地在清时的位置即所谓“今地”。又引鱼豢《魏略》曰:“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故除隹而加水,变雒为洛。”[4]是注地名变迁及其原因。
而《集解》对“许”的注释体例于此相仿,除引《後汉书·郡国志》明当时统属与位置、引《大清一统志》明清时位置之外,又引数家言许县改名许昌之时,是明地名之变迁:
《武帝纪》:“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第57 页)
《集解》:“豫州颍川郡许。刘昭注引杜预曰:‘献帝徙都,改许昌。’王应麟曰:‘汉颍川许县,本许国,魏文帝改曰许昌。《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郦元云:魏承汉历,改名许昌。’赵一清曰:‘许昌以魏黄初二年改,刘昭注误’。(周寿昌说同。)《一统志》:‘许昌故城,今河南许州西南’。”(第59页)
洛阳、许昌在汉魏之时相继为都城,即不为都城时,也仍然是重要的都会,无论汉魏,皆列名“五都”之中,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三国志》特别是《魏书》各纪传中频频提及,但《集解》唯在第一次出现时注出,此後重复出现,亦多不标明“见前”“见《武帝纪》”等字样。因为二者虽为名都,但并非争战之区,其名字、位置亦不存在任何疑点与争议,因此後来出现时并不反复注明。
上述两例,一为地名作为官职名的一部分,一为在行文中出现。而对于以概称出现的地名,《集解》亦在首次出现时给予注疏。
例如:
《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辛未,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第84页)(www.zuozong.com)
《集解》:“《尔雅·释山》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陆德明《音义》云:‘泰山一名岱宗,在兖州界,汉在泰山博县。又云在奉高县。华山在豫州界,汉在弘农华阴县。霍山一名衡山,在荆州界,汉在长沙湘南县,又云在庐江潜县。恒山在并州界,汉在常山上曲阳县,以犯汉文帝讳,改为常山。嵩高在豫州界,汉在河南。’《尔雅·释水》云:‘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第84页)
五岳、四渎是地名的概称,虽然在各个时代偶有变动,但大体如此,并无特别的疑点与争议,且在《三国志》中出现不多,大体都是祭祀之时才会写到,因此在此考释一次之後,也未见重复提示“见前”“见《武帝纪》”。
以上是《集解》注普通地名的惯例,即大部分的地名都注疏于首次出现之时。然而对于争战之区、扼要之地、有争议的地方或沿革疆域有所变动的地方,《集解》也偶见不注于首次出现,而集中注于与历史事件关联最紧密处的例子,而在该地首次出现和注疏後再重复出现时则时仅标明“见後某年注”“见某纪(传)某年注”。
例如:
《武帝纪》:“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第23页)
《集解》:“合肥见後建安十三年。”(第24页)
盖因合肥一地是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在东部的军事重镇,两国在此曾多次交兵,而建安十三年是《三国志》记载中两方势力首次在此交兵,因此《集解》将“合肥”的详注置于建安十三年下。
《武帝纪》建安十三年载:“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5]。《集解》引《後汉书·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合肥。曹魏以合肥为重镇,魏明帝云:‘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必有所争也’。”是照例注明该地当时的位置与统属,然而多取了描述其战略地位的记载。引《大清一统志》:“合肥故城,今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东北金斗城。”是照例说明该地在清时的位置。除此之外,《集解》又引《水经·施水注》《资治通鉴胡注》与《通鉴地理通释》,说明“合肥”地名由来与河流形势。这部分内容是考释普通地名时并不包含的:“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迳合肥县。应劭曰:‘夏水出城父东南至此。与肥合,故曰合肥。’阚骃亦言:‘出沛国城父,东至此,合为肥。’余按川殊派别,无沿注之理,方知应、阚二说非实证也。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胡三省曰:‘肥水北注淮,而施水东南入漅湖,已自分流,惟夏月暴水涨溢,则二水合于合肥县界,故合肥以此得名。郦元之说,庶乎有徵。’《通鉴地理通释》:‘淮水与肥水合,故曰合肥’。”[6]
如上所言,合肥为魏吴之间的军事重镇,战争迭起,而《集解》在建安十三年注释之後,其後再有合肥之名出现则有标明“见上年”等字样。
如《武帝纪》建安十四年载:“十四年春三月……军合肥。”(第38页)《集解》注曰:“合肥见上年。”(第38页)又如《明帝纪》载:“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7]《集解》注曰:“合肥见《武纪·建安十三年》。”[8]
而将对同一地名的考释分散于几处进行注疏,所针对的都是战略要地或前後有变动的地方。分散注疏的地名,第一次注释时往往连带沿革与今地,其後则依据当时的历史事件,选取地理书籍中的相关史实与考证。并在各处标明“互见某纪(传)某年注”。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此类“互见”的提示往往不仅局限于《集解》注疏的内容,也常有互见《三国志》本身或裴注内容之例。
仅以“江夏”一地为例来看《集解》的分散考释:
《武帝纪》:“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第120页)
《集解》:“江夏互见《聘传》。《郡国志》:‘荆州江夏郡,治西陵。’建安中,刘表以黄祖为江夏太守,治沙羡。(见《孙策传》注及范书《刘表传》)时孙策亦以周瑜领江夏太守。(见《瑜传》及《孙策传》注)祖死,表子琦为江夏太守,(见《表传》及《诸葛亮传》)琦合江夏战士万人,与刘备俱到夏口。(见《先主传》及《诸葛亮传》)此後魏、吴并置江夏郡,文聘屯石阳,别屯沔口,在江夏数十年,郡治安陆。(见《元和郡县志》)至嘉平中,荆州刺史王基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见《基传》)是汉末及魏、吴之江夏郡治,非复汉郡之旧矣。(吴江夏郡治武昌)《一统志》:‘西陵故城,今湖北黄州府黄冈县西北;安陆故城,今湖北德安府安陆县治;上昶故城,今安陆县西北;(谢钟英曰:当在今孝感县东南。)石阳故城,今德安府应城县东南’。”(第123页)
《文聘传》:“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第1507页)
《集解》:“江夏郡见《武纪》建安十三年。赵一清曰:‘吴魏并立江夏郡,吴江夏郡治沙羡,孙权以程普领太守。魏以文聘为太守,屯石阳。’吴增仅曰:‘建安中,刘表以黄祖为江夏太守,屯沙羡(《吴志·孙策传》)。魏武平荆州,以文聘为江夏太守,屯石阳。嘉平中,王基自城上昶,徙江夏郡治之。终魏之世,郡治皆在上昶也。洪《志》据《元和志》云:曹魏郡治安陆,盖上昶为安陆县地,统言之也。’谢钟英曰:‘《先主传》:建安十三年,与曹公战于赤壁,曹公引归,先主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其时江夏全境俱为琦有,迨琦既没,吴遂略取江夏诸县以通道江陵,於是程普为江夏太守。及孙皎代程普督夏口,赐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为奉邑,见《皎传》。吴之全有江夏,断在此时,其後沔北地渐入魏。嘉禾五年,遣将军周峻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见《陆逊传》。诸葛亮曰: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可知沔北之安陆、新市、云社、竟陵于黄武中皆入魏也。’王先谦曰:‘江夏郡魏吴分立,竟陵、云社、南新市、安陆四县地在沔北,建安中属吴,黄武时皆属魏。’弼按:‘《夏侯尚传》: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谢氏谓魏江夏郡境北界义阳、汝南,东界弋阳隙地,西及南皆阻汉水接吴,此实魏江夏郡之辖境也’。”(第1509页)
《陆逊传》:“(嘉禾五年)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第3466页)
《集解》:“新市见《孙皎传》,安陆见《魏志·蒋济传》,石阳见《魏志·文聘传》。胡三省曰:‘新市、安陆二县,皆属江夏郡,魏初以文聘为江夏太守,屯石阳,舟车凑焉,颇为繁富。沈约曰:江夏曲陵县,本名石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曲陵,宋明帝泰始六年并曲陵入安陆县’。”(第3467—3468页)
江夏郡地自汉末曹操与孙权交战之後,常为争战之区,且三分之势形成之後,魏吴二国皆置江夏郡,虽然同名,但位置、辖地、治所等当然不同,又因为江夏郡幅员颇广,是较大的行政区划,下辖诸县由于战争的影响而时有变动,实在难于集中在一处剖析明白。因此《集解》在考释时各随其事,将江夏郡的问题分置于数处相关的军事行动之下,而标明互见,以备查询参考。类似这般变动频繁情况复杂的郡县,往往处于三国交界的地方或边疆地区,在全部的地名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因此需要将一个地名分散到数处进行考释的情况并不太多。
综上所述,《集解》地理考释的基本体例是对于普通地名注释较简,对有争议、有变动、与战争相关的地名注释较详。通常前者只注明古地与今地,而後者则多注明山川形势、疆域增损、建置沿革等具体情况。《集解》在考释地名时一般都将对同一地名的注疏集中在一处,至于是集中于首次出现时还是集中于与史实相关最紧处,则要视乎该地只是普通地名还是具有特别的战略价值或其他复杂情况。而对于重要的争战之地或争议之地,如无法一次将源流本末剖析清楚,《集解》也会选择分散在数处考释并标明互见的方法。
此外,从上述几个例子中也不难看出,《集解》的地理考释,首重考沿革与释今地。无论对于一般的地名还是战略要地,无论注疏繁简,必定注出该地在当时的位置统属与清时位置。对于在三国时期没有变化的郡县都会,沿革往往取自《後汉书·郡国志》,释今地则以《大清一统志》为准。而其他有建置、撤销、改名、分割等变动的郡县,或是有争议、位置不确定的地方,则在两书之外另取相关资料进行考释,其中常用《宋书·州郡志》《水经》《水经注》[9]《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虽然卢弼在《覆胡绥之先生书》中称“马彪续书,郡国厘然,沈约《宋志》,颇详三国,考订沿革,取材二书”[10],对沈约的《宋书·州郡志》也颇为推崇,但在实际考释的引用中最主要的几种引用文献出现的频率来看,仍然以《後汉书·郡国志》与《大清一统志》引用最多,《宋书·州郡志》与其他诸书的引用大体相当,远不及二书引用频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