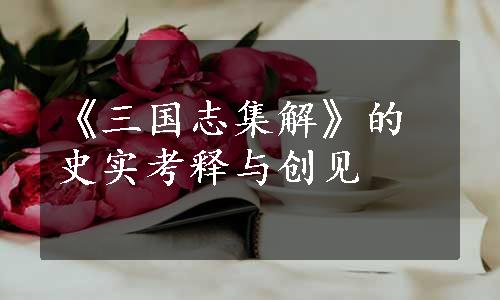
一、《三国志集解》史实考释的纂辑
如前所述,本章所研究的《集解》史实考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史料的补充,二是史实辨正。因此《集解》的纂辑也同样分为这两个部分,其各自的条数与分布情况见表七。
表七 《三国志集解》史实考释徵引条数与分布情况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上表就是史实考释中史料补充与史实辨正两方面内容的数量与分布情况,表中“史料补充”一项的条数,仅限于以补充史料为目的且一条考释中之全部内容都为徵引,没有任何附加阐释与辨正的情况,若是在徵引史料之馀有所辨正或在辨正某一问题时徵引史料作为论据,则不包括在这一项统计之内。通过上表的统计可以看出,在《集解》的徵引中,史料补充的条数较多,其数量是史实辨正的三倍有馀。
虽然《集解》在史料补充方面的徵引条数有1789条之多,但其取材的来源却并不广泛,除了《三国志》与裴注之外,以《後汉书》《晋书》与《资治通鉴》三种徵引最多,在《蜀书》部分对《华阳国志》的记载也较为重视,其馀如《後汉纪》《太平御览》《北堂书钞》《通鉴补》《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等书,只有零星的引用,数量极少,远比不上《後汉书》、《晋书》与《资治通鉴》三书的引用繁多。
东汉与晋朝是与三国时代前後相接的两个历史时期,因此,记载两朝史实的正史即《後汉书》与《晋书》中,有许多富于价值的史料可供与《三国志》进行对照或补充,对于上述二书的徵引,以《魏书》中的各纪传为多。在武帝、文帝之时的传记中,《集解》常引《後汉书》史料作为补充,因为魏国前期帝王大臣,均是由汉入魏,其行迹在《後汉书》中存留较多,特别是对于一些在《後汉书》与《三国志》中均有传记的人物,如董卓、吕布、袁绍、袁术、刘表、吕布、臧洪、公孙瓒等,更在相关卷中对《後汉书》频繁引用。由于《三国志》叙事极简,而《後汉书》文采过之,所以在史实的记载上,後者往往能够提供更为详细丰富的细节作为补充。
例如:
《董卓传》载董卓入京城後凶逆之事,曰:“……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第629页)
《集解》:“范书《卓传》:‘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及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范书《列女传》:‘皇甫规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及规卒时,妻年犹盛而容色美。後董卓为相国,承其名,娉以车并辎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妻乃轻服诣卓门,跪自陈情,辞甚酸怆。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围之,而谓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妻知不免,乃立骂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犹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礼于尔君夫人邪!卓乃引车庭中,以其头县轭,鞭扑交下。妻谓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尽为惠。遂死车下。後人图画,号曰礼宗云’。”(第632页)
从《集解》此条徵引,可见《三国志》与《後汉书》的叙事风格不同。董卓祸乱京师而招致各方势力的讨伐,是汉末三国的关节之处。其在京城的凶逆之事自然甚多,而《三国志》仍然保持一贯质朴凝练的风格,仅以最简单朴实的笔法进行记载,别无铺陈,而《後汉书》的记载则较为详尽生动,细节也更为丰富,正因为如此,它的记载能够起到与《三国志》形成互补与对照的作用,使人对于董卓凶逆之情状了解更为清晰。
又如:
《董卓传》载董卓杀伍琼、周珌之事:“初,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资、张邈等出宰州郡,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卓闻之,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第632页)
《集解》:“范书《卓传》:‘初平元年,馥等到官,与袁绍之徒十馀人,各兴义兵,同盟讨卓,而伍琼、周珌阴为内主。卓欲徙都长安,伍琼、周珌又固谏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劝用善士,故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遂斩琼、珌’。”(第633—634页)
在对同一事件的描述中,《三国志》与《後汉书》出现了细微的差异,前者称董卓“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但对于事实是否正如董卓所设想的一样却无记载,而《後汉书》则明言二人确实“阴为内主”,与讨伐董卓的同盟有通联之事,且指出此事虽为二人之被杀之主因,但拂逆董卓之意固阻其迁都也是二人获罪的因素之一。《集解》在徵引之後不加辨正,当是认为《後汉书》的记载可信,足可补《三国志》之阙的缘故。
与徵引《後汉书》同理,对《晋书》的引用,则多集中于魏明帝、三少帝时人物的纪传之中,其徵引的体例亦略同《後汉书》,故不再加举例。然而,由于《三国志》记事止于当代,向前追溯至後汉是为了记载三国形成的缘由与历史背景,但并未包括晋朝之後的历史,所以《集解》在徵引史料时,于《晋书》的徵引次数与篇幅要少于《後汉书》,常引的惟宣、景、文三帝纪而已。且《晋书》的史料价值与史学地位不如《後汉书》、《三国志》,故《集解》徵引之馀,时加辨正,不能算作单纯的史料补充,而应视为辨正的一个部分。
《集解》在史料补充时较为重视的第三部史书为《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虽然经过转手与加工,但是是书对史料的剪裁颇为得当,且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有别于正史以人物为中心展开记述的体裁,可以提供相对宏观与客观的视角,又完整地贯穿整个後汉三国的历史,不似《後汉书》与《晋书》的记载内容只有一部分与《三国志》的时间和人物重合,因此在《集解》的徵引之中,对《资治通鉴》的记载亦常有引用。
例如:
《文帝纪》载:“(黄初三年)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第306页)
《集解》:“《通鉴》:‘是时,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各有老兵百馀人,以为守卫,隔绝千里之外,不听朝聘,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于匹夫,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诸侯王过恶日闻’。弼按:此皆魏文猜忌残忍,有以致之。此任城王之所以不得其死,而陈思亦几不免矣。”[11](第307页)
《文帝纪》的这一句记载,只是依照惯例记载下来的一项宗室封王的史实而已,孤立地来看,似乎并无更深刻的内涵。而《集解》在此下徵引《通鉴》的记载,提供了曹魏防范宗室诸侯的具体情况,使人了解到魏时宗室诸侯的普遍待遇究竟如何。事实上,曹魏自立国之始就对宗室骨肉惊人地刻薄寡恩,其疏远宗室的情形在《任城陈萧王传》与《武文世王公传》二卷中多有体现,曹植是其中的典型,久为文、明两代皇帝疏远与防范,屡次上书求以自试而不得。《集解》将《资治通鉴》的这一段记载置于曹植封王的记载之下,显然也考虑到这段记载与其遭遇的切合。虽然《三国志》中也如实地记录了这些史实,但均散见于各卷之中,并无明确的总结与相关论述,读者固然可以通过细心体察来发现曹魏素来刻薄骨肉疏远宗室这一普遍现象,但若不留心各卷之间的联系与散见各处的零星记载,则不易得出上述结论,而《资治通鉴》此条记载的作用,就是提供了客观的、带有总结性质的叙述,使得读者易于对曹魏对待宗室的惯例得到总体上的大致印象,便于加深读者对这一史实的认识。
除了上述三种《集解》徵引史料的主要来源文献之外,其馀所徵引的诸书由于数量较少且体例相同,无甚特别之处,兹不赘述。
在史料的补充之外,《集解》在史实的阐释与辨正方面,也同样徵引了大量前人的著述,特别是对清人的成果网罗较为全面。在徵引前人辨正成果时,《集解》往往在一条考释之中存有数家之言。若诸家意见相同,则择有代表性的论述详引其一,其馀注明“某人、某人说同”;若诸家意见相异,则将异同之处一一罗列。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集解》罗列之馀常加按语断其是非或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这一情况当归于《集解》有所创见的部分,而非单纯的徵引前人成果。此外,由于著述之人在考辨史实时不免将前人或同时之人的意见转引,或加阐释,或加批驳,故有时《集解》直接徵引的只是某一家的著述,但其中也往往会涉及多种观点。当然,在考释时仅只徵引一家之言、一种观点的情况亦有不少,但其考释的对象往往是比较简单、无争议的史实问题。
例如:
《董卓传》载:“灵帝崩,少帝即位,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谋诛诸阉官,太后不从,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第622页)
《集解》:“《通鉴考异》曰:‘《何进传》:召卓屯关中上林苑。按,时卓已驻河东,若屯上林则更为西去,非所以胁太后也,今从《卓传》’。”(第624页)
这一条考释中,《集解》就只徵引了《资治通鉴考异》一家之言,其观点、论述也十分简单明确,只是通过对照原书《董卓传》与《後汉书·何进传》两者之间记载的差异之处,以地理位置与当日情势为据,判定何进当时是召董卓带兵入京即洛阳,而非往关中上林苑,肯定了原书《董卓传》的正确记载。这一条是关于史实细节的考释,情节并不曲折,亦无可争议之处,是以经《资治通鉴考异》定论之後,後来之人未曾再加考辨。
由于《资治通鉴》在编纂中广泛地参考了各种史料,常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甚至更多来源的史料编纂而成的情况,则其中当然有剪裁取舍的问题,为了说明取舍的缘由,司马光另撰了《资治通鉴考异》,其中对史实的考辨颇富价值。《集解》史实考释部分所徵引的考辨成果,大多为清人之作,而对于裴注之後,清代之前的成果,《资治通鉴考异》的内容较为受到重视,其徵引的具体情形如上例。
除了通过与它书记载进行对比从而判定是非的方法之外,《集解》的徵引中也有许多内容是通过对某一事实前後的相关情况、当时的历史背景等内容的考察来进行考释的例子。
例如:
《曹爽传》注引《魏略》载曹爽覆亡之事:“范南见爽,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徵四方以自辅。”(第955页)
《集解》:“王懋竑曰:‘司马懿与曹爽各领兵三千人,更宿殿内,是年,转为太傅,而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但不言录尚书事。然懿至正始八年,始谢病不与朝政,则前此固未尝不与也。正始二年、四年,懿出拒吴,五年,爽出征蜀,彼此出入未有疑忌。自爽出无功,晏等有猜防之意。六年,以羲领中垒、中坚营。七年,与懿异议。八年五月,懿谢病,盖已定诛爽之计,特以稔其恶而毙之耳。懿受文帝遗诏辅政,已有不臣之心。东擒孟达,西拒诸葛,威名甚盛。迨辽东之役,大肆诛杀,藉以服众。爽之愚騃,晏等之浮华,夫岂其敌!懿盖玩之股掌之上,而犹迟而後发。诛爽之後,自为丞相,加九锡,俨然以操自居,而俛仰之间,国祚已移矣。即使爽用桓范言,奉天子诣许昌,不过稍延月日之期,终必为懿禽灭,盖懿之阴谋已久,威胁已成,内外诸臣皆为之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961—962页)(www.zuozong.com)
曹爽及其兄弟、支党的覆灭,是司马氏掌握中枢权力、倾覆魏鼎过程中的关键事件,然而由于事涉当朝,所以陈寿著史时使用的措辞比较委婉隐晦,留下的记载也因此较为简单,而裴注引《魏略》的记载,则保留了更为丰富详细的细节,可以使人多少了解到这一事件的内情。《魏略》所记载的桓范向曹爽兄弟进言献策之事,发生在高平陵政变发动当日,司马懿父子已经取得兵权,控制京城局面之後。当时京城戒严,桓范设计骗开城门南奔曹爽,遂有此计,而曹爽兄弟犹豫不决,终于不纳其言,束手就擒而败亡。《集解》在此徵引的王懋竑之说,所针对的是桓范“以天子诣许昌,徵四方以自辅”的计策,王懋竑将曹爽、司马懿二人从并受明帝托孤以来数年中的职权、功业、势力消长变化、关系从“未有疑忌”到“有猜防之意”,再到司马懿定诛爽之计直至最後实施的过程简要地总结出来,指出了曹爽败亡的必然性。司马懿早在受文帝遗诏辅政时就已经生出了不臣之心,此後屡出征伐得胜,内外膺服其威名,而与此同时曹爽本身愚笨无才,支党皆浮华之徒,远出伐蜀惨败而归,其声望、能力与功业全然不是司马懿的对手,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加以司马懿“阴谋已久,威胁已成”,所以曹爽一党的覆亡乃至魏国国祚的倾覆皆已成为定局。桓范提议之时,政变已然发生,即使曹爽兄弟用桓范之言,也不过是迁延时日,无法旦夕之间改变其必然的结局。
在《集解》史实考释的徵引中,像上述两例那样每条考释仅徵引一家之言的情况数量较少,更多的情况是在同一条考释中包括了多家之言,各家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观点、视角、论述、研究程度上的差异。由于《集解》徵引前人论辨成果,绝大部分都属于此类情况,因此为节省篇幅,仅略举比较简单的两例作为说明。
例如:
《明帝纪》:“(太和四年)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第373页)
《集解》:“钱大昕曰:‘《武宣卞后传》云: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和四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此作六月,异。’潘眉曰:‘推太和四年五月无戊子,当是《后妃传》误’。”(第374页)
这是一条内容十分简单的考释,《集解》的徵引包括钱大昕与潘眉两人的意见,钱大昕的工作是引《后妃传》中的记载,说明对卞后去世时间的记载在《明帝纪》与卞后本传中一作六月,一作五月,指出了在时间上可能存在问题,但对于两种记载究竟何者为是却未下结论,而潘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当年五月并无戊子日,因而应该是《后妃传》的记载为误。
又如:
《邓艾传》载景元四年十二月灭蜀之役结束後论功之诏曰:“其以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第2073页)
《集解》:“潘眉曰:‘魏朝爵土无封二万户者。宗室诸王,惟任城王彰、陈思王植曾封万户。正始中,曹爽封武安侯,邑万二千户,群臣惟张鲁以客礼阆中侯,邑万户,满宠封昌邑侯,前後增邑至九千六百户。艾同时钟会破蜀,进封县侯,增邑亦不过万户,艾独增邑二万户,若非传写之误,则特典也。(司马氏爵土不在此例。)’沈家本曰:‘艾先独封邓侯,邑六千六百户。会封亭侯,邑三百户。破蜀之功,艾多于会,会由亭侯超封县侯,邑万户。艾不过增邑稍多耳,未尝厚于会,不得以此为疑’。”(第2075页)
在这条考释中,潘眉认为曹魏对大臣封赐爵土时没有封到二万户之多的例子,即使在宗室诸王中,也只有文帝同母弟任城王曹彰和陈王曹植二人曾经有过万户爵土,受遗托孤的武安侯曹爽爵土一万二千户。而在非宗室的群臣中,只有张鲁情况特殊获得一万户的爵土,其馀众臣,最多的也只有满宠的九千六百户,且是多次增加之後累积起来的户数。而邓艾与钟会一同灭蜀,钟会进为县侯,也不过是增邑一万户。据此,潘眉认为诏书中为邓艾增邑两万户过于丰厚,事有可疑,若不是传写出现问题就是特殊的荣典。但沈家本则认为潘眉以钟会的增邑来类比邓艾有不妥之处,因为邓艾原本封邓侯时就已有六千六百户,而钟会先封亭侯,食邑仅有三百户,二人在灭蜀一役之前爵土的户数本来就差异极大,况且在灭蜀的整个过程中邓艾之功本来就多于钟会,後者在论功时越过乡侯一级由亭侯超封县侯之馀,又增邑万户,而邓艾本来就已经是县侯,不过是增邑的数量稍多而已,但这与其灭蜀之功也是相衬的,不必对此有何疑惑。
以上就是《集解》史实考释部分纂辑前人成果的情况。在史料补充的部分,除了重视《三国志》与裴注各纪传见的互相参照互相补充之外,《集解》对于《後汉书》《晋书》与《资治通鉴》三种史书的引用占到史料补充中很大的比例,而对《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後汉纪》《通鉴补》《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等文献的引用数量都很少。在史实辨正的部分,《集解》比较全面地搜集了清人的研究成果,而对于清代以前的相关研究,比较重视的是《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胡注两种。
《集解》史实考释部分的纂辑,有胜于前人最突出的一点体现在史料补充方面。自裴注因取材之便对《三国志》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史料补充之後,由于相关文献的逐渐散佚,後人主要精力遂都转移到文字音韵的训诂与书中内容的辨正上,即使徵引史料,亦多是零星地截取只言片语作为辨正时的论据,若不能对辨正起到帮助作用则往往不加徵引,并无对史料进行系统徵引作为补充的主动意识。虽然在牵涉到文献的范围上《集解》并不广于清人著述,但其是有意识地仿照裴注之例进行系统地史料补充,在徵引的条数、篇幅与完整性上大大地超过了前人,虽然其所引之书史料价值逊于《三国志》,无法起到裴注所起到的补阙作用,但也起到了备异的作用。这一点是前人的著作未能做到的。
二、《三国志集解》史实考释的创见
正如本文在之前两章的研究中均已提及的那样,《集解》一书的首要宗旨,在于尽量全面地网罗前人的既有学术成果,而将自身的创见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上。因此,《集解》各部分考释内容中用于纂辑的篇幅均超出创见部分较多。不过,在史实考释这一部分,虽然纂辑篇幅超出创见较多这一总体格局并未改变,但後者的条数与在考释内容中所占的比例较之前的地理、职官两部分却有很大的提高,其具体的条数与分布情况见表八。
表八 《三国志集解》史实考释中卢弼创见条数与分布情况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从上表的统计可以看出,《集解》的史实考释部分,共有创见826条,虽然其数量同样远逊于纂辑的部分,但其在这一部分中所占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与地理部分创见276条、占考释总条数十分之一的情况相比,显然在数量与比例上都有大幅的超出。同样,与职官部分创见166条、占考释总条数五分之一相比也同样超过甚多,而且,如果将考释中创见的质量一并加以考虑,职官部分显然又不能与地理、史实相提并论。虽然史实考释的创见并非每一条都如地理部分那样精义纷呈,但在总体的质量上也保持着很高的水准,在考释的过程中,《集解》对于前人之说,凡是以为有误或意犹未尽的,悉加辩驳或阐释,凡是诸家之言有所异同的,则尽量断其是非,且常能注意到前人未加考释的问题,时发新意。
在进行史实考释时,卢弼较少像在考释地理与职官时在其创见之前冠以“弼按”的字样,特别是当其所考释的是前人研究中未尝涉及、并无既有成果可供徵引的问题时。
在卢弼有所创见的内容中,以与时间相关的考释数量较多,如历史事件发生的年月及具体日期、持续的时间、相互之间的先後顺序、人物的年龄等问题。此外,《集解》还常常在《蜀书》与《吴书》中年号改易或有事涉三方之时标明三国纪年的互见,这一情况在帝纪中尤为多见。对于《蜀书》中的内容,《集解》仅标明当年魏国的纪年,而对《吴书》则同时标明魏国与蜀汉两方纪年。
时间与空间,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之一,卢弼在《覆王季芗先生书》中提到前人考释的四条弊端,其中第三条就是“不察当时情势,详稽年月”。[12]而详稽年月的工作,就体现为史实考释部分时间相关问题的辨正。对于时间的考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某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即年月日的考释,一是对不同事件之间前後顺序的考察。前者较为简单,兹不赘举;而後者涉及的因素较多,往往需要将多方的记载进行互相对照,或体察当日情势来进行确定。
例如:
《武帝纪》:“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馀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第21页)
《集解》:“《官本考证》李清植曰:‘按《魏武故事》所载《十二月己亥令》,操先在济南,後徵为都尉,此拜骑都尉乃在济南相之先,似当以操自叙为正。’弼按:《陈志》不误。据《後汉书·皇甫嵩传》‘骑都尉曹操适至’,是时嵩讨黄巾,为中平元年,操年三十,迁为济南相亦在是年。故《让县自明本志令》云(此令见後建安十五年注):‘去官之後,年纪尚少,同岁中年有五十,从此却去二十年,乃与同岁始举者等’,正谓此也。‘後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乃连类叙述之辞。操为典军校尉,在中平五年,年已三十四矣。”(第22页)
这一条就是关于史实发生先後顺序的考释,针对的是曹操任济南相与骑都尉两职孰先孰後的问题。李清植引《十二月己亥令》中曹操的自述为据,认为曹操先在济南任职,然後被徵为骑都尉,而《武帝纪》的记载与《十二月己亥令》的行文顺序相反,应当以曹操的自叙为正确,《武帝纪》为误。原本,历史人物的自叙是最直接的第一手史料,其可信性一般要比经过他人加工而成的史料要高。李清植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而判定《武帝纪》对曹操先後任官的顺序记载出现了错误。对此,卢弼进行了辩驳。《後汉书·皇甫嵩传》中有“骑都尉曹操”的称呼,是时为中平元年,曹操年三十岁,迁为济南相在同一年,而其受徵为骑都尉至少在中平元年之前。而根据《武帝纪》後文建安十五年裴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记载,曹操从济南相任上去官之後至建安十五年正有二十年[13],也证明了曹操任济南相确是在中平元年。《十二月己亥令》中“後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的行文只是连类叙述的手法,曹操为典军校尉已经是迁济南相四年之後的事,其後于徵为骑都尉的时间就更长了。因此《武帝纪》对于曹操任骑都尉与济南相两职的先後顺序之记载并无错误。
上例即是《集解》考释史实发生先後顺序的例子。当然,并非全部的史实问题都仅与时间相关,其中也有很大的部分还牵涉到其他的因素。
例如:
《武帝纪》载:“绍又尝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第40页)
《集解》:“赵一清曰:‘按《後汉书·徐璆传》注,举玺向肘者,乃是袁术逼夺孙坚妻之物。魏武曰:我在,不听汝乃至此。其事为有徵。今以弟移作兄,陈承祚之疏也。’沈钦韩曰:‘绍之事在共讨董卓时,其云玉印,不必定是传国玺,又术拘坚妻夺玺在坚歿後,距讨卓时已三年。术在淮南,何缘举向曹操?此注合二袁两事为一,大缪。’弼按:沈说是。初平元年,术在南阳,与操隔绝。术拘坚妻夺玺,范书《术传》在初平四年。是时,术方与操战于匡亭,更无举玺向操之事。范书《徐璆传》章怀注误引卫宏之说,赵氏又误引此注,《陈志》实不误也。”(第41页)
这一条考释中其实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此处的“玉印”是不是传国玺,二是将玉印“举向其肘”的人是谁。关于这两个问题,清人已经进有考释。赵一清引《後汉书·徐璆传》注,将此处的玉印理解为传国玺,即孙坚得于洛阳,其死後被袁术逼夺的玉玺,因而同时认为将玉印“举向其肘”的是袁术而非袁绍,《武帝纪》将袁术之事移于袁绍身上是错误的。对于这一说法,沈钦韩进行了辩驳,首先,所谓玉印未必就是传国玉玺,其次,袁术夺玉玺在孙坚死後并不在此时,且袁术在淮南,并不在讨伐董卓的联军之中,与曹操并不在同一地点,没有同席并坐的机会,是以根本无法举印向曹操,赵一清所引的《後汉书·徐璆传》注将二袁的两件事混为一件事是错误的,《武帝纪》的记载并无问题。对于前人已有的两种不同意见,《集解》肯定了沈钦韩的说法,并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辨正:在时间方面,讨伐董卓的联盟起兵是在初平元年,而袁术夺得玉玺在三年之後的初平四年,因此此处之玉印若为袁术所举,也绝不可能是传国玉玺。在空间方面,初平元年袁术在南阳,并不在讨伐董卓的联军之中也即与曹操不在一地,而初平四年夺得玉玺之後袁术与曹操正在作战,更无理由举玺而向,因此无论是在初平元年还是初平四年,袁术都无可能做出这一举动,还应以《武帝纪》记载的袁绍为准。《後汉书》李贤注引用的卫宏之说是错误的,而赵一清不加考察地误引其说,才造成了错误的结论,《武帝纪》的记载并无问题。
除此之外,《集解》的史实考释亦多有见解过人之处,如卢弼在《覆王季芗先生书》中自言的“邺下初平,甄姬掩面事在建安九年,子建年才十三,词客惑于‘宓妃留枕’之艳辞,遂疑陈思,有不谨之嫌,此真千古奇冤,应为昭雪”[14],及胡玉缙《集解序》中所提及的“献帝聘操三女,据范书《献穆曹皇后纪》‘三女为宪、节、华,後立节为后’,证以本纪‘建安二十年,帝立操中女为后’;《陈留王奂纪》‘景元元年,故汉献帝夫人节薨,知立为后者乃节非宪’”[15]等事,皆是《集解》关于史实考释的眼光独到之处,然而其考释的形式大体类上,兹不多举。
总而言之,卢弼在史实考释中的创见大致可分为三类,对于前人已经有所研究的问题,凡是以为有误或言之不尽,则悉加辩驳或阐释;凡是前人观点有所异同的,则尽量断其是非;而对于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问题则往往视角独到,精义纷呈。在史实考释的部分中,卢弼创见不但数量与比例上较地理、职官部分有大幅的提高,且其创见的质量亦颇可称道,如果说《集解》地理考释的创见是虽少而精,那么史实考释的创见则可称为既多且精,颇富价值。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