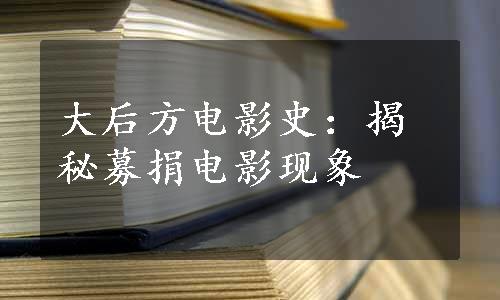
社会生活中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不会是孤立偶然的,它必然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发生在战争期间的特殊现象的考察更是不能忽视“战争”这个时代大背景。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抗,更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前方大量的军需物资要靠后方供给,后方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也必须得到满足。战争之前,中国工业生产基地和经济较发达地区都集中在东部。抗战爆发后,东部地区的沦陷,使本就薄弱的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国民政府不仅丧失了沦陷区的税收收入,内迁工厂的复工、东部人民的西迁又需要大量的资金。国民政府的解决之法,除了大举外债和广受诟病的大量发行钞票之外,最基本的措施就是增加名目繁多的捐税。在众多捐税种类中,娱乐税对国民政府意义重大。
1.娱乐税的含义
娱乐税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电影、戏剧、书场、歌场、球房、溜冰场及其他娱乐场所代为征收的一个税种。它的征收对象是消费者,而由场商院商等娱乐场所经营者代为征收,娱乐捐的税率采用弹性比例税率,按照售卖票价计征。[123]
从抗战爆发起,重庆市娱乐税的税率也经历了几次变化。1938年公布的《重庆市救济市战区儿童筵席捐娱乐捐实施办法》规定:筵席、娱乐税税率均为5%。1940年8月重庆市政府又发出布告,将筵席、娱乐两税税率由5%改为10%。从1942年起,娱乐税的征收得到了国家立法的支持,结束了多年来娱乐税征收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这部于1942年4月12日由国民政府颁布施行的《筵席及娱乐税法》里,娱乐税税率被提高到30%。1943年经过修正的《筵席及娱乐税法》再次调整娱乐税税率,规定娱乐税税率不得超过50%。[124]从一个地方税种到由国家统一立法定税,国民政府对娱乐税的重视可见一斑。
随着娱乐税税率的提高,娱乐税逐渐成为重庆市地方自治税捐的重要支柱。1943年重庆市筵席及娱乐税在地方自治五种税捐收入中占到了27.47%,排在第二位[125],而这还是1943年时筵席税和娱乐税加起来计算出的数据。我们从重庆市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时期《重庆市财政局税捐征收处三十三年一至六月份各项地方岁入超收明细表》和《重庆市财政局税捐征收处三十三年七至十二月份各项地方岁入超收明细表》中可以计算出,1944年仅娱乐税一项就已经占到重庆市全年地方税捐收入的25.39%,这一年里有5个月娱乐税收入排在第一位,剩下的7个月中,仅有1个月娱乐税收入排在第三位,其余时间里都处于第二位。[126]。
现将民国三十三年度重庆市财政局税捐征收处岁入超收明细表摘抄如下(原表项目过多,未摘抄税收数目较少的三项“车牌照税”、“轿牌照税”、“船牌照税”以及每月项目中的“预算”与“实超/实欠”两项):
表5-10 民国三十三年度重庆市财政局税捐征收处岁入超收明细表(单位:元)

续表

或许1946年的数据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娱乐税对重庆市财政收入的贡献在不断攀升:1946年时筵席及娱乐税占重庆市地方自治五种税捐的55.02%,远远超出第二名屠宰税25.4个百分点。[127]
但是真正对演映事业造成巨大负担的是随税附加的各种名目的捐费。“随税附加各种名目捐费,是地方税普遍现象。”[128]1943年6月份《中央日报》上民众影院放映《科学怪兽》的广告中明确表明其13元的票价构成:连捐7元、邮政储蓄金1元、节约建国储蓄券5元。其中连捐7元表明,票价本身只要7元,而且这个数字已经包括了娱乐捐的正捐。娱乐税调整为50%的规定是1943年7月8日才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的,那么即使之前的娱乐捐都按照1942年30%的规定执行,那么在这总共13元的票面数字中,真正的票价只有4.9元,只占到票面数字的37.69%,何况这个数字还不是真正扣除所有税收后的数字,这里面还包括了印花税、营业税等其他赋税。
民众影院《科学怪兽》一片的票价构成还只是一个个例,实际上在我们的查阅中,1941年到1944年的娱乐税附加捐名目繁多,在不同时期曾出现过冬令救济捐、防空捐等不同捐种。
在娱乐税及其附加捐节节攀升的背景下,募捐方式的娱乐演出应运而生。
2.募捐形式的捐税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起了多个“运动”,从“春礼劳军”、“寒衣代金”、“出钱劳军运动竞赛”、“劝募战时公债”,到捐献滑翔机的“一元献机运动”,不一而足。这些“运动”的共同特点都是要求各机构和个人捐钱捐物。
为了应付这众多的“出钱”运动,各影院一般都会提升票价,然后在报纸大广告中做出说明。比如1941年“国泰”上映《豆蔻年华》时就于4月19日做出广告说明:“为出钱劳军及劝募公债,本片开映特呈准每票附加1元,售票1张提1元作购战时公债及劳军捐款。”[129]1942年“唯一”上映《凯赛林女皇》时也于1月28日在广告中告知该片“为响应募献滑翔机,附加捐款一元”[130]。不论政府对各机构号召的这种募捐有没有强制性,实际上这都是各院商把自己身上的捐献任务转嫁给了观众。
前文描述主催方和募捐事由概况的部分曾经提到,年份靠前的募捐事由多为“为响应……运动募捐”,这也就是募捐形式的捐税经常使用的事由。这个时候抗战即将进入(或是刚刚进入)相持阶段,民众在抗战初期燃烧起来的爱国反抗的激情虽然已经黯淡许多,但仍然“余波未平”。从1941年7月由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到1941年10月止,重庆各界就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131]。“献机运动”的成绩充分说明了此时在重庆民众中蕴藏的爱国热情还可以被继续挖掘,因此此时的娱乐税附加捐都还能明目张胆地打上“募捐”的旗号,使“募捐”成为影片放映的一个噱头,反而能因调动起民众的爱国激情而达到广告效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的激情在慢慢平息,再加上电影、话剧、戏曲甚至马戏、魔术、游艺会等众多娱乐项目反复号召“募捐”的疲劳轰炸,“募捐”不再能成为调动观众兴趣的屡试不爽的手段。

资料来源 根据1941—1943年的报纸广告统计。
正如前文所举1943年6月民众影院《科学怪兽》票价构成一例所示,13元的票价构成中有5元是节约建国储蓄券,1元是邮政储蓄金,娱乐税正捐则包括在连捐的7元中。这个时候的娱乐税附加捐已经撕下早期“募捐”形式的温情面纱,以强制和隐蔽的形式成为整个票价构成的一部分。所谓隐蔽是因为此时的附加捐不再在报纸上做“募捐”大广告。13元中的节约建国储蓄券在1940年时已出现,不过1940年时的节约建国储蓄券的销售还是以“节约建国运动”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在报纸上做宣传。1940年11月的《中央日报》上就曾出现过“节约建国储蓄运动扩大宣传劝储周”游艺活动的连续多天的大规模广告。这些游艺活动从电影、话剧、戏曲演出到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无所不包,节储券的销售方式还是“当场购买节储券,每券赠送入场券一张”[132]。到1943年时,节储券已经成为电影票价中必须包括的一个部分,并且可能有部分观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购买一张电影票就已经购买了5元的节储券,因为即使电影广告中有说明一部影片的票价,也很少会把票价构成告知观众,像我们所举的《科学怪兽》列出票价构成的例子是极其少见的。
3.“强势”主催方与“高价”荣誉券
我们把那些在较早的年份里出现的,比普通券高出数倍的荣誉券称为“高价”荣誉券,这是与在下一部分的分析中会提到的“低价”的荣誉券相对而言的。
1943年4月22日,中国万岁剧团的话剧《蓝蝴蝶》在抗建堂夜场开演。广告称演出是“为先烈吴蔡二公纪念堂筹募建筑基金”,该剧的票价被定为20元、30元、50元、100元、200元五个档次,其中50元、100元、200元属于荣誉券设置。那么这些荣誉券的购买者是哪些观众呢?
在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档案中,有一批1943年时重庆市各行业公会对商会推销《蓝蝴蝶》剧券的回函[133]。查看当年的这些公函,我们发现重庆市商会向各行业公会推销的《蓝蝴蝶》剧券全为荣誉券,从50元到200元三种剧券均有。就向当时的重庆市商会写了回函的26个行业公会来看,荣誉券虽然没有全数售罄,但据不完全统计,《蓝蝴蝶》一剧通过重庆市总商会向各行业公会销售荣誉券的形式至少共收回14400元,虽然数目不大(仅相当于480张30元普通券),但对于还未开演的戏剧,这已经是实实在在的收入了。
那么重庆市商会为什么能向各行业公会推销这些荣誉券呢?
国民政府行政院曾经于1940年10月11日公布了一个《非常时期职业团体会员强制入会与限制退会办法》,该办法列举了包括工会、商会等11种职业团体,并规定“这些职业团体的法定会员或团体,均应加入当地业经依法设立的各该团体为会员,非因废业或迁出团体组织的区域,或受永久停业处分者不得退会”[134]。1942年12月颁布的《加强工商团体管制实施办法》又明确指出:“所谓工商团体指各职业及产业工会,各业同业工会,及县市总工会、商会……”在实施管制时要特别注重:“检查管制区内的公司行号及各业工人,依照非常时期职业团体会员强制入会并限制退会的办法,厉行强制入会,否则即依法予以停业停职的处分……”[135]
从这两部《办法》的规定来看,重庆市商会与各行业公会之间虽然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对于重庆市商会的通知,各行业公会还是不能不重视的,可以说这种通知带有半强制的性质,所以各行业公会还是能认购部分荣誉券。
从《蓝蝴蝶》荣誉券销售的这个个案中,我们可以窥见与荣誉券设置紧密相关的一个要素:一个“强势”的主催方。若想将那些高于普通券数倍的荣誉券销售出去,没有一个“强势”的主催方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主催方不一定是可以向销售对象发布强制命令的机构或个人,但一定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和影响力的机构或个人。如此一来,销售对象即使不会完全听命于该机构,至少不敢看低其影响力而会有所表示。
如果有普通市民要购买这些远远高于普通券的荣誉券,主催方和演出商(放映商)当然是很欢迎的,但是这些荣誉券设置的目标对象却不是普通市民。这一点从其选择投放广告的报纸的细微区别上有所体现。
我们选择了从1940年11月份到1941年3月份的《中央日报》、《大公报》、《新蜀报》三种报纸来观察设荣誉券的募捐演出广告投放情况。一般来看,从11月到来年3月的时段,基本是娱乐演映业经历从复苏到再次逐渐繁荣的时期,而之所以选择这样靠前的年份,是因为荣誉券的设置在靠后的年份中已经有所变质(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专门论述)。选择这三种报纸是因为它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倾向,《中央日报》是国民党机关大报,代表着有政商背景的读者群,《大公报》代表的是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群,而《新蜀报》则完全是一份贴近普通市民的地方报纸。此外,我们关注的基本上是“募捐戏剧”(包括歌剧、平剧、汉剧等),关于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在较早的年份里,“募捐电影”比例较小,而其中设有荣誉券的电影就更少,而“募捐戏剧”的比例即使在较早的年份里也一直较大。
将这5个月里设置了荣誉券又在报纸上投放过广告的戏剧剧目整理如下:
1940年11月
(1)话剧《凤凰城》:由重庆大学友联剧社为捐募寒衣代金在实验剧院演出
《中央日报》:大广告6—8日
《新蜀报》:6日时只有实验剧院其他演出暂停的广告
《大公报》:未知
(2)话剧《夜上海》:新生活妇工队与政治部为征募前方负伤将士药品,12月起,票价调整无荣誉券
《中央日报》:大广告26日/12月3—5日
《新蜀报》:大广告26日/28日/12月2日
《大公报》:未知
(3)话剧《明末遗恨》: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劝进会征募寒衣
《中央日报》:大广告11月29日一12月1日起断断续续出现
《新蜀报》:大广告11月6日
《大公报》:未知
1940年12月
(1)话剧《刑》:中央党部征募××(原文如此)代金公演,28日续演起票价调整无荣誉券
《中央日报》:大广告18、20、21、26、28、31日
《新蜀报》:大广告18日;小广告20—21日;续演大广告28日
《大公报》:未知
(2)歌剧《文天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队新生活妇工队征募××(原文如此)
《中央日报》:大广告20日
《新蜀报》:无
《大公报》:未知
(3)话剧《雾重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队新生活妇工队征募××(原文如此),1941年1月11日续演起票价调整无荣誉券
《中央日报》:大广告20日
《新蜀报》:大广告28日;1941年1月10—17日
《大公报》:未知
(4)平剧:业余联谊社劝募××(原文如此)代金在实验剧院平剧公演
《中央日报》:大广告22—27日
《新蜀报》:广告称因公暂停演出
1941年1月
(1)平剧:四川省银行同人为“出钱劳军”平剧公演
《中央日报》:大广告21—24日
《新蜀报》:无
《大公报》:无
1941年2月
(1)话剧《国家至上》:复旦中学叱咤剧社为响应出钱劳军运动于7日公演
《中央日报》:大广告8—9日
《新蜀报》:无
《大公报》:无(6日报纸缺损,因而无法确定6日广告)
(2)平剧:恒社重庆分社响应出钱劳军运动
《中央日报》:大广告21—25日
《新蜀报》:无
《大公报》:大广告22—25日
1941年3月
(1)平剧:立法院军政部兵工署妇工队筹募抗属事业基金公演
《中央日报》:大广告10—12日
《新蜀报》:无
《大公报》:8、9、12日
(2)话剧《花溅泪》:新生活妇工队与军政部兵役署为筹募抗属工厂基金,19日续演起票价调整无荣誉券
《中央日报》:大广告14、19、21、22日
《新蜀报》:大广告19—23日
《大公报》:大广告20—23日
(3)平剧:重庆市汽车业职业工会为募集福利基金
《中央日报》大广告:24日
《新蜀报》:无
《大公报》:无
(4)话剧《乐园进行曲》:为响应儿童号献机运动公演
《中央日报》:无
《新蜀报》:大广告(未说明有荣誉券)27日/29日
《大公报》:大广告(说明有荣誉券)24日/28日
从我们整理出来的这份清单中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第一,设有荣誉券的戏剧一般都不会放过在《中央日报》上投放广告,14部戏剧中仅有《乐园进行曲》一部没有选择《中央日报》。第二,即使选择在《新蜀报》上做广告,其广告攻势也不如《中央日报》,这体现为:一是《新蜀报》上的广告时间短于《中央日报》;二是只说明“因公演出”,而不言明演出具体信息;三是当票价调整降低不设荣誉券之后,再在《新蜀报》上做大规模广告。第三,《大公报》上设有荣誉券的“募捐戏剧”广告量介于《中央日报》和《新蜀报》之间。
这些特点说明,设荣誉券的募捐演出把目标观众群主体定为在当时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并且有较雄厚经济实力的政商界人士,而不是普通市民。
那么知识分子呢?在战前知识分子属于高收入阶层(此处知识分子主要指大学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等),1931年时,国立大学教授月薪平均为265.6元,省立大学为217.5元,私立大学也有124.3元。[136]即使到1937年重庆市的大学教授也能拿到225元的工资,可以作为参照的是,此时重庆市产业工人和一般职工的工资收入分别为24元和20元。[137]然而随着抗战的深入,教师属于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幅度最大的人群之一,而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幅度却最小。[138]1942年时重庆市产业工人的工资平均为436元[139],而身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的最高工资不过480元[140],虽然这是昆明的知识分子的收入,但凭身在重庆的冰心“每月的薪水只是一担白米”[141]以及“张恨水在四川住了8年,没有做过一件衣服”[142]的状况看,重庆的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也实在算不上“高收入阶层”。
所以陪都时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但知识分子因为其身份地位也属于“荣誉券目标观众”可以考虑的对象,可是却不能成为最主要的目标对象。
回到电影行业,正如前文概述“募捐电影”荣誉券一部分所言,在1943年之前的“募捐电影”中明确设置荣誉券的电影不多。但是我们找到的1943年之前设有荣誉券的电影,其主催方显示出与“募捐戏剧”相似的特点。
比如1940年5月1日在“国泰”上映的《白雪公主》,它的主催方为英国大使卡尔夫人;又比如1942年5月14日在“新川”上映的《小人国》,它的主催方是中美文化协会。这两个主催方都包括了外国友人,而且还是英美国家里有身份地位的人物,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亲英美倾向是众人皆知的,那么这位卡尔夫人和这个中美文化协会在陪都重庆社会的号召力就不可小视了。
至于目标观众群,由于资料的缺损,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两部“募捐电影”的荣誉券设置是针对的哪些人,但至少可以确定《白雪公主》选择了《中央日报》做大广告(不确定它有没有在《新蜀报》和《大公报》上投放广告),《小人国》则是在《大公报》上投放大广告,但没有选择《新蜀报》投放广告(不确定它有没有选择《中央日报》)。这说明,至少它们都没有错过向有能力和有身份的观众兜售产品。
那么,这些设置了“常规”荣誉券的戏剧或电影有没有达到“募捐”的目的呢?
首先,尽管不能确认较早的设置“常规”荣誉券的“募捐戏剧”是否每部都做到了真正的“悉数捐献”,但是其中至少有部分募捐演出是名副其实的。比如1940年11月28日在“国泰”上演的《夜上海》,《中央日报》的广告称该剧为“新生活妇工队与政治部为征募前方负伤将士药品公演”,观看这场演出的观众极为踊跃,“英、美、法、苏、比各国大使,荷兰、墨西哥公使认购荣誉券,英大使卡尔、法大使戈斯默捐款一百元”[143]。同年稍后的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劝进会征募寒衣话剧《明末遗恨》的公演收入了62339.78元,全部作为捐款,而演出开支14875.61元则全部由主催方银行业学谊劝进会承担。[144]而对于“募捐电影”,虽然我们缺少较早的“募捐”实情,但当时的报纸上有时会像1941年12月16日《中央日报》刊登“国泰”与“唯一”映出影片《长空万里》的联合广告那样,在说明该片的映出是为了“响应一元献机运动”之后,再附加一条“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派员在场监票”的说明。[145]这说明早期的“募捐电影”至少也有部分是真正为了募捐的目的,或者说在有“监票”的情况下,不得不实现“募捐”。
可以说“高价”荣誉券销售的成功和募捐目的的实现,与“强势”的主催方关系密切。
此外,“强势”的主催方,不仅有利于销售这些高额荣誉券,也使得申请荣誉券变得更加容易。
荣誉券的设置并非是随着“募捐”自然产生的,荣誉券票价的高低和数目的多寡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所以荣誉券票价数目的设置也完全是“人力”而为,因而与主催方也有莫大关系。这在当时一份申请设置荣誉券的上呈文中有清楚体现:
1943年3月20日—23日,北碚区社会服务处为了筹募事业基金约请教育部实验戏剧教育队在北碚民众会场公演话剧《蜕变》。为了至少达到收支平衡,这次演出准备申请设置荣誉券。申请设置荣誉券的上呈文如下(标点为引者所加,原文无标点):[146]
《论筹办社会服务处因无开办经费实无法成立》前经面呈,钧座允予由职约请友人演剧募款以作服务处开办费用。今已商得友人同意允先垫出排演装置及招待费用一万五千元近期可开始排演,约半月后即能演出。预计上演三日,需用演出费五千元,共计开支约贰万元左右。以过去本市演剧先例,如专靠门票收入实无法筹集巨款,且恐友人垫款亦难归垫。故特呈请钧座除予以演出上一切帮助外,尚祈于有关方面安出一百元一张之荣誉卷(原文如此)二百张,五十元一张之荣誉卷(原文如此)三百张,则可收入三万五千元,估计三日门票最低可收入五千元,共计约可收入四万元。除开支外尚可余贰万元以作服务处经费。
由这份公文,我们可以获得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对于戏剧演出来说,不设置荣誉券,几乎很难实现收支平衡。
第二,申请设置荣誉券的工作主要由主催方完成,那么荣誉券申请能不能被批准下来,能够被批准多少面额的,能够被批准多少张,这些都与主催方的能力紧密相关,换句话说,主催方的身份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荣誉券设置的成败。
当然,也有地位低下的主催方“赚”到相对较高荣誉券的例子,不过,这却是事出有因。国泰大戏院首映卓别林的名片《大独裁者》就是一例。
1941年11月26日开始,“国泰”与“升平”联合首映《大独裁者》。其广告表明该片是由重庆市中小学校奖学金保管委员会为筹募奖学金而特请公映,票价被订为:普通券15元、20元,荣誉券30元、50元。
再来看其他年份11月前后的话剧演出的票价:1942年8月陪都战时人才调剂协会为筹募福利金而请演的《孤岛一女伶》票价为10元、15元、20元三种(未设荣誉券);1943年1月“中制”万岁剧团响应文化劳军运动演出的《蜕变》票价为15元、20元、30元、50元四种(50元为荣誉券)。
按照常理戏剧演出的票价应该比电影高,而《大独裁者》的票价几乎与戏剧等同,而此时其他电影的票价却仍然照旧为8元(1942年11月14日《新蜀报》上“国泰”与“升平”放映《招财进宝》联合广告,票价一律8元)。这说明《大独裁者》一片不仅申请到荣誉券还在普通券上也实行了单独提价,而这次放映的主催方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重庆市中小学校奖学金保管委员会。
实际上在放映这部名片的操作中,从引进拷贝开始的每一个环节,作为院商的国泰大戏院都拿出了足够的重视。
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资料中,有一份1942年国泰大戏院请求为《大独裁者》增价的函件,这份函件不仅说明了《大独裁者》增价的原因为“片租特昂,而各处上演该片者售票均较常增价一二倍以上”[147],并且它还是一份由国泰大戏院总经理夏云瑚亲自上呈给社会局的公文。而夏云瑚是当时重庆市电影戏剧同业公会理事长,他经营的“上江院线”包括了“国泰”、“民众”、“升平”在内的在当时重庆赫赫有名的影剧院,在陪都重庆夏云瑚也算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所以尽管增价要求曾经被重庆市府驳回过[148],但是从放映时的广告看,“国泰”这次的增价要求最终还是被批准。由此,我们也不难推测,此次放映所申请的“高价”荣誉券究竟是由何方力量促成。
对于主催方的作用,我们还有一种立足于以下两份文件的猜测:
仍然以1943年3月20日至23日在北碚民众会场上演的话剧《蜕变》为例。这里有一份《蜕变》在北碚民众会场的售票明细报表[149]。虽然从这张表上不能看出该剧最终有没有成功申请荣誉券,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出它的普通券销售情况。这张表除了票房统计数据,还清楚地列出了娱乐捐数字。该剧应该缴纳的娱乐捐是7140元,而票款总收入是23800元,那么,娱乐捐比例是每票30%。
我们知道,国民政府1942年4月颁布的《筵席及娱乐税法》规定的娱乐税税率就是30%,所谓30%只是上限,即娱乐税税率不得超过30%。“娱乐税率上限”说明在具体每部电影或戏剧实行的娱乐税税率上,是有可以由“人力”所为的空间的。而这个规定直到1943年7月才改到50%[150]。那么1943年3月《蜕变》在北碚的这次演出,从娱乐税正捐(仅仅就查到的资料还不能确定该剧的演出有没有负担娱乐税附加捐)上来说,没有讨到任何减免的便宜。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娱乐税减免是不可能的。
1942年12月9日开始,国立剧专剧团的《哈姆雷特》在“国泰”上演。我们从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该剧的全部支出决算[151]中查到了其应缴娱乐税数目是8600元,而总收入是191902元,娱乐税税率仅仅只有4%多一点,而此时政策规定的娱乐税上限仍然是30%。
《蜕变》30%的娱乐税税率与《哈姆雷特》4%的娱乐税税率的区别,让人不得不怀疑与它们的主催方有极大关系:《蜕变》的主催方是北碚区社会服务处,而《哈姆雷特》的主催方则是全国性的组织全国慰劳总会。那么主催方的身份是否也关系着其“主催”的电影或戏剧最终应该承担的娱乐税率的高低呢?
由于掌握的资料所限,在此只提出这个问题,抛砖引玉,留待后续研究中继续。
4.“弱势”主催方与“低价”荣誉券
前文荣誉券概述的部分,我们曾提到,1943年设有荣誉券的募捐电影的比例大幅提高。荣誉券设置与往年相比也有所变化,具体说来,1943年的荣誉券并没有如往年一般有超出平均票价水平一大截的“荣誉”身份,它仅仅只是借用了“荣誉券”的名称而已。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这种仅仅借用“荣誉券”名头的荣誉券称为“低价”荣誉券。
“低价”荣誉券出现的根本原因,与这个时期“募捐电影”(“募捐戏剧”)其“募捐”动机的改变紧密相关。
前面概述主催方与募捐事由一部分曾经提到,从募捐事由看,年份靠前的募捐事由一般为“为响应……运动募捐”,而主催方也往往是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人物或机构(这也就是前文“高价”荣誉券分析所言的“强有力”的主催方)。年代靠后的募捐事由则是“为……募集事业基金”、修建校舍、赈灾等民间活动,而主催方也更多的是由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湖南旅渝同乡会、新村小学之类的民间小型机构组成。
荣誉券的变化与主催方及募捐事由的变化也并不是孤立的两个现象。
重庆市档案馆保存了1943年时的一份统计表,名为《国泰电影院附加冬令救济逐日一览表(32/11/5—32/12/6)》[152]。该表列出了从1943年11月5日到12月6日“国泰”上映的每部电影的已缴纳的冬令救济捐金额和未缴纳的冬令救济捐金额。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其“备考”栏的说明。在11月5日到6日的《情之所钟》的“备考”栏中注明了“普育小学募捐奉令不加冬令救济捐”;11月11日到18日期间放映了《幻想曲》和《鸳鸯劫》两部影片,这两部影片的“备考”一栏也同样注明“普育小学募捐奉令不加冬令救济捐”。这三部影片都不用缴纳冬令救济捐,而其他影片即使没有缴纳救济捐,也得在后来补上。
此外在我们的考察中还发现了多卷当时各机关单位为募捐娱乐公演而请求减免娱乐税的来往函件。
这些陪都时期的资料都充分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日益加重的娱乐税及其附加捐(尤其是附加捐)可以通过“募捐”的方式得到减轻甚至免除。那么各院商自然会寻求各种机构来做自己的主催方,以达到减免娱乐税附加捐的目的。
于是,在政策的刺激下,以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湖南旅渝同乡会、新村小学、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等小型机构为主的主催方纷纷出现,募捐事由也多以该机构“为……募集事业基金”、“为……募集校舍校具”等模糊或微小的目的为主。
这个时期所谓的“募捐”大都是院商不得已而为之,院商寻找主催方的目的是为了减免娱乐税附加捐,因此在主催方的选择上更加马虎,只求有一个主催方挂名而已,主催方也因而花样百出。相应地,荣誉券票价也减少许多,因为后期的主催方正如前文所举,多是一些民间小型机构,势力弱小,和较早的重庆卫戍总部特别党部、新生活运动总会等权力大名声响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自然在争取荣誉券设置的问题上就比较乏力。
而对于主催方来说,“高价”荣誉券时期良好的市场回报也给了他们“投资”的信心,与寻上门来的院商或是戏剧演出商合作就是一本“以小博大”的生意,更有甚者完全是“无本生意”,既无大风险,还能有大收益。
这里,我们引入当时的三份文件以做详细说明。这三份文件分别是某“募捐电影”主催方的计划书、某“募捐电影”主催方的收支预算表以及某戏剧演出商与主催方的一份合同。
“募捐电影”计划书是由中国社会研究会起草,该会主催了1943年2月在民众影院放映的《刘倩倩》一片。计划书原文如下:
查文化劳军运动其用意在募得之款购备宣传工具以充实前方军中文化食粮,藉以增强抗战情绪争取最后之胜利,发动以来,全国响应。本会为赞助此项运动起见,拟假民众电影院放映电影六日,以收入所得除开支外,悉作文化劳军捐款。其计划分叙如下:
一、地点:青年会民众电影院
二、日期:二月二十八(×)[153]日至三月二日
三、片名:《刘倩倩》
四、票价:定价每票为十二元(印花每票四角八分在内),外加娱乐捐□邮政储□各一元(六角六分)[154],每票合计为十四元。(附注)每票十二元,其中院租每票七元,实得每票为四元五角二分。
五、收入方面:每天四场每场为客满可售九百张票。经折算结果平均每天可售二千五百张票,六天可共计售一万五千张票,共收票价一十八万元。
六、支出方面:①印花费需七千二百元②广告费需六千元③印刷费需二千元④交际费需四千元⑤杂支需一千元⑥院租片租需十万零五千元⑦除开支外可净得五万四千八百元正。[155]
从这份计划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合作信息:
第一,院商与主催方在票房收入上采取分成的方式。主催方“租片”并未采取先付定金的方式,这对主催方来说,避免了分担院商放映的风险;而对院商而言,虽然风险没被主催方分担,但与没有主催方的情况相比,因为有票房分成(计划书中院商分成的部分被成为“院租”、“片租”),至少是可以保证没有损失的。
第二,票价中包括了印花税、娱乐捐、邮政储蓄金、院租和主催方所得五项,而支出方面却有印花税、广告费、印刷费、交际费和杂支、院租六项,也就是说没有包含在票价中的广告费、印刷费、交际费和杂支这四项要由主催方负担。这四项支出加起来一共一万三千元,而主催方的预算净收入是五万四千八百元,以一万三千元的投资“搏”四倍多的盈利,这对让“生意”找上门来的主催方来说是极有吸引力的。
第二份文件是《市立新市场镇中心学校造呈电影募捐收支预算表》(见表5-12)。
表5-12 市立新市场镇中心学校造呈电影募捐收支预算表

资料来源《市立新市场镇中心学校造呈电影募捐收支预算表》,0060-14-77卷,重庆市档案馆。
这张收支预算表也印证了前例显示的院商与主催方对票房采取分成的方式来获取收入。与前例不同的是,做出这份预算表的新市场镇中心学校将杂项开支也算到票价分配中,这样一来,主催方连小额的杂项支出都可以由票价来补偿,承担的风险更小,却可能得到53000元的收益。
与新市场镇中心学校相比,第三份文件中的主催方则完全是在做“无本生意”。
这份文件是1942年8月由施超与陪都战时人才调剂协会签署的关于话剧《孤岛一女伶》的合同。该剧当月在抗建堂演出的大广告从8月6日起出现在《大公报》上。合同原文如下:
立合同人:战时社会事业人才调剂协会力行联谊社(以下简称
甲方)
施超(以下简称乙方)
兹因甲方为筹募福利事业基金,征得乙方同意合作公演话剧《孤岛一女伶》,经双方议定条款如下:
一、公演日期定为三十一年八月八日至八月十六日,共九场。
二、公演之一切筹备排演、上演时之前后台工作均由乙方负责进行,甲方有监督之权。
三、此次公演之排演用费、布景用费、院租、电费、职演员酬劳、捐税以及一切开支均由乙方自行筹措担负。上演之全部座票收入归乙方作为开支。
四、此次公演,每场划最优座位五十席出售荣誉券,全部所得除印刷及特别开支外,所余乙方得分半数抵充座票收入之不足,其余半数归甲方所得。
五、此合同自订立之日起生效。
立合同人(www.zuozong.com)
甲方代表:李□勒
乙方代表:施超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一日[156]
这份合同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孤岛一女伶》的约定演出时间是八月八日,而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八月一日。如果不是乙方施超的演出团能在七日之内排演出一出话剧,那就是这出戏剧在排好之后才仓促找到了“预订”它的单位。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演出放映事业中主催方处于“卖方市场”的局面。
第二,主催方战时社会事业人才调剂协会力行联谊社不负担演出的一切费用支出。这说明主催方完全不需要承担演出的任何风险。
第三,合同规定该剧每场公演都要划出50席作为荣誉券,荣誉券收入的一半归主催方所有。尽管后来的报纸广告上该剧的票价是10元、15元和20元,没有荣誉券的设置,但是这份合同说明了主催方在跟演出商合作之初的本意是要从演出收入中分一杯羹。至于最后报纸广告上刊出的票价,有可能是后来主催方与演出商之间又有新的协议,或是报纸上没有列出荣誉券。
总的来说,1943年大量出现的“募捐电影”应该被视为在捐税加重的情况下,由院商主动寻求的解决之道。但同时院商与主催方的合作又是双赢的,院商可以获得捐税的减免,还能保证收入;主催方则是以自己的“名头”或者再加上极小的投资试图赚取更大的收益。
【注释】
[1]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37—1949)》,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2]孙科:《发刊辞》,载《中苏文化》,第1卷第1期,1936年5月15日,第1页。
[3]顾执中:《回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5]〔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6]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1 页。
[7]夏衍:《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载《夏衍研究专集》(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页。
[8]虞吉:《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第81页。
[9]〔苏〕包包夫著:《苏联电影中的十月主题》,苏凡译,载《中苏文化》,“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11月7日,第222页。
[10]〔苏〕爱森斯坦:《苏联电影二十年》,贺孟斧译,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150页。
[11]VOKS原稿:《苏联电影艺术家》,芳蓁译,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161页。
[12]〔法〕Rudolf Muller:《苏联的戏剧与电影》,微杰译,载《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3卷第4期,1939年1月1日,第24页。
[13]《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致苏联电影界书》,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2页。
[14]《全苏电影从业员复中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的信》,载《中苏文化》,第10卷第1期,1942年1月1日,第31页。
[15]施焰:《三则建议——给中国电影界》,载《扫荡报》,1938年12月4日。
[16]集体影评:《〈彼得一世〉在中国观众面前》,载《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3卷1、2期合刊,1938年12月1日。
[17]田汉:《怎样从苏联戏剧电影取得改造我们艺术文化的借鉴》,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4页。
[18]郑伯奇:《苏联电影给予中国电影的影响》,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17页。
[19]史东山:《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21页。
[20]史东山:《抗战以来的中国电影》,载《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25日,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421页。
[21]王平陵:《从苏联电影谈到中国电影》,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24页。
[22]葛一虹:《苏联电影与苏联戏剧给予了我们什么》,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10页。
[23]“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纪录,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5页。
[24]罗静予:《论电影的国策》,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2页。
[25]宋之的:《略论电影通俗化问题》,载重庆《扫荡报》,1939年4月10日,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26]向锦江:《论电影的民族形式》,载《国民公报》,1941年6月8、15、22日,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27]雷兴华:《重庆电影在1940年》,载《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28]虞吉:《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第85页。
[29]廖全京:《大后方戏剧论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30]转引自廖全京:《大后方戏剧论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31]马彦祥:《抗战戏剧发展的检讨(上)》,载《大公报》,1940年1月13日。
[32]马彦祥:《抗战戏剧发展的检讨(下)》,载《大公报》,1940年1月16日。
[33]虞吉:《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第86页。
[34]虞吉:《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第87页。
[35]郑伯奇:《苏联戏剧给予中国抗战戏剧的参考》,载《中苏文化》,第4卷第2期,1939年9月1日,第20 页。
[36]凌鹤:《中国戏剧运动与苏联戏剧》,载《中苏文化》,第4卷第2期,1939年9月1日,第24—26页。
[37]王平陵:《苏联的电影戏剧在五年计划中的运用》,载《中苏文化》,第4卷第2期,1939年9月1日,第32页。
[38]《中华全国戏剧抗敌协会致苏联戏剧界书》,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1页。
[39]《全苏电影从业员复中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的信》,载《中苏文化》,第10卷第1期,1942年1月1日,第31页。
[40]《中苏文化》,第10卷第1期,1942年1月1日。
[41]《中苏文化》,第1卷第1期,1936年5月15日。
[42]《中苏文化》,第1卷第2期,1936年。
[43]《中苏文化》,第20卷第1期,1949年1月30日。
[44]〔美〕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徐建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45]钟大丰:《作为艺术运动的30年代电影》,载陆弘石主编:《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46]〔苏〕普多夫金:《电影剧本》,载《普多夫金论文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119、120页。
[47]田汉:《田汉文集》第14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48]郑伯奇:《两栖集》,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146页。
[49]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38、239页。
[50]戈公振:《从东北到苏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51]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52]高文波:《抗战时期俄苏文学译介述略》,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766页。
[53]惠元:《〈十三勇士〉观后》,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日,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54]惠元:《〈血肉换自由〉观感》,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2月12日,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55]凌鹤:《推荐〈夜莺曲〉》,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4月19日,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56]吴克坚:《从〈马门教授〉影片说到我们的外交方针》,原载《新华日报》,1939年8月16日,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57]向锦江:《推荐〈生路〉》,原载《新华日报》,1941年5月27日,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页。
[58]沙雁:《评苏联名篇〈雪中行军〉》,原载《文艺月刊》(特刊)第2卷,1938年,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59]陶雄:《〈列宁在1918〉观后感》,原载《新蜀报》,1942年2月4日,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
[60]凌振元:《中外电影简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61]黄天佐:《苏联电影的新阶段》,载《中苏文化》,第1卷第3期,1936年,第4页。
[62]阳翰笙《:我对于苏联戏剧电影之观感》,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28页。
[63]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编:《苏联电影史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64]何必昵:《杂谈〈塞上风云〉》,原载重庆《扫荡报》,1942年3月1日,转载重庆文化局编:《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453页。
[65]李道新:《中国电影史1937—1945》,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66]何非光:《苏联电影给我们的印象》,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第48页。
[67]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68]葛一虹:《从〈华北是我们的〉与〈好丈夫〉说到我们抗战电影制作的路向》,原载《新华日报》,1940年2月22日。
[69]徐世骐:《我在重庆看了70年电影》,载《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70]田苗:《我对战时重庆电影的认识》,载《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71]虞吉:《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第86页。
[72]《重庆观众烧掉〈木兰从军〉》,见《艺林》,第68期,1940年2月。
[73]见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电影·花木兰陪都历险记》中石曼的采访,重庆卫视2011年8月12—22日播出。
[74]《〈木兰从军〉在渝被焚事件特辑》,载《电影世界》,第11期,1940年4月。
[75]见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电影·花木兰陪都历险记》中石曼的采访,重庆卫视2011年8月12—22日播出。
[76]《重庆观众烧掉〈木兰从军〉》和《张善琨卜万苍对〈木兰从军〉被焚事件声明》,见《艺林》,第72期,1940年4月。
[77]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78]《张善琨卜万苍对木兰从军被焚事件声明》),见《艺林》,第72期,1940年4月。
[79]《陈云裳在上海半年》,见《艺林》,第69期,1940年3月。
[80]李道新:《中国电影史1937—1945》,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81]《扫荡报》,1939年1月15日。
[82]《群丑跳梁 臭不可闻》,载《电影纪事报》,第8期,第5页。
[83]《胡蝶归来有感 且看后效如何》,载《电影纪事报》,第8期,第5页。
[8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7页。
[85]〔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86]《新蜀报》,1940年10月11日。
[87]《大公晚报》,1946年3月25日。
[88]方井:《月薪数百元够买几包烟?——心酸的纪录》,载范国华等编辑:《抗战电影回顾》,重庆市文化局1985年印行,第89—90页。
[89]石曼,余叙昌:《又见大后方影剧明星》,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90]《中国电影》,第1卷第2期,1941年2月1日,重庆。
[91]参见顾倩:《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1927—193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版;冯俊峰:《百年光影的民国记忆》,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92]汪潮光:《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载《电影艺术》,1997年第3期。
[93]陈兰荪:《我所知道的中制和中电两大影剧厂》,载《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94]吴克坚:《从〈马门教授〉影片说到我们的外交方针》,载《新华日报》,1939年8月16日。
[95]吴克坚:《从〈马门教授〉影片说到我们的外交方针》,载《新华日报》,1939年8月16日。
[96]张红:《抗战中内迁西南的知识分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转引自孙晶:《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97]司马文森:《我对苏联电影的观感》,载《中苏文化》,第7卷第4期,1940年10月10日。
[98]苏光文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99]苏光文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100]〔美〕C.C.艾伦、D.弋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
[101]葛一虹:《从〈华北是我们的〉与〈好丈夫〉说到我们抗战电影制作的路向》,载《新华日报》,1940年2月22日。
[102]李道新:《中国电影史1937—1945》,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103]葛洪保:《云南影视业再现生机》,《云南广播电视报》,2005年2月23日。
[104]李道新:《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独特处境及历史命运》,《当代电影》,2001年第6期。
[105]虞吉:《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106]原载《大公报》,1940年1月13、15、16日。
[107]原载《大公报》,1940年1月17、19日。
[108]原载《扫荡报》,1939年4月10日。
[109]任一宁:《抗战时期重庆电影概述》,载《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110]李道新:《中国电影史1937—1945》,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 页。
[111]刘立滨:《电影市场学》,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112]详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113]《每周电影》,第2期,载《中央日报》,1940年12月21日。
[114]《新蜀报》,1940年12月29、30日。
[115]《每周电影》,第1期,载《中央日报》,1940年12月7日。
[116]虞吉:《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117]余纪:《抗战陪都电影市场的好莱坞景观》,载《电影艺术》,2006年第5期。
[118]熊学莉:《陪都时期的电影宣传研究》,西南大学电影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10页。
[119]“募捐电影”资料出自刘畅:《陪都重庆抗战中期放映业研究》,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
[120]1943年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的统计。
[121]1942年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新蜀报》和《大公报》的统计。
[122]参见何云贵:《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戏剧演出》,载《戏剧文学》,2005年第8期。
[123]参见虞拱辰主编:《中国赋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124]参见金鑫、刘志城、王平武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316页。
[125]参见《重庆市地方自治五种税捐收入比较表》(1943年),载金鑫、刘志城、王平武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126]《重庆市财政局税捐征收处三十三年一至六月份各项地方岁入超收明细表》、《重庆市财政局税捐征收处三十三年七至十二月份各项地方岁入超收明细表》,0064-8-2317卷,重庆市档案馆。
[127]参见《重庆市地方自治五种税捐收入比较表》(1946年),载金鑫、刘志城、王平武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128]金鑫、刘志城、王平武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129]参见《中央日报》,头版,国泰大戏院《豆蔻年华》广告,1941年4月19日。
[130]参见《新蜀报》,头版,唯一大戏院《凯赛林女皇》广告,1942年1月28日。
[131]《八年抗战,成都人记忆中留下这些关键词》,载《成都日报》,http://www.newssc.org/gb/Newssc/meiti/cdrb/zk/userobject10ai729884.html?o9zEb=mVjZH1mS4aS1.
[132]参见《中央日报》,1940年11月10—16日。
[133]参见0084-1-414卷,第1—72页,重庆档案馆。
[134]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35]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36]参见马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37]参见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138]参见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139]参见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表7-2,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140]参见马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215页。
[141]参见马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142]参见马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143]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44]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45]参见《中央日报》,头版,国泰大戏院院、唯一大戏院联合广告《长空万里》,1941年12月16日。
[146]《论筹办社会服务处因无开办经费实无法成立》,0081-4-2289卷,重庆市档案馆。
[147]《国泰为开映〈大独裁者〉请增票价由》,0060-1-338卷,重庆市档案馆。
[148]《重庆市府指令重庆市社会局》,0060-1-338卷,重庆市档案馆。
[149]《北碚民众会场售票明细报表》,0081-4-2289卷,重庆市档案馆。
[150]参见金鑫、刘志城、王平武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151]《全国慰劳总会主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附设剧团为响应文化劳军旅渝公演〈哈姆雷特〉全部支出决算》,0060-1-513卷,重庆市档案馆。
[152]《国泰电影院附加冬令救济逐日一览表(32/11/5—32/12/6)》,0053-2-1127卷,重庆市档案馆。
[153]原文在“八”字旁有“×”符号,似意为“二十八日”有误。查当月报纸,该片上映时间为二月二十五日。
[154]原文在“一元”旁边加入了“六角六分”的文字。但实际上最后合计出的“十四元”仍然是按照“各一元”计算的。
[155]《中国社会研究会响应文化劳军筹募慰劳金计划书》,0060-1-513卷,重庆市档案馆。
[156]《战时社会事业人才调剂协会与施超订立公演合同》,0060-1-513卷,重庆市档案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