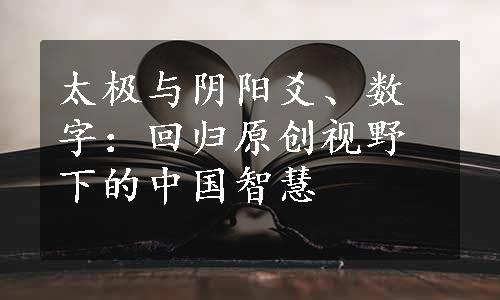
在六十四卦中,既然没有也不可能有“易道”的标示,但按《周易大传》所说,卦爻象却是作为“易道”的“太极”所生,并对“易道”有所显示,这就说明,“易道”不可能离开六十四卦,而是隐于其中。不过,在《周易》体系中,存在三种符号体系。一种是阴阳爻符号体系,也是最根本的体系。另一种是数字符号体系,例如构成卦象爻位的初、二、三、四、五、上;揲筮中的象数;在阴阳爻之外,用不同的奇偶数字记载不同卦的方式以及“变卦”与“卦变”之数,等等。第三种,就是卦爻辞组成的文字符号体系。显然,在这三种符号体系中,阴阳爻符号体系是最抽象的符号体系,但比起另外两种符号体系却具有最深广的包容性。另外,例如作为标示爻位的数字符号,介于阴阳爻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爻位数字所标示的,既是时间坐标也是空间坐标。例如乾卦的“六龙”,都是时空并存于每一龙的显示。在这种时空交会中,不仅能够看到不同季节的展现,而且不同季节的天地人“三才”之景象也会或隐或显地展现出来。人们飘逸在春风中,潇洒自在;而在寒冬冰雪中,瑟缩不能舒展。在夏日的骄阳下,无风的烤晒,让人喘不过气;可是当金秋来临,看到丰收成果,一切辛苦就都抛到脑后。洞房花烛,谁能忘记那幸福燃烧的时光呢?一旦碰到意外丧偶,孤独和绝望也会撕裂心肺!成功的趾高气扬和失败的灰心丧气,展现人生常态,然而在消沉之后,你看他又踌躇满志和野心勃勃了。如此等等,岂不都是显示在这不同的时空交会之中吗?也许,海德格尔的“Dasein”的“Da”,与这里爻位数字所标示的意思具有可以沟通的境域。事实上,活着做事和享受生活的人,总是处于不断变换的时空坐标或交会中。从这个最基本的时空坐标出发,去推测人的可能态势和走向,正是《周易》最能启迪人的思想之一。比起前两种符号体系,作为系辞的文字符号体系,虽然具有明确具体的显示性,但在对于“易道”的显示上,却容易受局限,甚至弄不好,还会“言不尽意”,导致“道可道,非常道”。
这里说数字符号介于卦爻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是说在表意上数字已经不像卦爻符号那么抽象,但也不像文字符号那么具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这里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如果当年没有留下卦爻辞,那就真会像顾颉刚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变成谁也解不开的谜,变成不可理解的无字天书。因为,它们是最抽象的符号,比现在计算机“二进制”的0、1还抽象(0、1还有数量意义可言)。但正是这种最抽象的卦爻符号,可能适合于载“道”。因为,所谓最抽象,是从“有”以至可以抽象到“无”。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篇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黑格尔那里,经过对“有”抽象,到最后“有”变成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有”,这时“有”就过渡到“无”。但是,“象思维”的“抽象”与黑格尔的概念思维的“抽象”,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因为“象思维”所进到的“无”,不是黑格尔那种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即不是作为向获得丰富规定性的具体概念进展的起点之“无”,而是作为万事万物“原发创生”之源的“无”。所以,“象思维”在卦爻符号创造上的“抽象”,是破除概念思维包括数字思维、回归“原发创生”之源的一种“悬置”的功夫。与现象学还原的功夫有一点相似性,但又不可同日而语。现象学还原在胡塞尔那里,像康德那样,是为了给陷入危机的形而上学寻找一个解除危机的基础,即康德所说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基础。而“象思维”则是回归思想文化的“原发创生”之源。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对“存在”(或译为“是”)即始于古希腊einai(拉丁文esse,英文to be,德文sein,法文être)意义的探索,比起从康德到胡塞尔的探索,具有思想突破的价值。海德格尔提出“缘在”( Dasein) ,去存在( zusein) ,特别是提出“自身缘构发生”( Ereignis) ,可以说,都是力图回到思想文化“原发创生”之源的精神求索。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非常重视接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启发,所以他对于“无”的领会,也超越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观点。
事实表明,要展开从“太极”到“八卦”再到“六十四卦”的“易道”,没有数字符号的中介,就不可能有从“太极”这个“大象无形”或“无物之象”到具象的过渡,也就不可能作具体的“观象系辞”。这种在最抽象的卦爻符号与具体的文字符号之间的数字符号,在“易道”和道家之“道”的展开过程中,正是显示从“无”到“有”的过渡或者“有生于无”的过渡。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已经看到一(太极)、二(两仪)、三(作为生四象的两仪) ,而“四象”、“八卦”则已经进达具象,如方位和万事万物。在道家老子那里,这种数字所显示的从“无”到“有”的过渡,更为明显。如老子所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在这里,“易道”的“太极”与老子的“道”还有所区别。老子的“道生一”,与作为“有”的“一”相对的“道”当是“无”,而“易道”之“太极”则是“有”与“无”的合体,所谓“无极而太极”。“太极”这个合体比较具体的展现,就是“两仪”即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似乎可以从这种描述中加以领会。(www.zuozong.com)
同老子“道”之“三生万物”相比,“易道”则是“阴阳生万物”。阴阳既然是“易道”之“太极”比较具体的展现,它就比较具体地包含有“易道”“原发创生”的生机。或者说,作为“易道”最终根源的“无”,这个具有无限“原发创生”生机的“无”,就隐含在“一阴一阳”之中。正如著名易学家胡煦所言,“须知其来,俱由太极天心而来。所以方来之爻,俱名曰初。无一卦无初爻,则无一卦无太极”。阴阳爻作为《周易》六十四卦体系的基础和灵魂,具有“原发创生”的生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与“无”合体的“太极”隐含于阴阳之中。阴阳所展开的无限形式的辩证运动,其根本的动因也在于此。
无论是“太极”还是“阴阳”,在“象思维”里都是表述“易道”的始源性范畴。任何始源性,都具有神秘性。但是,只要这种范畴具有解释的合理性,就应当承认这种“神秘”的合理。在这里,阐发这种始源的“神秘”,并不意味着迷信,而是表明始源的深邃甚至深不可测。对于始源要求经验主义的实证或科学主义的证伪,都是离开始源的本真本然。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虽然解构了形而上学的虚构,但是最终却不能解构掉形而上学,其原因就在于任何哲学的真理追求,总是要不断回到始源,从那“神秘”中寻找开拓新思的刺激。即使从知觉经验出发的梅洛庞蒂,也不能不重视始源。他说:“哲学在能够说出真理时,不应把哲学本身当做知识,意味着哲学是不断更新的对自己开端的体验,意味着哲学整个地致力于描述这种开端。”不断回到“始源”或回到“开端”,之所以必需,就在于“始源”或“开端”就像一条河流的源头。一条河的存在,取决于“始源”或“开端”的源头活水。回到“始源”或“开端”,就是要护持和开发源头活水,以便使哲学和思想之河得以长流和常清。实际上,追溯源头的现象,不止是哲学,而且整个文化都是这样。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甚至也包括科学,在发展过程中都要不断追溯源头,以便在神秘深邃的源头那里寻找获得新发展的刺激。这也如梅洛庞蒂在谈到现象学工作时所说的,“现象学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普鲁斯特的作品、瓦莱里的作品或塞尚的作品一样,在辛勤耕耘——靠着同样的关注和同样的惊讶,靠着同样的意识要求,靠着同样想理解世界或初始状态的历史意义的愿望。哲学在这种关系下与现代思想的努力连成一体”。在这里,梅洛庞蒂说到“初始状态的历史意义”,其实“初始状态”作为“始源”,与所流淌的“一条河”构成一体,就是说传统不仅是历史,也与现实一体相连。所以,对“初始状态”的追溯,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