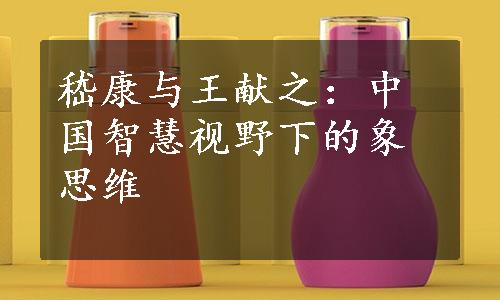
嵇康,字叔夜,三国末期的大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反名教的精神,因此为司马氏门阀士族统治者所痛恨,并最终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之罪被杀。在临刑将死之时,嵇康表现得凛然正气,从容自若。《世说新语·雅量》对此有如下生动描述:“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这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叛精神,特别是面对死亡的从容及其悲剧美,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震撼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往人们大多只知道嵇康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精通音乐,而不知道嵇康还是草书大家。并且,嵇康草书的地位之高,按张怀瓘的排序,仅在张芝之下,而居王献之之上。从这种排序可以看出张怀瓘对嵇康草书评价之高。
在《书议》中张怀瓘有一段对比王羲之(逸少)草书与嵇康(叔夜)草书的议论,很值得玩味。他说:“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贤人君子,非愚于此而智于彼,知与不知,用与不用也。书道亦尔,虽贱于此,或贵于彼,鉴与不鉴也。嵇叔夜身长七尺六寸,美音声,伟容色,虽土木形体,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加以孝友温恭,吾慕其为人,藏有其草书《绝交书》一纸,非常宝惜。有人与吾两纸王右军书,不易。近于李造处见全书,了然知公平生志气,若与面焉。后有达志者,览此论当亦悉心矣。”在这里,张怀瓘提出如何鉴别书道的标准问题。贱此贵彼,取决于鉴别的标准不同。在比较王羲之草书与嵇康草书时,张怀瓘贱王羲之而贵嵇康,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要问:如何领会张怀瓘所用的标准呢?对于王羲之草书,他认为“不足贵”,理由在于缺乏“风骨”,所谓“有女郎材,无丈夫气”。由此可知,张怀瓘对于草书评价的标准,可以说全在“风骨”如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隐去了对嵇康草书的正面评价,而只是以指出王羲之草书缺点这种反衬的方式,来肯定嵇康之草书。不过,张怀瓘从草书的“风骨”去看书家的“风骨”,从而使这个“风骨”标准更加深厚。他对于嵇康的人格魅力,十分倾倒。他倾慕嵇康的为人,所谓“美音声,伟容色”、“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还只是外表的描述。对于嵇康反传统、抗拒司马氏门阀统治者和临刑从容的凛然气节,他只在提出嵇康所写的《绝交书》时,含蓄地说了一句“了然知公平生志气”。张怀瓘这种含蓄的笔法说明,他对于嵇康在《绝交书》中对统治者的抗拒和借历史所作的尖锐批判,只能“了然知”,而不能宣扬。即使是大唐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对于抗上和反叛传统的思想也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张怀瓘还是用曲笔,把嵇康草书的“风骨”与其人格的“风骨”一体写出来了。他对嵇康人格与书格一体之倾慕尤其表现在,他有一纸嵇康所书《绝交书》的书法作品,有人想用两纸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与他交换,却遭到他的拒绝。这一点,很重要。书法艺术既然是抒情写意的艺术,那么从事这项艺术者的品格如何,也不能不与其所创造的作品密切相关。
张怀瓘如此倾慕和重视嵇康的草书,也含有他对于书法艺术灵魂——“写意”——的深刻认识。如前所述,不拘一格的反叛传统的精神或超越现存规则的革新精神,乃是“写意”之魂的重要内涵。张怀瓘在“二王之妙”中特别推崇王献之的,也正是这种“写意”之魂。也许是出于这种原因,张怀瓘一有机会就要推崇嵇康和王献之。例如,在《书断》中他称赞嵇康:“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临不测之水,使人神清;登万仞之岩,自然意远。”对于王献之,称其去世后仍有俊杰之士继承,谓:“子敬没后,羊薄嗣之。宋齐之间,此体弥尚,谢灵运尤为秀杰。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同时,他还对王献之章草书的创新在实用和书道两方面的积极意义大加颂扬。就实用的意义,他指出:“或君长告令,公务殷繁,可以应机,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惟叙事。披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用今天的话说,王献之所创造的章草书体,简便和加快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公务可以“应机”,私事可以“含情”“若面”。尤其是对于书道的弘扬和深化,张怀瓘对于王献之更是赞赏有加。他指出:“妙用玄通,邻于神化。然此论虽不足搜索至真之理,亦可谓张皇墨妙之门。但能精求,自可意得,思之不已,神将告之,理与道通,必然灵应,有志小学,岂不勉欤!”就是说,王献之对书道的贡献,就在于“玄通”、“神化”。什么意思?这里所说的“玄”和“神”,就是孙过庭所说的“风骚之意”与“天地之心”,也就是以诗意之心而与大“道”相通。因此,能够这样“玄通”和“神化”,就能“张皇墨妙之门”,或悟而真正入书道。但是,这种体悟需要下功夫,要“精求”,要“思之不已”。只有这样,才“自可意得”或“神将告之”。(www.zuozong.com)
不难看出,“写意”之魂表现在反传统和创新的统一。在这里,反传统在于反对传统的僵化,而不是简单地对传统加以否定。因此,反传统的实质是“扬弃”( Aufheben)传统,或者说是使传统在“扬弃”中有新的发展,而不至于僵化而衰亡。创新则是这种“扬弃”传统的必然结果。例如王献之,“幼学于父,次习于张,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私心,冥合天矩,观其逸志,莫之与京”。张怀瓘在《书断》中的描述,进一步透视出王献之行草书的奇雄,如说:“至于行草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怀瓘还写出了王献之特立独行和不为权贵折腰的人格魅力。有三件事可以见出这种人格。其一,“初娶郗昙女,离婚”。其二,“人有求书,罕能得者,虽权贵所逼,了不介怀”。具体事例如:“谢安请为长史,太康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其三,“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离婚之事在魏晋隋唐,虽然允许,但仍然是社会突出事件。在这件事情上,既可看出那时中国在两性关系上,比起宋代以降,还存在可以选择的一定自由,而王献之的表现则说明,他在爱情和幸福的追求上是相当解放、独立和自由的。至于其二,对于求书特别是权贵求书,王献之的态度则显示出他作为士者的刚正不阿和对艺术崇敬的伟大人格。真正的艺术是创作,而创作是有条件的,是不可以随意为求者之求而作的。这种所求,之所以为王献之所鄙视,就在于所求者,大多附庸风雅,是为一己名望等私心所求,而非对艺术的理解和热爱。王献之对谢安的严厉批评,就是对这种权贵私心和附庸风雅的痛斥。其三所表现的,则是王献之作为真正艺术家的品格。所谓“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说明艺术创作不是像工匠那样,可以随时随地而为的事情。相反,艺术创作,必须有“兴会”,有“触遇”,而这种“兴会”和“触遇”,不是经常有,而是“偶其”有。至于这种“兴会”和“触遇”,就是艺术家诗意诗心的萌动,或如孙过庭所说的“取会风骚之意”,“物我两忘”而通于“天地之心”。张怀瓘说王献之“皆发于衷,不从于外”,即此之谓也。
张怀瓘在高度评价嵇康草书和王献之章草的成就时,还特别把他们做人的高尚品格加以突出。那么问题是,书法艺术作品的品格是否与其创作者的品格相关呢?应当说,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前面玉涛特别强调王羲之以《丧乱帖》为代表的杂帖的书法成就,就在于晚年的王羲之经过国事家事连续不断的悲剧,使他原本“骨鲠高爽,不顾常流”的品格,比写《兰亭序》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嵇康的《绝交书》神韵精绝,更受到张怀瓘的珍爱和敬重,也正是在于嵇康的书法及其内容所表现的与他的那种不畏强暴而大义凛然的品格,是完全一致的。张怀瓘有点近乎偏爱王献之的章草书,也与他高度尊崇王献之的人品有关。在王献之的品格中,确乎能看到与嵇康品格一致的方面,特别是在刚正不阿和抗拒强权方面,两人确实是站在了同一人格的历史高度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