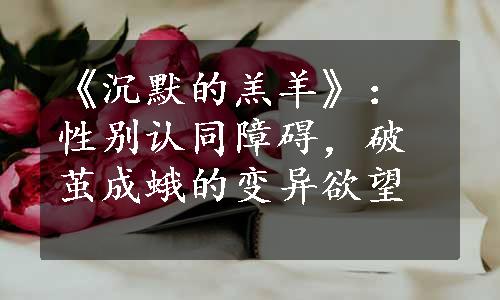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乔纳森·戴米执导,1991年于美国上映,118分钟。
朱迪·福斯特、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
获第64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5项奖项。
《沉默的羔羊》是一部由托马斯·哈里斯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由英国著名男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和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朱迪·福斯特联袂主演,由乔纳森·戴米导演。1991年全球上演之后,在1992年奥斯卡之夜大放异彩,荣获第6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五项大奖,这种殊荣在世界电影史上罕见。该影片与其说是一部节奏紧张、恐怖的惊险电影,不如说是一部带着浓浓精神分析色彩的经典之作,被称为“迄今为止好莱坞影史上最成功的一部精神分析影片”。影片将大量的对话和动作置于幽闭的静态环境中,以心理分析为核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不同人物角色的个性特征和内心的变化,以及变态心理的蜕变过程,让观众在一种相对比较阴暗和压抑的气氛中感受心理悬疑片的独特魅力。所以,长久以来,该影片作为一部经典的心理恐怖片被人们谈论和铭记。影片中几个重要人物如克拉丽丝、汉尼拔、“野牛比尔”等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该片荣获奥斯卡五项大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剖析,并通过电影艺术将一个个人物活生生地展示在银幕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影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克拉丽丝·史达琳、汉尼拔·莱克特、“野牛比尔”,都存在着不同的心理疾病,他们的行为的动力依据来自精神分析学说。
故事从朱迪·福斯特扮演的联邦调查局见习特工克拉丽丝·史达琳结束受训被分配到联邦调查局工作开始。她所在的城市发生了一系列命案,凶手是一名专门杀害年轻女性并剥去部分皮肤做衣服的变态杀手“野牛比尔”,已经有不少年轻女子死在他手上。为了解凶手这一特殊的变态心理,寻找出隐藏巧妙的“野牛比尔”,受FBI负责人杰克·克劳福德之命,克拉丽丝·史达琳的主要任务是去到戒备森严的巴尔迪摩联邦监狱医院访问一位曾经名噪一时、而今被关押在此的精神病专家汉尼拔·莱克特博士,以获得罪犯的心理行为资料。
汉尼拔·莱克特博士是一位思维敏捷、知识渊博、足智多谋、沉着冷静并有严重精神变态的中年男人,他有食人肉的恐怖嗜好。史达琳的思维能力完全不是汉尼拔的对手,汉尼拔要求克拉丽丝·史达琳说出自己童年的个人经历供他分析,经过接触和交锋,史达琳为博士的智慧所折服,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既同情又憎恨的微妙感情。汉尼拔被史达琳的真诚和纯真打动,在多次接触中,他断断续续地给史达琳提供了一些关于“野牛比尔”的线索。他精准的心理分析使变态杀人犯“野牛比尔”的特征渐渐明晰起来。精明的汉尼拔准确地分析了“野牛比尔”的心理特征,逐渐缩小犯罪嫌疑人的范围,并不断为史达琳提供破案线索。在汉尼拔的帮助下,史达琳终于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名叫詹姆的人身上。因为史达琳发现他曾经从外国带回一箱苏里南的毛毛虫,他还去过变性医院试图变性但遭到了医生的拒绝。此时,参议员的女儿凯瑟琳失踪了,在他的指点下,史达琳越来越接近凶手,在“野牛比尔”的住所经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对抗后,史达琳终于击毙了“野牛比尔”,救出了凯瑟琳。“野牛比尔”虽然被击毙了,但是更为恐怖的事件出现了:汉尼拔设法获得转移出监狱的机会,杀死了看管他的几个警察,逃出了戒备森严的铁笼。在庆功会上,史达琳接到汉尼拔的电话,更危险的杀人狂汉尼拔获得了自由,危险笼罩着整个社会……
《沉默的羔羊》是一部心理悬疑片,影片为观众设下了诸多悬疑。集智慧和邪恶于一身的汉尼拔,为什么会患上食人肉的怪癖?史达琳要抓捕的连环杀人凶手“野牛比尔”为什么会有如此残酷而怪异的行为?这些悬疑引导着观众一步步观看下去,直到最后谜底揭开。
“野牛比尔”是本片中恐怖的来源,他的形象源于现实中连环杀人案的三位凶手,分别是引诱女性进入货车的特德·邦迪、将被绑架女性囚禁于地窖中的加里·海德尼克和剥人皮的艾德·恩格。源自现实形象的影片带来的恐惧感更为真实,影片塑造的“野牛比尔”真实名字叫詹姆·伽姆,是一个专门杀害年轻女人并剥去她们皮肤的变态连环杀手,穿14码鞋的较肥胖女性成为他猎杀的目标。他生活在既阴暗又凌乱的地下室中,其间有腐烂的尸体、发育中的群蛾、弥漫在空气中的狂躁的音乐,他异装癖的举动,足以令人感到恐怖和阴森。“野牛比尔”的杀人手段极为残忍,每次杀害被绑架的女性时,都将她们的皮剥下,剥皮只是为了给自己缝制一件完美的女性“皮衣”。已经有5名少女被害。
从汉尼拔那里得知,连环杀人凶手“野牛比尔”是一名异性癖者,即性别认同障碍患者。比尔的童年非常不幸,他的母亲很可能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成长中的个体都渴望得到母亲的关爱。经常遭到继母虐待的比尔,讨厌自己的男性身份而渴望变成女性。比尔虽然从心理上已经完成了向女性角色的转变,但是在生理上依然是男人身体。成年后的“野牛比尔”曾去过三家变性医院希望变性,但在遭到这些医院的拒绝之后,他突然意识到他的转变无法通过他人来完成。极度痛苦的比尔开始寻求其他的出路,寄希望于穿着一件由女人皮肤缝制的衣服而“转变”成为女性。
童年时代“母亲”形象的缺失,使小比尔执着于他的“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再加上罗杰斯式非条件关怀的缺失,最终使“野牛比尔”的灵魂和肉体发生了一种分裂—— 他渴望通过将自己变成“女性”(潜意识中的母亲形象)来满足其自体意象的需求。被“野牛比尔”杀害的受害者口中那只骷髅蝶的虫蛹,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描述,“破虫成蝶”意味着“从一具身体到另一具的灵魂轮回”。在“野牛比尔”眼里,受害者的灵魂将被禁锢在骷髅蝶的身体里永世不得超生。而他穿上她们的皮,就能永远地占据她们的身体,从而将自己变成真正的女性。“野牛比尔”就是想通过这个灵魂和肉体置换的过程,完成他那“完美的犯罪”。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都具有多重性,正如世界上任何事物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野牛比尔”也不例外。影片在给我们展示其“残暴”的同时,又给观众呈现出其“内心脆弱”和“单纯”的一面。“野牛比尔”非常疼爱他的宠物狗,会用很过分宠爱的腔调对着那只鬃毛狗说话:“宝贝儿,把那个放下来,你会叫针给扎着的……”在凯瑟琳被关在深井里设法引诱他的宠物狗到深井里后,利用不伤害宠物狗作为不伤害自己的交换条件,威胁说要掐断宠物狗的脖子时,“野牛比尔”眼睛里含着泪水,行为也变得更加疯狂。这些细节表明了“野牛比尔”内心的脆弱,说明他内心也是有感情和渴望获得感情的。
影片《沉默的羔羊》共118分钟,而汉尼拔·莱克特医生在片中的戏并不多,仅仅十六分钟的时间。可是,就是这短短的16分钟时间,汉尼拔这个食人魔的形象便根深蒂固于你的记忆中。当我从银幕上第一眼看见这位著名的精神病专家汉尼拔博士的时候,除去影片开始时的暗示和严肃、冷酷的监狱环境氛围,很难将他与囚犯、心理变态、“食人狂”等这些可怕的称谓联系起来,可是事实确实如此,汉尼拔是精神病专家,但他本身又有精神疾病,这也许是影片具有的独特魅力之一。
影片时刻都在提醒我们,汉尼拔是一头令人恐怖的野兽!比如,在史达琳会见汉尼拔博士之前,上级不断提醒她一定要小心行事,不要和汉尼拔有过多的交谈。随后,当史达琳进入黑暗的监狱之后,在恐怖的音乐声中,狱警告诉她必须和汉尼拔保持足够的距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影片中的这些细节都在暗示我们汉尼拔的可怕。他静静地站在牢房中央,双手下垂,可又立刻让人觉得他更像一头稍息着伺机而动的野兽。汉尼拔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食人魔!他目光犀利而虚无缥缈,能看到人的心底;他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傲慢,智商极高,对于平常人使用他深奥的智慧根本不屑一顾;他是一位博学家,同时也是连环杀手,他疯狂地间隙性地杀人,并吃掉受害者身体的某一部分;这无疑是野兽和恶魔的化身。影片充分地展示了汉尼拔对兽性的执着与向往、对内心深藏的欲望疯狂展现、自恋和对自己杀人过程的享受,他吃人肉、食人脑,凶狠残暴,是一位“彬彬有礼”的食人恶魔。这就是影片给我们展示的汉尼拔的怪癖。比如在《沉默的羔羊》发行十周年纪念《沉默的羔羊2》中,汉尼拔凭借自己高超精湛的医术,割掉了警探保罗的天灵盖,让保罗处于麻木状态。在史达琳面前,从保罗的脑子里割下一块放到锅里煎了之后喂给保罗吃,保罗在吃的同时还说:“It is good。”(www.zuozong.com)
汉尼拔高超的心理分析能力与变态的食人肉行为使他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对象。对于所有观影者而言,汉尼拔最著名的、最血腥和最不能让人理解的行为就是他的吃人肉和吃人脑的行为。为什么汉尼拔会有这种“独特而怪癖”的变态行为?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没有一种心理表现是无意义的、任意的、没有规律的。”总是有深层次心理因素导致汉尼拔具有这些特性。对于汉尼拔的嗜血与变态行为,影片《沉默的羔羊》中并没有直接深入地展开,我们仅从《沉默的羔羊》一部影片是很难得知此种怪癖的成因。要想对汉尼拔有更为透彻的、全面的解读,就必须对《沉默的羔羊》的四部曲《少年汉尼拔》《红龙》《沉默的羔羊》和《汉尼拔》进行全面的分析。在2007年发行的影片《少年汉尼拔》中,我们清晰地得知他的这种变态行为源于童年时妹妹被战争中的逃兵杀死并烹食。长大后的汉尼拔以血祭血,将当年的逃兵全部虐待致死。这种复仇的心理成为他本能中的本能(毁灭生命的本能即死的本能)。
我们可以用心理分析从潜意识、梦的分析、恋母情结等三个视角对汉尼拔进行解读。
我们从2007年的影片《少年汉尼拔》中可以看到,汉尼拔·莱克特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就受到贵族式的教育,其父亲是立陶宛的男爵、一个庄园主,母亲出身于意大利子爵家庭。汉尼拔的童年初期充满温馨和快乐,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纯真而快乐,可爱的妹妹米莎就像他的小尾巴,也是他最爱的亲人。《少年汉尼拔》开始的镜头就是他和妹妹一起快乐幸福的情景。然而,一场战争却夺走了这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他们的农庄,在他们避难的小屋外面,德国轰炸机射死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也被炮火炸死。然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真正毁了汉尼拔一生的是妹妹米莎的死—— 残忍的德军吃了他的妹妹。汉尼拔和妹妹米莎被以格鲁塔斯为首的一群操持着各种语言的逃兵抓住并关起来。那时正值冬季,由于沿路已经设了关卡,这帮人被困在汉尼拔一家作为避难的小屋里。由于食物少得可怜,汉尼拔目睹了格鲁塔斯啃吃鲜活的小鹿的头。这群饥饿的士兵在吃完所有能够找到的食物之后,靠吃儿童等到了战争结束,米莎也是其中之一。2岁的妹妹被他们带走,年幼的他歇斯底里地反抗之后依然无法保护米莎,被打倒在地的他看见格鲁塔斯像砍杀鹿一样杀死了米莎并烹食。汉尼拔倒在雪地里,也就是那一刻,汉尼拔已经在现实社会中死了,他幼小的心理便刻上永远无法打开的死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写道:“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这些幼年的创伤成为无意识积压在汉尼拔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报仇和嗜人肉的潜意识心理积淀。这应该可以作为汉尼拔变态行为“合理性”的一个解释吧。
少年的汉尼拔一直生活在孤儿院里,而这所孤儿院恰恰是汉尼拔以前的家。在这里生活的汉尼拔除了经常受到工作人员的打骂之外,还时刻饱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因为“家里”的一切时刻唤起儿时幸福生活的记忆与对父母和妹妹的回忆、想念。在孤儿院的家里,很多儿时的记忆和经历一次次在汉尼拔眼前回闪,特别是妹妹被杀以及被烹饪吃掉是他内心深处最不愿想起并深埋在潜意识深处的伤痛。这些因素使汉尼拔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他努力地去忘掉潜意识中积淀的伤痛。平时,少年汉尼拔总是一个人孤僻地住在孤儿院里,甚至不会说话。内心痛苦的汉尼拔每晚都会“叫”,每晚都会被噩梦惊醒,梦境中有妹妹米莎惊恐地喊着自己的名字,自己却没有任何能力救米莎;梦境中有格鲁塔斯一伙人残酷杀害米莎时狰狞的面孔和穷凶极恶的嘴脸……米莎的死成了汉尼拔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梦魇。
逃出孤儿院的汉尼拔凭记忆在孤儿院的家里找到一张旧照片,来到叔叔家。不幸的是,叔叔早在一年前去世,只剩下婶婶(紫夫人)一人,婶婶成为汉尼拔唯一的亲人。青年时期的汉尼拔是在婶婶家度过的。当汉尼拔成为医学院最年轻的学生后,他对解剖尸体有极大的兴趣。汉尼拔不断地痴狂于解剖和分析尸体的各个部分,这也为他以后“独特”的犯罪行为埋下了铺垫。随后的汉尼拔,通过给自己注射警察审讯罪犯时使用的药剂,回想起幼年时杀害妹妹的那伙人,努力找到了他们—— 吃掉他们脸颊的肉,砍下头颅来做祭奠。内心通过一次次的杀戮不断获得满足,潜藏和压抑在内心深处中为妹妹报仇的潜意识迫使汉尼拔成长为一名出类拔萃、才华横溢而精神极度变态的精神病专家。
在极度恐惧的缠绕中我看完了《少年汉尼拔》《汉尼拔》(《沉默的羔羊2》)。影片中,年幼的汉尼拔所经历的一幕幕悲惨的遭遇让观者心灵窒息。在经历不断的报仇之后,杀戮打开了汉尼拔心灵之门。伴随他的变态行为,他对自己的杀人过程和吃人行为达到了疯狂的“自恋”状态,他欣赏着自己的杀人过程,享受着吃人肉的“快感”。幼年的汉尼拔在饿得昏迷意识蒙眬之时,求生的本能使他忘记了社会伦理和道德原则的约束,吃了妹妹的肉并贪婪地吮吸着汤匙,他也就顺理成章地选择吃仇人的肉来为妹妹报仇。吃杀害妹妹格鲁塔斯一伙人的肉让他内心的潜意识欲望冲破了“现实原则”和“道德原则”束缚,潜意识欲望获得极大的满足。杀人嗜血、吃人肉成为他唯一快乐的事情。
作为影片的中心人物,史达琳具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勇气和善良的心灵。《圣经》中的羔羊是软顺、软弱无助的,“羔羊”在圣经中就隐喻着弱者、无力反抗的一方。史达琳从小失去母亲后又在10岁时失去了父亲,年幼的她失去了依靠无疑就是弱者。在《沉默的羔羊》中,多次提到史达琳的那个关于羔羊的梦魇。无依无靠的史达琳寄养在经营农场的叔叔家。史达琳的记忆中,两个月后一个早春的黎明,被一栏等待着被他叔叔宰杀的羔羊的惊叫声惊醒,善良的她感受到自己和这群羔羊同样的命运。她试图放走它们,但是由于羔羊太小,或者因为恐惧,它们还不懂得逃走。史达琳抱起一只羔羊绝望地逃走,结果被捉住,受伤的羔羊还是死了,她的拯救最终失败了,羔羊还是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她被送进了孤儿院,完完全全地沦为栏中的“羔羊”。虽然远离了农场,远离了被宰杀的羔羊,但羔羊的尖叫声却一直伴随着她成长。史达琳在夜晚常常被梦中羊群的尖叫声惊醒。儿时一次拯救羔羊的失败经历在她内心深处刻上难以抹去的印记,从“野牛比尔”手中拯救出凯瑟琳以弥补儿时对羔羊拯救失败的遗憾,最终完成对自己的心灵的拯救。
影片中反复提到了史达琳那个关于羔羊的梦魇。她经常梦见一群羔羊被宰杀,耳边常常萦绕着羔羊被宰杀前的凄厉的哀嚎声。这都是梦的象征作用,即为了逃过意识的检查作用,将潜意识中的恐惧用一种化妆的方式展现在梦中。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有两个层面:一层为显性梦境,一层为潜性梦境。史达琳梦的显性梦境为羔羊被宰杀,非常可怜。隐性梦境则是史达琳自己的恐惧之感,她将自己潜意识中的恐惧通过梦转化成为羔羊对被宰杀的恐惧。这种恐惧便是她10岁那年父亲死于追捕窃贼时罪犯的子弹,这便是一个无母丧父的小姑娘内心深处的惊恐、绝望与痛苦无助等种种心灵体验。这种体验其实是以羔羊被宰杀的情境置换的,也是史达琳的隐性梦境。
史达琳出生于美国的一个荒僻的小镇,父亲是镇里的一名守夜人,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年幼失去父母的她无法像一个正常女性一样从父亲那里获得依靠和安全感,从而使她无法正常地完成女性成长过程中的“俄狄浦斯时期”,父亲只是成为一个活在她记忆中的死者,是一个“缺失了的存在”符号,也是一种隐喻。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个在童年时代丧失了父亲的少女意味着她将无法成功经历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也意味着她无法在心理上健康地长大成人。在这个意义上,史达琳一直处于心理变态中。影片中,史达琳的父亲是缺失的,他一出现就已经处于“死亡”状态。在她的成长的道路上,父亲除了留给她一段痛苦的回忆—— 漫长而痛楚的死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史达琳想要战胜在危难时刻内在地、本能地呼唤父亲庇护与依赖的心理,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一个替代父亲作用的影子,寻找变态杀人狂“野牛比尔”的过程,似乎就是她寻找“父亲之名”的过程。
父亲角色的缺失,也对后来史达琳对其上司克劳弗的特殊情感产生了根源性的影响。直到影片的结尾,在庆功宴上,克劳弗以一种父亲般的口吻说“我为你感到骄傲”时,史达琳才真正获得满足,从“恋父情结”中解脱出来。史达琳的恋父情结不仅仅在克劳弗的身上有所体现,在影片中更多地体现在汉尼拔身上。影片中汉尼拔既充当了史达琳“父亲”的角色,也充当了史达琳“心理医生”的角色。影片用了大量的镜头展示了史达琳与汉尼拔的较量。开始时,史达琳奉命去见汉尼拔,或许是上司对她优异表现的肯定,或许是想利用她的美貌对长期禁锢的汉尼拔实施“性别战略”。但是,在史达琳与汉尼拔的较量中,身为囚徒的汉尼拔,凭着其超强的精神分析能力和超强的精神控制能力使史达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囚徒—— 一个被黑暗记忆与创伤情境囚禁心灵的囚者。这在他与史达琳第一次在牢房中见面就得到了充分展示。史达琳坚强的外表被汉尼拔犀利的话语所粉碎。电影中,她外表坚强,其实史达琳是一个内心充满恐惧、从来没有安全感的人。汉尼拔窥视到了她行为背后的潜意识动机,他一次又一次以提供比尔的线索为诱饵迫使史达琳走进了他预设的陷阱中,迫使她接受精神分析疗法,使她重回到童年可怕的梦魇中。最终,史达琳被汉尼拔的智慧所折服,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既同情又憎恨的奇妙情感,向汉尼拔讲述了童年的丧父经历和丧父之痛。虽然作为一名优秀的女警员,史达琳没有能够战胜具有超凡智慧的杀人魔汉尼拔,但是她却以自己的勇气和毅力赢得了汉尼拔的欣赏,甚至是爱怜。史达琳将她隐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全部告诉了汉尼拔。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尼拔成了世上和她最亲近的人。在此时,汉尼拔已经完全取代了史达琳父亲的角色,他也将史达琳对父亲的情感、依恋与怀念,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汉尼拔用其高超的心理分析技能,强化了史达琳自小就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对父亲爱的渴求这样一种情感,从而成功地与史达琳建立起一种父女关系。汉尼拔也最终帮助她走出了恐惧和她长久以来的“俄狄浦斯情结”。但这又带来另一种情感,那就是史达琳对汉尼拔产生了一种除去“恋父”之后的爱。在影片中表现为:史达琳最终将会爱上这个恐怖、绅士、理性的“吃人狂魔”汉尼拔。汉尼拔与史达琳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显露无遗。当史达琳送来被没收的画时,汉尼拔意味深长地开玩笑道:“人们会说我们相爱了。”当史达琳展露内心的创伤后,汉尼拔那双冷酷的眼睛居然闪现了泪光;而当他们被迫分离时,导演在影片中设计了这样一个微小的动作:汉尼拔的手指轻轻地触到史达琳的手,这样细微的动作,是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欲望关系。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父亲是女儿从其与母亲的天然联系中摆脱出来后的第一位恋爱对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