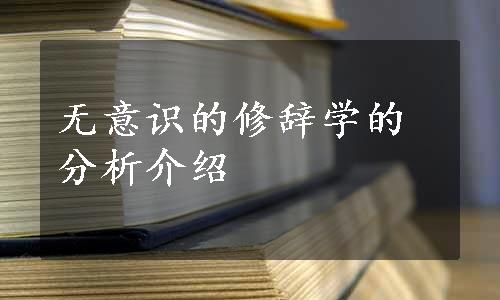
语词有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
阿赫特贝尔的诗的第一行非常巧合地体现了精神分析学和解释学在诗歌方面的一致之处:一种对语词的魔力的特殊开放性。“语词”,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导论》讲座中认为,“一开始是充满魔力的,直到今天,语词仍然保留着他们许多古老的力量”。(SE,15:17)语词所具有的这种魔力,归根结底,与这样的观点紧密相关:不是言说者在掌控着话语,而是话语掌控着言说者。是语言,而不是人,有着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引自弗洛伊德的那句话已经指出,我们在此所关心的并非是一种现代的概念体系,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说过,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具有一种世界去魅化(Entzauberung)的特征。因此,把魔力赋予语言,对我们而言,听起来古老陈旧,似乎源自某种毫无根据的语言的人格化。这样的一种观点让我们回想起一种变相的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过去。[5]
语词的去魅化似乎是同西方形而上学一并而生的。去魅化的原型就是将神话转换为逻辑,就像柏拉图的作品里所完成的那样。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言,柏拉图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常常是极为傲慢的:在《伊安》篇里,他的话听上去就更像是讥讽,而不是肯定。“诗人只有在灵感降临,神志失常和不再有理性时,才写得出作品来。”(Ion,534b)当他禁止诗人进入理想国时,柏拉图也似乎把(对)语词的魔力(的信念)从西方形而上学和科学中驱逐出去(参看1.1节)。
然而,弗洛伊德认为:“时至今日,语词仍然保留着许多魔力。”[6]在被形而上学放逐的地方,诗珍藏着语词的魔力,从而使它能够在多少个世纪中存活下来。自浪漫主义时期开始,似乎就有人谈到了(对)语词的魔力(的信仰)的复苏。荷尔德林、乔治、兰波和马拉梅的诗歌,以及阿赫特贝尔的含蓄韵致的诗歌,都要求收回被形而上学剥夺的认知领地。诗人似乎发现与精神分析学家结为同盟是值得的。如果用马拉梅的话说,那么精神分析学,就好像诗歌一样,赋予了“语词原动力”。这不仅适用于谈疗法的实践,而且对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理论而言,也同样适用。
在谈疗法里,在“精神分析治疗只不过是语词的变换,而没有别的什么”(SE,15:17)的意义上,语词有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正如我们可以把诗称之为一个谈话事件一样,而精神分析学,正如弗洛伊德的一个病人的广为引用的说法一样,也可称之为谈话治疗。但是,在第二个,更突出的意义上,在诗歌与治疗实践里,语词有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接受治疗的患者沉浸在自由联想里:无例外地,他被要求言说任何闯入他脑海中的事。[7]正如在古人看来,另一种声音是通过诗人而言说,而在谈疗法里,另一种声音浮现出来:无意识的声音。无意识的“声音”并不直接对我们言说,就像神的声音会通过诗人的话语或神谕一样。“无意识是故事里察觉不到的,因为它无法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言说。但是无法直接言说的内容,可以间接地说,用口误、说漏嘴、梦境等来说。”(Mooij,1975,105)在日常的交往中,口误和说漏嘴会被片面地看作为一些对话中无关紧要和非理性的干扰,而在谈疗法和诗人的灵感里,口误和说漏嘴则被看作是让无意识发出声音。因此,谈疗法与诗都处在与日常语言的冲突关系之中:“诗人和分析家……因此在分析对话的语境中(或者诗的卷轴里)创造出另一种语言:异常的、变形的、(与‘日常’交流相较而言)颠覆性的”(Mehlman,1976,119)。(www.zuozong.com)
在无意识的精神分析(元)理论里,也确定无疑地在拉康的理论里,语词有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在理论层次上,语言的首要性再次呈现,正如我们从谈疗法的方面评述的那样,并且在这个层次上,语言具有一种双重的意义。首先,根据拉康的观点,无意识像语言一样结构化:“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它的结构像一种语言。”(l'inconscient,c'est le discours de l'Autre:ilest structure comme une langage)(,7)根据穆伊的观点,这句话还可以解读为:“从一个特别的故事里逃离出去的东西,仍然被它找不到出口的故事标识着。因此,无意识不是无定型的和无结构的,相反具有一种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和那个意识的故事的连贯性不同,但是无意识仍然凭借着这种连贯性给出了一个故事,一种他者的话语(un discourse de l'Autre)。这个故事会被添加到那个意识的故事的空白之处。”(Mooij,1975,130-131)因此拉康也认为无意识是一系列的语词(,798)。
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有一种无意识的修辞学。拉康辨别出了无意识的模式和特性,以及隐喻和换喻的文字形象的凝缩和置换(参看Freud,SE,4:270-309,和,799)。这使得精神分析学的解释变成了一种与文字解释及与其相关的有意味的艺术(asignifying art)。[8]“从这个角度来看,解释是填充故事显现出来的空白空间,并且它的变形证明了解释。由此,这些空白的空间同时被赋予意义。”(Mooij,1975,105)故事的意义——用第一章中论述的隐喻来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滑行在语境之中(正如阿赫特贝尔的语词的意义滑行在我的解释过程中一样)。这意味着,对患者的故事的解释,与其说是一种重构,不如说是一种对过去的建构。考虑到这个故事是他必须言说的,患者对过去设计了一副新的“面孔”,与此同时,以一种新的,未来可能性来理解他自身。因此,作为一种建构,精神分析学的解释首先是一种创造,一种想象力的创造。
这种解释的观点摧毁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壁垒,这种差异的相对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称得上精神分析学最为根本的洞见之一。在1925年的《自传研究》里,弗洛伊德认为,在他当发现神经功能症并非原发于实际发生的事件,而是由幻想与妄想引发时,精神分析学才走上了既定的方向(SE,20:33-34)。当他发现幻想和记忆无法区分之后,他不再热衷于通过揭露压抑的回忆来重构过去发生的事件,而是对调查患者们的幻想感兴趣(Ellenberger,1970,488)。[9]因此,我们可以把精神分析学称之为一种虚构的科学。然而,他并不会因此遗忘了这种科学的对象——如果我可以用这种悖论的方式来表达的话——是由“真实的虚构”组成的。而问题在于,这些无意识的幻想是否建构了人类个体的生活经历。
在无意识的理论里,这种语言的首要性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讨论。在拉康看来,这种无意识不仅像语言一样被结构化,而且,与此同时语言还形成了“无意识的可能性的条件”(Lacn,1970,8)。这种无意识并不是像弗洛伊德在他的遗传学的方法中假定的那样:一种处在语言意识“之下”的个体发生或系统发生的古老层次,相反它是语言文化的相互关系(Mooij,1975,132)。因此,穆伊套用了海德格尔的一个术语,他说意识与无意识是同源的(gleichursprünglich)(Mooij,1975,13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