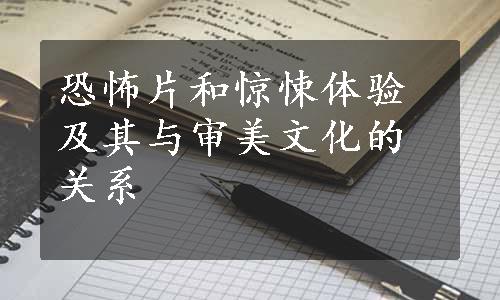
恐怖片的出现源自人的本能和心理对恐怖刺激的一种潜在需要。正如聂欣如所言,电影自一诞生就有了恐怖片,并且延续至今,正由于“恐怖的感觉是一种高强度的刺激,它在某种程度上能提高人的反应能力和爆发力”[10]。因此,它能给人以一种惊悚体验,能满足人们的某种心理调剂和释放需求,也许这就是恐怖片最主要的审美效应。郝建在《影视类型学》中这样描述恐怖片:“比《精神病患者》多一声尖叫,比《群鸟》多一次来源不明的威胁,比《后窗》多一眼肆无忌惮的偷窥,那就是不打折的恐怖片。”[11]自1910年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恐怖片《科学怪人》(12分钟)诞生起,在西方电影史上,恐怖片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银幕上鬼影憧憧,从不间断。尤其是近年来,恐怖电影不断掀起票房和舆论的热潮,其声势不亚于其他类型的影片。恐怖片之所以经久不衰,首先正是源于它满足了人类的本能需求。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观众对恐怖片的观影心理基础源于人类对死亡的焦虑。弗洛伊德早期曾将本能分为性本能和营养本能两类,后期他又把本能重新划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两类。他提出了一个颇受争议的论题:人人都有死本能。他认为死本能是一种驱动力,促使人们做出某些行为,就像性冲动一样。比如战争、自杀,或者早期的角斗和现代的拳击,以及文身、穿孔的流行,都是死本能在无意识层中作用的产物。就此而言,或许观赏恐怖片也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宣泄方式,是死本能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在看恐怖片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心理体验:尽管恐怖,还是满怀惊喜;看的时候吓得心惊胆战,说起来又津津有味,大有痛快淋漓之感。在某些人看来,看恐怖片“玩的就是心跳”。因为日常生活平淡乏味,人们需要获得异乎寻常的高峰体验,就像受到轻微的又不至死亡的电击一般。它也是现代人缓解生活压力,发泄心中积蓄已久的不平和不满的途径之一。恐怖片以面目狰狞的幽灵鬼怪,嗜血变态的连环杀手,疯狂变异的生命种族再加上阴森森的黑夜,迷离摇曳的树枝,黑暗中时隐时现的魑魅魍魉,扣人心弦的紧张节奏……带给观众极强的视听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让观众从中体验到生与死的一线之隔,仿佛潜在的危险正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逼近,从而感受到平凡的现实生活的安全可靠,也可排遣些许内心的忧虑、紧张,或心灵上的孤独感。
许多恐怖片都由某种“原型”发展、推理而来,这就出现了一个故事在不同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情形。如西方描写吸血鬼故事的恐怖片,大多源自1930年美国制作的《德拉库拉》。德拉库拉是一位欧洲的伯爵,在他所购买的几乎已被废弃的古堡里,游荡着一位美貌的女子,她总是主动勾引男性,然后又突然地咬住男人的脖子吸他的鲜血……这一故事被欧美各国不断重拍,以至成了吸血鬼恐怖片的一个经典。然而,任何一种类型片的兴起和繁荣总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诱因,它往往能够隐喻或者影射某一社会历史阶段中某类群体的普遍心理。早期的西方恐怖片是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下民众焦虑心理的曲折反映和变相释放。在好莱坞,恐怖电影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时期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时期,于是,《弗兰肯斯坦》(1931)、《X博士》(1932)、《我与僵尸同行》(1934)等成为这一时期恐怖片的代表作。这些影片的故事常常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恐怖主要来自人类外部,来自异域时空的超自然的魔鬼或者异类,魔鬼与人类的冲突是影片的主要矛盾,影片的结局常常是人类最后战胜异己,消灭魔鬼,世界得以恢复正常。这与当时美国民众在经济和战争的双重阴影下,对现实生活充满恐惧的心理是合拍的。六七十年代,美国又一次开始经历其有史以来较为动荡的时期,越南战争使美国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接着“水门事件”又在公众中激起了更大的政治波澜,女权主义运动试图让女性摆脱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不少知识女性不仅要求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同时也呼吁必须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地位,经济衰退、犯罪率上升,种族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日益分崩离析。与此同时,反传统、解构历史、拒绝意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开始兴起,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恐怖片强势回潮,出现了《驱魔人》、《恐怖万圣节》、《德州电锯杀人狂》、《闪灵》等一系列经典恐怖片。
现代恐怖片的特征杂糅多样,往往在背景造型方面兼容了西方哥特式风格和东方的玄秘恐怖色彩,同时也吸收了心理恐怖片及好莱坞剧情片的经典桥段。具体来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故事发生的场景通常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借以表现人类孤立无援时的惊恐心态。如《小岛惊魂》就发生在英吉利海峡的一座小岛的古宅中,《猛鬼屋》则发生在苏格兰一幢叫做“小丘庄园”的百年鬼屋里。这类影片常常设置切断电话线、风雪封堵、呼叫系统失灵等桥段,使主人公失去与外界的联系,无望地陷入绝境。如《闪灵》将故事安排在一座山区酒店中,暴风雪使得酒店与外界的公路交通、电话联系中断,无线电呼叫系统被男主人公破坏,从而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二是影片中有着非常明显的善恶势力的对立与冲突。多数情况下,恐怖片导演习惯于设计一个性格坚毅的正面人物处于危机四伏的境遇之中,他(她)不断受到邪恶灵异势力的威胁,然后必然会有另一个善良的化身来相助或向他(她)伸出援助之手。这种拯救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家庭内部成员的合作来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作出了某些道德拯救方面的探索。比如《闪灵》中的杜兰斯太太对儿子丹尼的拯救、《驱魔人》中母亲对孩子的拯救、《猛鬼屋》中爱莉诺对家族中受害小孩的灵魂的拯救,等等。三是“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叙事方式在恐怖片中的普遍使用,加剧了恐怖片的惊悚感。恐怖片总是习惯于不断制造紧张、惊险、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主人公被步步逼向绝境,最终到达生死关头,情节也由此推向高潮。不论是《闪灵》中前来解救的哈罗兰先生迟迟不能到达,杜兰斯先生对妻儿的追杀几欲得手,还是《猛鬼屋》中的博士被困于废旧的旋转天梯,险些被摔得粉身碎骨,爱莉诺在最后关头伸出援手将其解救,凡此种种情节的设计都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使观影者犹如身临其境般体验那种在现实生活中难得产生的深度惊悚感。其四,血泪、附身、鬼娃恐怖意象的反复运用。血泪,始终是恐怖片中常常会出现的视觉冲击图像,无论是恐怖片中的暴力血腥镜头,还是电影中像眼泪一样渗透或者流淌出来的鲜血,都是现代恐怖片制造惊悚体验的惯用电影元素。《闪灵》中随着门缝渗出的血浆会令观众一时惊得目瞪口呆,《猛鬼屋》中被钢丝刺瞎双眼,石锤砸下头颅等画面,让人不忍直视。附身也是一个惯用的模式。如《闪灵》中杜兰斯先生被恶鬼附身,《驱魔人》中芮根被鬼附身,《卢浮魅影》中苏菲·玛索扮演的女主角被木乃伊鬼魂附身,都是被不可知的灵异势力操纵,以致失去了人性的常态,作出违背理智的举动,它也隐喻着人类对“恶”的恐惧。小孩在很多时候都是渲染恐怖的工具。他们的天真无邪与灵异势力的邪恶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他们恰恰又是灵异势力与现实世界联系的中介,是所谓的“通灵者”,能够感受到成人无法感受的力量,从而暗示出种种导向恐怖的线索。《闪灵》中的丹尼老是诡异地与脑中虚幻的小孩东尼对话,《驱魔人》中的芮根莫名其妙地对着电视自言自语,《小岛惊魂》中的小女孩甚至将她感受到的另一个世界的形象描绘出来,这些都是超自然力量或人的心理活动使然。同时,音效的使用、心理悬疑的渲染也为恐怖片烘托出骇人的气氛。
观看恐怖片是对恐怖快感的体验,恐怖片通过模拟危险让观众感受恐怖气氛,通过解除危险又让观众相信确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从而使恐惧和愉悦相互混杂。恐怖片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和游戏性,所以绝大多数恐怖片在内容上往往表现为尽量隐去现实生活的状态,转而把重点放在虚构情节、变换造型上,以制造特殊的恐怖效果。电影里所出现的恐怖常常是一种偏于情绪和心理上的恐怖,但只有不仅在情绪上,同时也在思想上产生震撼和有影响力的恐怖感,才能使观众获得较高层面的审美愉悦。电影史上真正经典的恐怖片往往融娱乐性和启迪性于一体,在追求恐怖气氛的基础上又能巧妙地融进人文思考和精神内涵,以使恐怖效果从观众视听感官层面向文化心理深处延伸、渗透,进而揭示文明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某些缺陷在人们内心深处所造成的精神恐慌。如威廉·弗莱德金的《驱魔人》,描写了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离婚妇女被恶魔附体,生下一个多病的女儿。在多方求医无效后,经过两位教士的驱魔术,才解除了危机。这部明显向传统的魔怪恐怖片回归的类型片,既向焦虑不安的公众暗示着只有真诚的信仰才能保证和平与安宁,同时也把社会混乱的根源转移到了某种不可知的非人类的力量上。这一拯救人们心理危机的恐怖片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并引发了一系列妖术和魔怪电影的问世,如《凶兆》、《卡里》以及《驱魔人续集》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启发。
在恐怖片文本的叙述过程中,也常常会体现出一些特殊的文化价值,这是一种在商业文化中少见的反思恐怖片,通过运用暴力和血腥来质疑现实社会的理性原则和自然法则。在恐怖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一些反常的东西以魔鬼或怪物这样一种非自然的、变态的形象出现,它们破坏社会秩序,违背各种现存的法度和界定,甚至自己确立一套游戏规则,从而导致秩序社会的瓦解。恐怖片的文化立场在于,它揭露了现实中社会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中诸多压抑人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或许比鬼怪更令人恐怖。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不怕“鬼”了,但像魔鬼一样的人,却会叫人从睡梦中吓醒。对文明社会和具有正常主体身份的“我”而言,魔鬼、怪物、精神病人都是“他者”,但是恐怖片的道德观却要求“自我”反省“他者”的来由及其异端行为的来龙去脉。现实中其实就隐藏着种种恐怖因素:失落的痛苦,死亡的威胁与恐惧,未知领域、事件发生的不可预测性等,但由于它们合于现存的法度和规定性,人们往往不会将它们视作恐怖因素,而是自然而然地将之认同为“正常”的、本该如此的。恐怖片则暴露了理性世界中的某些局限性,迫使我们去直面非理性,思考非理性。在恐怖片中那些被日常生活压抑的领域变形为鬼魅等非理性的破坏力量,这一变形使现实世界在表象层面上变得容易理解,同时也允许观众将心中那些难以表达的感觉转化为官能的快感。这一过程就像弗洛伊德描述梦的运作一样,认为梦境可以通过置换、凝缩、变形等手段,使内心欲望的压力和充满矛盾的无意识得到释放和表达。恐怖片通过对那些既吸引人又易引发恐惧感的素材进行加工,来达到对现实中被压抑的欲望的替代性满足,这就呈现出了与其他类型片完全不同的审美效应和文化批判,即通过强刺激的惊悚体验,来折射出人类无意识层中原本就存在着的审美心理、求生的冲动、向善的诉求,这或许正是恐怖片常拍不衰的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动因吧。
【注释】
[1]大卫·波德维尔、克莉丝汀·汤普森:《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彭吉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2]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郭青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www.zuozong.com)
[3]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吴菁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4]《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14页。
[5]大卫·波德维尔、克莉斯汀·汤普森:《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彭吉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6]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吴菁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7]荣格:《心理学与文学》,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2—43页。
[8]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崇高与滑稽》,《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第89页。
[9]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10]聂欣如:《类型电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11]郝建:《影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