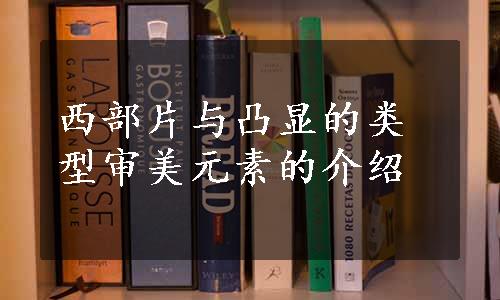
五、西部片与凸显的类型审美元素
西部片并不如许多人所误解的那样等同于美国的早期警匪片,除美国外,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都制作过这种类型电影,其中尤以意大利的西部片最为出名,成为有别于美国西部片的另一个独树一帜的流派。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的西部片有所衰落,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投拍西部片。然而不得不承认,西部片为世界范围的观众所熟悉,还是要归功于美国西部片。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西部片影响力之大,远胜于其他国家,而且它的类型元素的运用比起其他国家的同类影片更为典型,也更具审美趣味,因此今天人们谈论西部片,首先想到的仍然是美国的西部片。
美国西部片以美国开发西部为背景,对美国人开发西部这段历史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的神化,影片素材大多取自一些早期开发者记录的民间传说,并加以想象和拓展,通过电影语言赋予其浓厚的传奇色彩,而非再现历史的真实写照。美国西部片旨在创造一种理想的道德规范和人格力量,去反映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因而在西部片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善良的白人移民受到暴力的威胁,英勇的牛仔以及执法者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曲折故事。1903年,埃德温·鲍特推出的《火车大劫案》充分运用镜头剪辑表现时空转换和交叉,在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奠定了西部片的基本特点。从30年代末起,西部片建立起自己的经典风格:原生态的西部荒原,逶迤起伏的群山,成了展开各种传奇故事、恩怨情仇的空间背景;代表着文明与秩序社会的警察是持正义的一方,同西部的野蛮罪犯进行着殊死搏斗,最引人注目的则可算那些枪法超群、骑术精湛的“牛仔”们,他们以除暴安良的侠举和独来独往的个性奠定了一种“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并存”的标准的“美国神话”。30—50年代为西部片鼎盛时期,较著名的有《关山飞渡》、《红河》、《正午》、《原野奇侠》等影片。
西部片的确具有明显的模式化的情节构成、人物安排和视觉设计。那些可以看得到地平线的蛮荒的原野,具有传奇色彩的牛仔形象和他们跃马驰骋、持枪格斗的激烈场面,所内含着的价值观念——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强调人的个性、意志和个性张扬等等,都是西部片必不可少的叙事策略,它们既是西部片重要的审美因素,又同时勾勒出了美国民族神话的雏形。荒漠,烟尘,落日,以及与孤胆英雄相匹配的牛仔裤、宽边帽、马靴、子弹带等是西部片中典型的视觉审美元素,所有这些视像图谱的背后,则是美国刚建国后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崇的英雄主义与拓荒精神。符号化的视觉元素,连同枪战加英雄救美的情节和极具个性化的硬汉形象,在西部片中反复出现,共同形成了西部片的配方程式,以诠释拓荒时期文明战胜野蛮,个人与社会、印第安人与白人间由冲突而逐步发展至相互理解的最基本同时又十分复杂的种种关系和矛盾。
枪是西部片中重要的道具,也是西部片重要的审美元素。枪之于牛仔,好比灵魂之于身体,有一手好枪法是一个西部人骄傲和仗义的资本,也是让人敬重和畏惧的外在条件,拔枪、射击、中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潇洒动作和漂亮身姿,几分霸气英勇,几分利落彪悍,都源自枪这一物件。虽然每部西部片表现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然而,无论是描写父子恩仇的《红河》,还是“历险+社会反省”式的《关山飞渡》,或是另类轻喜剧西部片《虎豹小霸王》,亡命枪战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情节。在西部片中,另一个类型审美元素是马。西部片里的神化演示,也是关于马的神化演示。可以说没有马就没有西部片,马为西部片带来了强烈的运动形式和节奏效果。电影《红河》里,父子俩在漂泊中先后拒绝了深爱自己的女人,却永远对自己的马不离不弃。马代表着骑士的尊严,所以在《日落黄沙》中,派克踩断马镫而落马,立刻遭到手下的揶揄:“你连马都骑不好,还谈什么团结?”在《不可饶恕》中,伊斯特伍德想重新找回往日的尊严,却怎么也爬不上马背,搞得灰头土脸。可见马之于西部骑士,其作用绝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而是身份的象征。此外,影片还用一定的时间长度去表现牛仔对纯洁的姑娘或女人的钟情。西部女性的独特气质,也是这类影片的重要类型审美元素,她们质朴而美丽,热情而善良,野性中有温柔,勇敢中不乏智慧,当英雄们似倦鸟归巢,回到家中,可爱的女性就姗姗登场了。女性角色的设置无疑也是西部片饶有趣味的一个方面。她们为英雄打气,给予他们家的温暖以及最终的归宿。在《正午》中,凯恩在新婚妻子的帮助下,终于击毙了匪帮,然后扔掉警察的徽章,和妻子一起坐上马车,远离伤心地。在《与狼共舞》中,邓巴在西部遇到了美丽的“挥拳而立”,两人情投意合,浪迹天涯。就连在《不可饶恕》中,未成年的女儿都成了伊斯特伍德可以重托的对象,他对女儿说:“看好猪圈里的猪!”然后,爬上马背,扬鞭而去。
而西部片中硬朗的牛仔形象更是美国人创造群体英雄时的夸张想象,当然也是西部片最重要的审美元素。1939年,福特执导的有声片《关山飞渡》因聚齐了所有西部的经典元素而被公认为西部片的里程碑之作,其造型风格、人物设定和叙事情节都奠定了西部片的基本模式。影片描述了一辆驿车穿越美国西部新墨西哥州蛮荒之地的惊险旅程,呈现出鲜明的西部视觉影像。其中的人物也是颇为类型化的:美丽善良的妓女,优雅高傲的贵妇,嗜酒如命的医生,胆小怕事的酒鬼,亡命天涯的赌徒,偷盗公款的银行家,人情味十足的警长,还有为生活奔命的马夫。而约翰·韦恩主演的林果就是一个典型的西部牛仔形象,他英俊潇洒,桀骜不驯,头戴宽沿帽,手持左轮枪,为了复仇而战。结局是白人战胜印第安人,林果杀死普林兄弟复仇成功,最后和自己心爱的女人一起远走高飞。这自然让美国观众,尤其是美国的男性观众产生了一种圆满自足的成就感和归宿感。《关山飞渡》获得了纽约影评协会最佳导演奖、第12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及最佳音乐两项金像奖,约翰·韦恩也就此成为西部牛仔英雄的代言人而深入人心。1979年5月约翰·韦恩去世,为了悼念他,洛杉矶建筑物上的国旗均降半旗,洛杉矶体育场上也点燃了奥林匹克火炬,直至韦恩的葬礼结束。可见西部片塑造的银幕形象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偶像,而是一个民族自我膜拜的偶像。诚如巴赞所言:“西部片是一种神话与一种表现手段相结合的产物。”[9](www.zuozong.com)
然而,西部片中的英雄形象亦非一成不变。早在1952年,《正午》一片就改变了以往西部片中以年轻强壮的铁汉为男主角,描写他们浑身是胆、叱咤风云的业绩为模式,而是塑造了一位垂垂老矣的迟暮英雄形象。警长凯恩以匡扶正义为己任,携新婚妻子回到小镇,与匪徒作最后的殊死搏斗,不料却得不到他所保护的镇上民众的支持,民众只求息事宁人,妄图同匪徒妥协相安。凯恩陷入苦境,虽然最后赢得了胜利,却毫无圆满的感觉。凯恩作为警长不再是众人热捧的对象,而是被边缘化地显得如此孤单却又不为人所理解。在此,传统的西部片所塑造的美国式的英雄神话已经开始动摇。《正午》的出色成就除了一改以往西部片英雄角色的人物图谱,将人的心理变化通过更为写实的手段得以揭示出来外,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既遵循了经典西部片的套路,同时在结构与人物关系方面又有所突破和逾越。主人公的年华不再、孤独无助,完全有别于传统西部片中被神化得有点类似古希腊英雄的强悍形象,这种设置可以看作是经典好莱坞与新好莱坞之间的一种过渡。
好莱坞电影在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民族电影兴起的影响,以及法国新浪潮的冲击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近亲繁殖的类型电影从形式到主题都进行了“反思”。而在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动荡与政治的危机,电影旧体制与旧观念的逐步被淘汰,又促成了新好莱坞主义兴起。这样,美国电影从内容到形式都与经典好莱坞时期有较大不同。西部片这一好莱坞经典类型也开始发生了变化,非英雄化、非神话化,重新审视当年追杀印第安人的反道德、反人道主义的行径,以及对西部开发时白人将自己的文明强行灌输给印第安部落等提出了种种质疑,成为新西部电影的一时之潮流。20世纪福克斯公司1969年出品的《虎豹小霸王》一直被认为是非主流的西部片,然而这部充满调侃、自嘲意味的轻喜剧片,正是以反面人物为主角,吹响了西部片反叛经典的号角。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印第安人与白人关系的变化。1970年制作的影片《小大人》描写了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婚姻生活。主人公杰克是一个从小就被印第安人收养的白人,从肤色上讲,他是白人,然而从文化上讲,却与印第安人站在同一立场。杰克也全然不是传统西部片中的英雄,而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窝囊废,他回到白人世界后并没有寻回自己的“根”,而是被视作异类,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而在印第安圈子里他却非常自在,受到信任,最后他报复了白人屠杀者,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像杰克这样的“白色印第安人”非仅此一例。在1990年获多项奥斯卡奖的《与狼共舞》中,邓巴从接触苏族印第安人,了解他们,到帮助他们,誓死捍卫他们的安全,在被毒打时毅然说着印第安语,可以说除了肤色不同,已经完全融入了印第安部落的文化中。同印第安人友好相处,甚至在关键时刻维护他们安全的白人形象一再出现在西部片中并非偶然,美国人渴望以友好的姿态来处理国内的民族争端、民族矛盾,正是这种转变的较为深刻的内在原因。尽管这种同情并保护印第安文化的白种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肯定只是少数,但电影正是通过塑造这类人物形象满足了美国民众对当年所谓的“西进运动”的集体反思,再次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原则。
90年代以后,西部片的神话仍被不断重写,同时又被不断颠覆。但草原、蓝天、骏马、大漠荒烟、英雄豪气,这些经典场景和西部片中经常出现的类型审美元素仍在不断重演,然而主题已同传统西部片大相径庭。在《不可饶恕》中,金秋,麦田,余晖下走来了两个年老的枪手,两匹老马,片中响起一曲田园牧歌式的美国乡村音乐,伊斯特伍德以这样一个开局回望他的40年西部片之旅,多少有些“古道西风瘦马”的荒凉感。然而这部影片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回忆感伤,“不可饶恕”凝注了伊斯特伍德对“以暴制暴”这一西部片惯例的彻底反叛。1994年的《燃情岁月》是一部至今令人难忘的西部片。影片中没有纠缠于各派势力的斗争,而是将父子之情、兄弟之情、爱人之情交错融合在西部风光中,同时通过主角崔斯汀一生的命运同灰熊的相联,表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奇妙联系。在这部影片中,西部的山水风情不再只是为了映衬英雄的豪迈气概,也不是为了烘托各种打斗场面,而是力图在西部的自在景物与人物的内心世界之间寻找一种相似点,营造出自然万物与人的灵魂深处的共鸣。尽管影片中崔斯汀与灰熊那牵扯不清的情节似乎总难免让人感到过于神秘,夹杂着某种不可知论,但它的悲情史诗般的书写,在恢宏大气的音乐和壮丽如画的自然风光的映衬下,感动着成千上万个观众。
西部片作为美国自身的民族“创世”神话,是美国人英雄主义的化身,也是美国人民族精神的体现。然而“9·11”后,传统西部片中的神话般的世界观被抛弃,而神话背后的真实意义则被提取,并为现代人所接受。华人导演李安的《断臂山》对“神话”进行了真正的颠覆与解构,他将本来互不相关的同性恋题材与西部片类型结合,产生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西部电影。这是对西部片的拯救,还是将开创一种新的类型片?一切似乎都只是开始,新型的西部片是否能再次引发人们对逝去的峥嵘岁月和往日的美国情调的怀念,尚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我们似乎仍能从各种新西部片、超西部片中找到它最基本的审美因素,紧身衣、短枪、宽边帽、枪战、马、驿车、酒店、个性很强的男子汉、属于西部汉子的女人,以及它们共同所续写的新的奇迹、新的文化内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