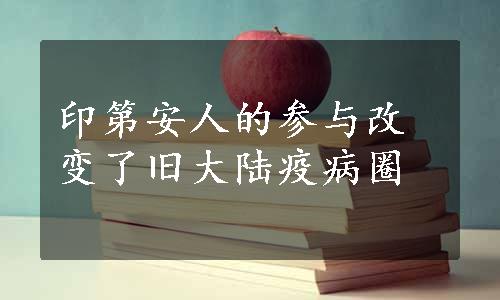
假如1546年的瘟疫的确是斑疹伤寒,那么美洲印第安人的加入也开始影响旧大陆人群的疫病圈。这一推断,在下一波美洲疫病灾难(肆虐于1558—1559年的流行性感冒)中被证实。流行性感冒于1556年暴发于欧洲,断断续续延续到1560年,在大西洋两岸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有人估计,死于这场流感的英国人不少于总人口的20%;[16]相似的损失也出现在欧洲的其他地方。16世纪50年代的流感是否像后来在1918—1919年暴发的流感那样是真正的全球性瘟疫,尚且不能确定。不过日本史料确曾提到1556年暴发的“咳嗽风暴”,“非常多的人因此死去”。[17]
美洲印第安人加入16世纪亚欧大陆的流行疫病圈,并没有使他们免受来自大洋彼岸的其他传染病的侵袭。旧大陆上传染性较轻的疫病,到了缺乏后天免疫力的新大陆就变成了致命的杀手。因此,白喉、腮腺炎以及头两号杀手——天花和麻疹,在整个16、17世纪定期发作。每当曾经与世隔绝的美洲印第安人开始频繁接触外界的时候,循环反复的传染病就在他们的土地上获得了新的活力,四处攻击无助的原住民。诸如,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在17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衰减,当时首次留下记载的传染病便暴发于此。80年后,这里的人口减少了90%以上,“枉负”了西班牙传教士竭力保护和照顾其印第安教民的一片良苦用心。[18]
显然,在欧洲文献不曾提及的地方,很难搞清楚疾病和人口减少的过程。[19]无疑,即便在新大陆人口稀少的南北两头,传染病的驾临也并非一定要经过与欧洲人的直接接触。正因法国人曾在位于今天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皇家港口”(加拿大境内)建立了一个据点,我们才碰巧得知,在1616—1617年,曾有一场不知名的大瘟疫掠过马萨诸塞湾地区。英国人和印第安人都相信,这是上帝为三年以后新教徒的到来扫清道路。而后始于1633年的天花使殖民者确信(如果他们需要确信的话),在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中,神的确站在他们这边。[20]
在加拿大和巴拉圭的耶稣会传教士留下的记载中,同样的经历比比皆是。南北美那些相对隔绝的小族群,即便人口不足以在当地较为长久地一次性维续传染链,他们对欧洲传染病也像墨西哥和秘鲁那些人口稠密的族群一样敏感。一位德国传教士在1699年表述的看法值得在此复述:“印第安人死得那么容易,以致只是看到或闻到(smell)一个西班牙人就会使他们魂飞魄散。”[21]如果他说的是“呼吸到”(breath)而不是“闻到”,他就说中了。
美洲印第安人不得不面对的还不仅仅是一长串致命的欧洲疫病。在新大陆的热带地区,气候条件适宜有些非洲传染病的繁衍,这些传染病曾使得非洲对陌生人而言就意味着危险。疟疾和黄热病是在新大陆安营扎寨的两个最重要的非洲疾病,它们之所以在日后显得至关重要,在于它们是人类在新大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定居和生存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致命的热病经常袭击新大陆早期的欧洲定居地。比如,哥伦布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指挥部,就不得不在1496年迁到更有益健康的地方。这些史实及其他早期探险者和殖民远征队的患病经历,都被用来证明在欧洲船队横穿大洋之前,新大陆的疟疾和(或)黄热病就已然存在。那些指望依靠沿途打劫来维持给养的远征队,因供应短缺而导致的营养不良,也解释了大部分的患病经历;[22]当然,也有不少相反的证据几乎可以证实,疟疾和黄热病都不存在于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大陆。
就疟疾而言,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出自有关对容忍疟疾感染的人类基因特征的分布状况的研究。这一研究表明,印第安人完全没有这类基因特征。同样,传染到新大陆野生猴子身上的疟原虫看起来与旧大陆的一样,事实上都来源于人类的血液。在非洲,不同的疟原虫感染不同种类的宿主,并有选择不同的蚊子作为替代宿主的偏好。而在美洲,则没有发现这种“专业化”倾向,这意味着疟疾是美洲舞台上的新演员,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人类和猴类都不曾携带疟原虫。[23]
这点也可以从西班牙入侵者早期留下的文献中得到印证。比如,一支西班牙远征队于1542年顺亚马孙河而下,因印第安人的进攻死去3人,因饥饿死去7人,报告没有提到热病。一个世纪以后,另一支队伍溯亚马孙河而上,到达安第斯山对岸的基多(Quito)。有关这次航行的详尽报告在描述沿河原住民人口时称,他们富有活力、健康而且人口众多,却没有提到途中的热病。今天谁也不会把亚马孙盆地的美洲印第安人说成“人口众多”,那些已与外界接触的部落既不“健康”,也非“富有活力”。除非带有足够的抗疟疾药,任何欧洲人也不能指望在今天或19世纪类似的航行中保持健康。推论似乎无可争辩:疟疾肯定是在1650年之后的某一时刻才光顾亚马孙。[24]
不过,疟疾在新大陆过往频繁地区稳定存在下来的时间不会这么晚,尽管还没有发现疟原虫初次登陆新大陆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传染病被引进多次,因为欧洲人和非洲人都长期遭受疟疾的困扰。疟疾在美洲环境中扎根和扩散之前,必须得有适当的蚊种与疟原虫相适应,这意味着必须在某些地区首先出现旧大陆类型的蚊子。制约蚊种分布的因素还不是很清楚,但关于欧洲的研究表明,各自独立的因素间的细微差异即可影响一种蚊子与另一种蚊子的此消彼长。[25]合适的疟蚊可能已经存在于新大陆,其被疟原虫传染的容易程度,类似于20世纪南北美的穴居啮齿动物被鼠疫杆菌的传染。只有这样,疟疾才可能在新大陆上迅速发展为疾病的主角之一。事实上,疟疾几乎毁掉了热带低地的美洲印第安人,乃至于几乎清空了原本人口稠密的地区。[26]
黄热病首次成功地从西非传到加勒比是在1648年。当时,黄热病在尤卡坦(Yucatan)和哈瓦那暴发,这种传染病之所以这时才在美洲立足,可能基于以下事实:黄热病在新大陆成为传染病的前提,是一种叫作“埃及斑蚊”(Aedesaegypti)的蚊子必须在新大陆的环境中找到和占有一个生态龛。据说,这种蚊子非常适应人类家居生活,喜欢滋生于静滞的小水域中,且不是底部有淤泥和沙子的自然水体,最好是人工制造的容器,例如水桶、贮水池、葫芦瓢,以备下卵繁衍。[27]
直到这种“埃及斑蚊”登上船只(显然在水桶里)、穿过大洋并在温度常年处于华氏72度[1]以上的地方上岸定居,黄热病才能在新大陆中传播开来。一旦时机成熟,黄热病还会成为人与猴子共患的传染病。与疟疾相比,它所造成的频繁而出其不意的致命后果更让白人感到恐惧。对于黄热病,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一样敏感。不过,比起黄热病这个令人恐惧的非洲远亲——英国水手戏称其为“黄家伙”,疟疾的流布范围要广泛得多,也导致了更大量的死亡。
埃及斑蚊对水桶的特殊偏好意味着,携带黄热病的蚊子能够在船上一次性待上数周或数月,即便在漫长的旅程当中也可以不断地攻击船员。其他传染病如果在船上暴发,大多很快就可能耗尽自己。要么像流行性感冒,每个人都得病,然后同时恢复;要么像天花,只有一些缺乏后天免疫力的人病倒。黄热病却不同,欧洲人在成年时一旦染上,通常都会死掉,很少有水手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结果,一次持续数月的航程可以被黄热病持续的致命攻击链所缠绕,没人能预知谁是下一个“倒霉蛋”,又该轮到谁去死。难怪,加勒比和其他热带海洋的水手如此惧怕“黄家伙”,原因就在于那里正是埃及斑蚊大行其道的地方。(www.zuozong.com)
在新大陆,非洲热带传染病可以轻易落户的地方,就像他们之前完全暴露于欧洲传染病一样,给美洲印第安人之前存在的人口带来完全毁灭性的打击。但在热带传染病不能深入的地方,像墨西哥的内陆高原和秘鲁的高原,虽然前哥伦布时代人口的毁灭足够猛烈,但并不那么彻底。[28]
在加勒比海沿岸及大部分岛屿等存在种植园需要输入大量劳力的地方,非洲奴隶取代了被灭绝的美洲印第安人。尽管其他陌生传染病,特别是胃肠型疫病,也造成了奴隶的高死亡率,但由于非洲人大多已经习惯了在疟疾和黄热病的环境下生存,因此由这些疾病造成的人口损失相对较小。此外,男性人口的绝对占优和不利的育婴环境,以及被渡海而来的非洲奴隶不断打破的区域性疾病平衡,都决定着加勒比地区的黑人人口在19世纪之前增长有限。而后当黑奴买卖中断,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在大西洋两岸传播疾病、臭气熏天的运奴船不再出没于海上时,黑人数量在加勒比群岛的广大地区开始飙升,白人则相应减少,有时甚至完全消失。奴隶制的终结,以及单一种植甘蔗的土壤地力的耗尽,这些经济和社会的变迁,虽有利于促成这一结果,但黑人在抵制疟疾传染上的优势也不可低估。[29]
总体来看,美洲印第安人所遭受的灭顶之灾,其规模之大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因为今天是一个传染病几乎已无足轻重的时代。在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曲线中,尽管不排除地域差异,前哥伦布时代与最低点的比例还是约为20:1甚或为25:1。[30]在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背后潜藏的是巨大而漫长的人间痛苦:以往的社会架构分崩离析,旧有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古老的生活方式失去意义。一些表达当时情形的心声被记录了下来:
死尸的恶臭弥漫。当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倒下后,人们大半逃往田野。狗和秃鹫在吞嚼尸体。死亡是多么可怕。你们的祖父死了,随之一同离去的还有国王的儿子、兄弟及其亲戚。于是,我们成了孤儿,啊,我的孩子们!我们从小就成了孤儿。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等死![31]
美洲印第安人肯定是新疾病的主要受害者,但其他人口也不得不适应环球航行所改变了的疾病传播方式和内陆贸易方式。大多细节已无法复原,但总的模式尚可相当清晰地看出。
首先,像美洲印第安人这样以往与世隔绝的人口,当与欧洲人或其他航海者接触时,通常会经历一系列严重的死亡,这类死亡曾经改写了美洲历史。至于哪种文明病危害最大,则视情况的不同而不同,部分取决于气候,部分取决于某种疫病何时到来等偶然因素。可是,与世隔绝的人口对外来疫病的敏感,总归是流行病学上事关生死的事实。区域性的灭顶之灾,因此便成了公元1500年后一再重演的悲剧。
不过,在文明的人口中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更为经常的跨海接触趋向于使传染病均质化,潜在致命的偶发疫病,逐渐让位于地方性的传染病。当船只开始出没于地球的各大洋,并把所有的海岸线联结为一个国际交流网络时,疫病分布的均质化过程就意味着疾病将被传播到更多更新的地区,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这些地方制造具有地区毁灭性的流行病。伦敦和里斯本曾作为欧洲疫病的发源地而臭名昭著——的确名副其实。不过,到了大约1700年时,帆船已最大限度地把新疫病扩散到新地区。从此以后,传染病对人口的影响开始降低,在没有其他因素参与的地方,最终为拥有传染病经历的现代人口的持续增长铺平了道路。
一面是原来隔绝社会所经历的惨烈的人口损失,一面是具有患病经历的民族所展现出的全球性人口增长潜能,这样的对比使世界的力量平衡明显有利于欧亚的文明社会。随着传染病的长期破坏,随着幸存者融入日益扩大的文明社会圈的进程在全球各地的加快,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也相应减少了。
细节只是偶尔可以复原。尽管传染病也给非洲一些地区的隔绝人口带来了灾难——比如在南非的霍屯督人(Hottentots)当中——但没有人能说出灾难源自哪种疫病,伤亡又究竟出现在何时。在非洲的西部和中部,比以往规模更大的奴隶贸易不仅致使人口混合,还驱动人口从一个疾病环境走向另一个新的环境,从而致使传染病的扩张越过了原有的自然界线,只是我们无法确知,这些变化随后是否对人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入侵者无疑给内陆村落带来无数的伤害,但显然人口灾难却没有大规模地出现。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快速循环的传染病,无论产生了怎样不可小觑的人口后果[32],所有因病导致的死亡率提高,都被玉蜀黍和木薯在非洲农民中的迅速扩展而带来营养改善所掩盖,甚至不止如此。这些由美洲进口的农作物的卡路里产量,突破了以往单位可耕地所能供养的人口上限;尽管得不到相关统计数字,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地区,很可能同旧大陆其他地区一道走进了17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口增长历程。[3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