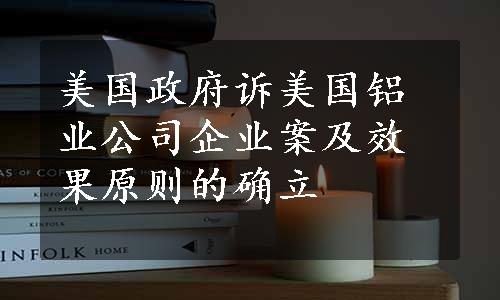
1945年的美国政府诉美国铝业公司等企业案(以下简称“美国铝业公司案”)[16],已成为美国反垄断法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案例,其判决最终确立的效果原则及其相关观点在其后相关案例中被广泛引用,并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承认为具有约束力的原则,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反垄断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案中的美国铝业公司(Aluminum Co. of America,以下简称“Aloca公司”)是一家注册于美国的公司,其股东于1928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一家与Aloca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完全一致的独立法人Aluminum Limited,以接管Aloca公司在美国境外的资产。至1931年中期,Aloca公司与Aluminum Limited已彻底分离,但几个控制Aloca公司近50%股份的主要股东仍控制Aluminum Limited近50%的股份。1931年,若干家注册于瑞士、法国、德国、英国的铝业公司与Aluminum Limited筹谋合作成立了一家注册地在瑞士的公司,各方分别在1931年、1936年达成国际卡特尔,其主要内容是为控制世界铝市场的价格水平而组成产销联盟,各方以其各自在公司的持股比例约定产量份额及销售价格底线,以限制总体的铝生产量与销售价格。该卡特尔对美国国内市场的铝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司法部以Aloca公司作为被告起诉至地方法院请求宣判被告垄断州际和国外商业,并要求解散被告。地方法院以本案涉及的参与者都是外国公司,且该卡特尔也是在美国境外运作,Aloca公司与该卡特尔无关为由驳回了指控。后原告上诉,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了该案。
上诉法院将其判决分为四个部分,其中与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相关、亦是本案诉争焦点之一的是第三部分,即注册于美国的Aloca公司与注册于加拿大的Aluminum Limited就前述垄断协议是否构成共谋,以及Aluminum Limited与其他外国公司的共谋行为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就此,上诉法院认为,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Aloca公司也参与了上述外国公司直接的卡特尔,尽管其与Aluminum Limited存在共同的大股东,且存在一系列商业往来,但除非有证据显示一家公司没有做出独立的决策而是完全遵从另一家的指示,否则他们在法律上应被认定为独立的主体。在排除了Aloca公司的垄断合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注册于加拿大的Aluminum Limited与其他外国公司之间在美国境外达成的卡特尔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针对这一问题,上诉法院推翻了此前美国香蕉公司诉联合水果公司案判决所明确的属地管辖原则,认定本案适用美国《谢尔曼法》,开启了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先河。
该案主审的汉德法官认为:本案中1931年与1936年两个卡特尔是否违反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并不取决于美国是否承认其他国家对此的相关规定,相反,法院仅需考虑美国国会是否对非美国公民在美国境外的行为进行强制规范,以及相关管辖权的行使是否符合美国宪法,因为美国的法院没有在美国的法律之外行使职权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汉德法官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正如美国香蕉公司诉联合水果公司案、美国诉鲍曼案[17]、布莱克默诉美国案[18]等判例所述,法院不应对美国法进行过度的扩张解释,使其适用于对美国领土范围内没有任何影响的案件;另一方面,基于国际惯例及既定规则,一国可以针对外国公民在国外的、但对于该国有消极影响的行为进行管辖,且该等管辖权一般会受到他国的承认,这一点在斯特拉斯海姆诉日报案[19]、拉马尔诉美国案[20]、福特诉美国案[21]中均有所体现。据此论述,美国的反垄断法便有了域外适用的效力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汉德法官进一步认为,如果协议意在影响美国的进出口,而且其事实上也产生了这样的影响,那么尽管该协议并非在美国国内订立,也可适用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这也是认定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两个前提条件。这一论述突破了国际法关于管辖权的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的理论限制,成为关于国家针对反垄断案件实施管辖权的一个新兴依据——效果原则(或称影响原则)。
美国铝业公司案中法院的论证思路可整理为:首先声明美国立法者有权对非美国公民在境外的行为制定相应规范,且其司法权的行使符合美国宪法及国际法;进而论证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性——基于国际惯例及既定规则,对于在美国境外发生的、对美国没有任何影响的行为,美国反垄断法不应适用,但对于旨在影响且实际也影响了美国相关市场的行为,美国反垄断法可以适用,且美国法院也拥有管辖权;同时,在提出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两个前提条件,即当事人意在影响美国的进出口,而且事实上也产生了相关影响时,还引用了在先的适用传统属地管辖原则进行判决的美国诉太平洋及北极铁路和航运公司等企业案[22]、美国诉剑麻销售公司等企业案[23]、汤姆森诉凯瑟案[24]、美国诉诺德·德彻·劳埃德案[25]等判例,以证明本案的判决与在先案例并不冲突。
一国将国内法适用于国际经济领域,必须符合公认的国际法。[26]基于这一基本立场,美国铝业公司案的前述论证过程从逻辑上来看具有其合理性——法院并非是脱离国际法凭空捏造出了效果原则,而是在法官们认为的、效果原则属于国际法惯例的角度出发,去分析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效力[27]。也正是基于此,该案的判决公布后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美国国内及其他国家的过多关注。当然也不排除在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其他国家因战后经济复苏的原因或社会经济制度的需要,无暇关注此类案件或忽视市场经济作用等因素。但效果原则的此等论证,仍存在以下可质疑其正当性之虞:(www.zuozong.com)
1.引证“既定规则”的正当性
如前所述,法院在论证美国反垄断法的可适用性时,是基于国际惯例及既定规则,但是其所引证的“既定规则”,均为美国国内法判例或成文法条文。在当时及该案后的一段时间内,除美国及在美国干预下的德国、日本外,世界上少有国家颁布反垄断法,且法院所引证的案例也仅为美国判例,因此,法院所依据的既定规则是否符合公认的国际法,是难以进一步做正当性论证的。
2.法律冲突下域外适用的正当性
一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难以避免的会产生与所在地国的法律冲突问题,基于效果原则的一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更可能会导致与行为地国乃至其他影响发生地国的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冲突问题。在这一冲突下,如何证明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正当性,是上诉法院没有详细论述的问题,这也是单纯适用效果原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3.反竞争影响界定的正当性
法院在提出效果原则以论证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性时,提出了一个适用管辖权的新的连接点,即行为对境内市场产生了反竞争的影响。但法院并没能明确界定何为影响与非影响的界线,而是跳过了界线问题,从举证的角度认为只要控方证明了行为人具有影响的意图,则应由行为人对影响负举证责任。效果原则内涵界定不明的问题,也为日后法院利用其模糊性而不适当的扩张美国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埋下了伏笔。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