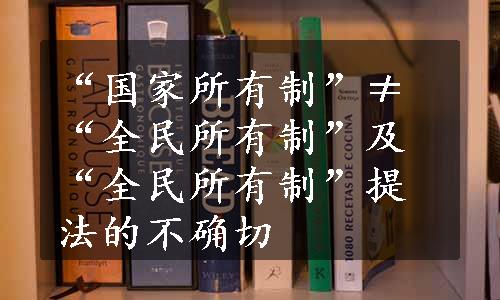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学界、政界、经济界,“国家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都是通用的,谁也不注意其间的差别。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无疑是最有权威的法律,其中第三条这样写道: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
在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五章“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第四十一条规定得更为明确:
企业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企业财产包括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财产,以及其他依据法律和国有资产管理行政法规认定的属于全民所有、由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
“全民所有”为什么“即国家所有”?《条例》中未加任何解释——似乎也不必做这种解释。这种不必解释本身,实际已是一种解释:国家集合了全民的权利,体现了全民的权利,国务院,也即中央政府代表着国家来行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所有权是私法或民法的物权中最基本的权利,它可以转让和被剥夺,但不能由他人代表来行使。经济生活中,常有所有权人委托他人代表自己行使所有权所派生的其他权利,如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等,但这不是转让出所有权。所有权人与这些代理者发生委托代理关系时,往往要有明确的契约,而且要有利益的回报,租、赁、借、当、贷等汉字中,就已显示中国古代早就清楚这种关系,而古罗马法中对此更有具体规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所有权与其派生权利的关系有了更为充分的体现。美国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就是由此而发的。而现代法律之具体、丰富,重要原因也在于此,不论私法还是公法,都要强调所有权是基本权利。
马克思在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时候,反复强调:这并不是取消个人的权利,而是要明确和保证以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所有权。因此,公有制是“重建个人所有制”。从这种意义上说,“全民所有制”的提法,比较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但它又很不确切,这点下面再分析。
如果说“全民所有制”还能表示劳动者是所有权主体的话,那么,“国家所有制”则将所有权完全归结于国家,乃至政府。将“全民所有制”直接等同于“国家所有制”的惟一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就是全民的代表,因此,国家所有制也就是全民所有制。
这里,我们首先可以发现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全民所有制”提法的依据,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述,那么,也就应依据马克思关于国家的论断来规定“国家所有制”。马克思历来反对将国家视为全民代表的观点,而是强调国家的阶级性及其阶级统治工具的特点。只要国家存在,它的性质和特点就不能改变。因此,“国家”不可能代表“全民”,它只能代表“全民”中居统治地位那部分人。“全民”在“国家”那里已经不“全”。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作为“代表”,不可能成为所有权的主体。我们不妨退一步,假设国家是全民的代表,全民所拥有的所有权也不是转让给国家,而是将由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等权利委托给国家机构去代理,国家作为代表所有权主体的机构,行使占有权,并不等于,也不应该剥夺所有者的所有权,而是要执行所有权主体的指令,维护其利益。
第三,将“全民所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制”,忽略了所有制的内容,即所有权。从半个世纪以来的有关论述中,几乎都未从所有权来说所有制,不是把所有制作为所有权及其派生的权利体系,而是将它视为决定一切的制度。当说“全民所有制”时,不论所有权,也就很容易地从制度的转换——并非所有权的转让——将之变成“国家所有制”。然而,不强调所有权及由其派生的各种权利所构成的权利体系,也就没有所有制的内容,公有制应当是比私有制更加注重个人所有权的制度,但以“国家所有制”取代“全民所有制”,也就淡化、削弱了劳动者个人的所有权。(www.zuozong.com)
第四,以“国家所有制”等同并取代“全民所有制”,强化了国家的权利,在未实行充分民主的条件下,很容易造成马克思所担忧的“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状况,而劳动者个人的权利,得不到明确和保证,由此造成对公有制的内在威胁。
总之,“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不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等而论之。以“国家所有制”等同并取代“全民所有制”,不仅造成逻辑上的混乱,更反映出中国公有制的不完善,是国有企业主要矛盾的表现。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全民所有制”这个提法。它是通行了半个世纪,但却是不严格、不确切的。
“全民”之“全”,是指全体,而“民”则是又以个体存在的,“全”只是范围,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实际的权利主体。“全民”中的个体,才是权利的主体,他们必须依相应的法律机制,行使自己的权利。“全民所有制”,确切的称谓应为:在特定国度和地域范围内全体公民个人所有权所体现的制度。所有权的主体是个人,而个人又要依相应的政治法律机制——其要点就是民主,来集合分散的权利,再由之控制其派生的占有权、监督权、管理权等。
而“全民所有制”这一提法,无疑是将“全民”作为一个实际的权利主体,但又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机制来保证其范围中的个体的所有权,这样,“全民”就成为一个空壳,归“全民”的所有权只能由国家掌握。然而,国家作为一个机构,在未经作为所有权主体的个人选举的情况下,所“代表”的,就只能是构成国家机构的主要人员的利益。“全民”的所有权被虚置,而国家机构的负责人,则成了所有权的主体。但是,这些负责人的所有权又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他们的地位也不是以所有权的法律规定来保证的,而是取决于其政治活动和关系。一旦他们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处置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实际上已经侵犯“全民所有制”的权利,就有可能受到法律制裁。因此,他们中的少数人只能通过违法手段,将国有资产以各种方式转变成其个人财产,但不能直接成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全民所有制”的提法中,还有一大缺陷,就是忽略了劳动力的所有权。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将劳动力所有权作为基本权利,生产资料所有权不过是劳动力所有权的派生权利,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承认劳动力的所有权,但在私有资本企业中,基本权利却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在其中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由资本所有者购来的劳动力使用权——劳动力所有权的派生形式。也正因此,作为劳动力的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只有依据其劳动力使用权得到相应货币价格的权利,而没有在企业占有、经营、监督各环节的权利。
公有制中的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主体,更是其劳动力的所有权主体。这一点,在合作企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是从这种意义上,我说合作企业是公有制的典型。而国家资本所体现的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的初级形式,是很难体现劳动力所有权的。“全民所有制”这一提法,也不能反映劳动力的所有权在企业中的地位。
从有关的法律条文和政策文件上看,“全民所有制”的所有权仅局限于生产资料(有时也用“财产”等概念)上,并不包括,也不能包括劳动力所有权。
劳动力是劳动者本身的能力,劳动力所有权是个体性的,只能由劳动者个人拥有。对于企业来说,只有加入该企业的劳动者并在其中劳动的人,才能体现其劳动力所有权。这在合作企业中的表现是明确的。但“全民所有制”的“全民”并不是都要到国有企业中就业,他们的劳动力所有权不能都体现于国有企业,只有在国有企业中就业的那部分劳动者才能体现其劳动力所有权。
“全民所有制”的提法,完全忽略了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从而使其公有制的性质得不到体现。
从作为一个概念的标准看,“全民所有制”具有明显的缺陷,它只是一个不准确的提法,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因此,当我们探讨中国的国有企业矛盾,不仅要明确“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也不能以“全民所有制”这一提法作为立论的依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