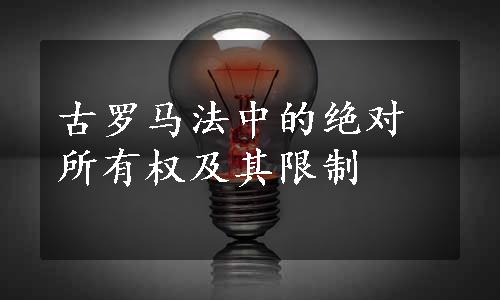
作为大陆法系“鼻祖”的罗马法,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就是个人主义色彩浓重的所有权,所有权被认为是“对物最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主宰”,[3]罗马法上的所有权也因此被视为是绝对所有权的最早渊源。在《优士丁尼法典》中,所有权的模式是极具绝对性的,所有者对其物享有绝对的处置权,这样的处置权又极少受到来自公法的干预或限制,各种财产上的负担都被控制在最低数量范畴,而且即使设定了法律上的负担,也被非常小心地与物的所有权区分开来。[4]据考证,在古罗马法典中所有权最早被表述为主权(dominium),[5]后被称为“mancipium”,现代意义上的所有权对应的称谓直到帝国晚期才出现,谓之“proprietas”。[6]Proprietas在罗马财产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是其他物权显要的主宰(signoria eminente sulla cosa)。所有权人可以对物行使所有可能行使的权利,拥有对物最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in potenza)主宰,其权利具有绝对排他力和永久性,法律只以否定的方式而非列举的方式来界定所有权的内涵,这是因为所有主的权利被认为是无穷无尽、变化万千的,不可能一一列举穷尽。[7]
自由性无疑是罗马法所有权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不同于欧洲十八、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所有权观念,此时期的所有权也并非“绝对”到无所约束、任意妄为的程度,罗马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了这种自由性早期时候仅对罗马家庭中的家父而言,而对社会具有较高价值的物上,如土地、奴隶等,受法律限制仍然繁多。这些限制在《十二铜表法》开始到帝政之后始终存在,特别是在罗马—希腊时期以及优士丁尼法中表现明显,例如《十二铜表法》第7表中就规定有基于相邻关系的限制,提出了相邻田地之间应留有必要的通行和犁地空间的法律要求。又如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里设立了诸如不得滥用权利的基本原则规定,其经典表述为“使任何人不滥用自己的物乃系公共利益之所在”,[8]这意味着所有权人只有对自己物进行合理使用才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一旦超出合理使用的范围就应受到限制,这是当时处理相邻关系、地役权关系的重要指导性原则。事实上,时效取得制度也正是建立在该理念基础之上,对物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也被视为是一种权利的滥用,因此罗马法开创性地用时效取得来约束、限制所有权人,促使其积极使用资源。[9]在罗马法的很多制度中都体现出了对公共利益的重视,例如,公家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征收、征用甚至没收私人财产,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禁止个人在过于靠近城市范围内焚烧尸体等。[10]此外,罗马法中还存在有大量他物权对所有权的限制,包括用益权(usus fructus)、地役权(servitus)、地上权(superficies)、居住权(habitatio)、永佃权(ius emphyteuticarium)等,这些他物权的种类和内容随着罗马法的发展更加丰富多样。[11]
从时代背景的角度看,这种所有权观念的形成绝非偶然,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经济等原因,必须放在古罗马时期“氏族社会”—“农业社会”—“小商品经济社会”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早期的罗马氏族社会里,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仍属氏族共有,各个家族只能拥有诸如奴隶、羊群等动产的所有权,再由氏族团体分层分配给各个家庭以占有和使用,只不过古罗马人的氏族宗法、血缘纽带等约束力和维系力较弱,社会结构较为松散。后来随着帝国大肆扩张领土后,社会的开放度大幅增加,商业氛围逐渐浓厚起来,原来的氏族共同体的土地共有模式俨然严重阻碍了商品的交换流通,古罗马的土地分裂运动由此展开,最先表现为家庭不动产与氏族分离,后随着家父权进一步的衰落,更符合自然法理性精神的万民法规则影响力增强并得以扩展,因此在罗马帝国后期家庭财产也开始解体,“个人所有权”方才生成。由此可见,罗马法中的所有权产生的过程是渐进的,历时漫长,从时间上来说,也非人们所假设的先有所有权,再分离出用益物权、地役权等他物权,而是先有地役权和用益物权再有所有权的,换句话说,所有权实际上是地役权(servitus)和用益物权(usus fructus)在确认所有权人地位的共同需求作用之下的结果。[12](www.zuozong.com)
相比而言,作为英美法之渊源的日耳曼法却始终没有绝对所有权的观念,这也是由其特殊的氏族特性、地理和商品发展条件决定的。一方面,日耳曼人有很强的团体主义倾向,彼此间人身依附关系较强,个人始终未脱离团体上身份的约束,原始平均主义思想一直未被打破,个人主义未得到发展。[13]另一方面,当时日耳曼社会地处比较封闭的内陆,商品生产和交换很不发达,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村落社会、农业社会的阶段,土地是重要的物质生产资料,必须公社所有,再分配给家庭使用、收益,这样也已经足以满足生产生活所需,因此,日耳曼人传统上更注重的是不动产的使用价值,而不强调土地归属本身,个人也缺乏将土地私有化的动因。相比而言,日耳曼人的财产体系更注重“以使用为中心”,具有占有和所有混合、物权社会性色彩浓重等特点,不动产上的具体权益被分割成管理、处分、使用、收益等各种具体权利,对财产的归属并不在重点考虑之列。[14]总结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中对所有权的观念的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罗马法中所有权观念是在重视经济价值的贸易经济时期产生的,又因传统个人主义之观念较重,因此有将所有权认作是全面的、完全的支配权的经济上的动机和必要,因此产生了注重归属的所有权中心主义;日耳曼法则是建立在重视利用价值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生存环境较为封闭,奉行的是原始平均主义思想,商品的生产交换也不如罗马那样发达,财产的交易主要还局限于团体之间,故而将所有权特别是土地所有权作为较强程度的利用权来对待,因此产生了更注重财产权利的实际效用和具体行使而非财产归属的财产体系。由此可见,财产制度的产生是社会需求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不同社会而异,而罗马法与日耳曼法对所有权的认识和限制上差异同理可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