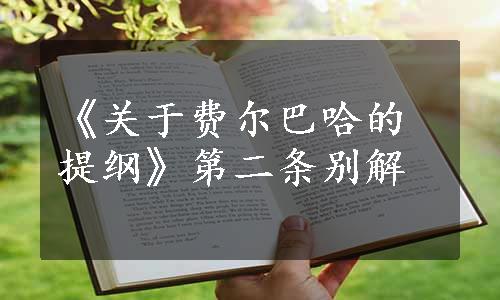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二条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本、哲学教科书和有关研究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文献,都认为这一条讲的是真理观问题,马克思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之所以出现这种一边倒的解释,显然与这一条的中译文有关。笔者查对了第二条的德文原文,联系当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发现中译文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下面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德文原文是:
Die Frage,ob dem menschlichen Denken gegenständliche Wahrheit zukomme—ist keine Frage der Theorie,sondern eine praktische Frage.In der Praxis muäder Mensch dieWahrheit,i.e.Wirklichkeit und Macht,Diesseitigkeit seines Denkens beweisen.Der Streitüber die Wirklichkeit oder Nichtwirklichkeit des Denkens—das von der Praxis isoliert ist—ist eine rein scholastische Frage.[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译本第一版(1972年)的译文是: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译本第二版(1995年)的译文是: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3]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第二版译文基本上和第一版一样,但做了一些重要改动。主要有:在第一句“客观的真理性”的“客观的”后面附上了德文的对应单词“gegenständliche”;第三句则完全采取忠于原文的直译。
细心的读者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在“客观的”一词后面附上“gegenständliche”呢?原来在《提纲》的第一条中“gegenständliche”这个词出现过,第一版译文中译作“客观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4]中译本第二版则把“gegenständliche”改译为:“对象性的”[5],后面仍然附上“gegenständliche”这个德文单词。显然,在第一条中把“gegenständliche”译为“对象性的”更符合原文,那为什么在第二条中一个词还要保持原来的译法“客观的”,不译为“对象性的”呢?笔者认为,这与对第二条德文原文的理解有关。
《提纲》第二条共三句,第一句是理解的关键。“Wahrheit”一词德文词典的释义是:真理,真话,实话;真情,真相,真实性。可见并非一定要译成“真理”不可。“gegenständliche”一词在马克思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含有通过人的活动使对象得以改变的哲学意味,因此,译为“客观的”是不妥的,应释为“对象性的”。该释义在《提纲》的中译本第二版第一条中改过来了,但第二条为什么不相应改过来呢?也许译者是考虑到译为“对象性的真理性”,文句不通,所以保留原译文,后面附上德文原词,算是给读者一个交代。殊不知这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与第一条的译法相矛盾。在这么短的两段文字中一个词有两种不同的译法是很怪异的。二是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对象性的真实性”,而不是在讲“客观的真理性”。与之相联系的是《提纲》第二条第一句中动词zukomme的译法。德文词典对zukomme的释义是:走进;接近;面临;对……得当、适宜、适合、符合;等。中译本把它译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中的“具有”,不仅很牵强,而且会造成一种误解,似乎马克思认为人的任何思维都可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就使马克思停留在费尔巴哈的“直观”层面上,与黑格尔哲学相比反而后退了。黑格尔曾批评那种随便滥用真理的见解,他指出:“以为真理存在于表示某种确定结果的或可以直接予以认识的一个命题里。对于像‘凯撒生于何时?’‘一个运动场要有多少长?’这类问题,诚然给予一个明确的简洁的答复。……但这样的所谓真理,其性质与哲学真理的性质不同。”[6]黑格尔虽然是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关于真理的见解,如真理是具体的、真理是一个过程、真理是认识发展的较高阶段、真理是全体等,是很深刻的。马克思说过:“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7]费尔巴哈哲学之所以贫乏,除了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外,就是缺乏辩证法。所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种译法与马克思这个专门评论费尔巴哈哲学的提纲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
笔者认为,《提纲》第二条第一句应译为:“人的思维是否符合对象性的真实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相应地,第二句改译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实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第三句还是按照中译本第二版译法,译为:“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8]笔者认为,改译后的第二条更加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具体表现在:
一是对第二条的理解更加明确了。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认识的对象是在不断改变着的,所以对人的思维是否符合这种不断改变着的对象性的真实性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必须从实践上去理解。思维的真实性,也就是思维的现实性、力量、此岸性,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正是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实践,使思维的真实性更能体现现实性,也更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在此前的巴黎手稿中曾说过:“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9]“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0]思维的这种真实性、现实性和力量,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此岸性”。在离开实践的情况下去讨论思维的现实性,这不是在重蹈经院哲学的覆辙吗?
二是和《提纲》其他条的内容更一致了。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批判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在改变现实世界中的能动作用;第二条指出,由于脱离实践活动,费尔巴哈的思维所反映的“感性客体”缺乏真实性,因此既不现实,也显得苍白无力;第三条指出,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改变了环境,而且改变了人本身,这里也包括人的思维;第五条则进一步批判费尔巴哈,指出光凭感性直观而不了解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是不可能彻底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抽象的思维”的。
三是马克思在《提纲》之后与恩格斯一起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第二条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11]马克思举了很多例子来加以说明,如樱桃:“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的。”[12]再如费尔巴哈所鼓吹的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河水。马克思指出:“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这说明,只有从人类的工业、农业、商业和社会变革等实践活动出发,才能真正解决思维是否符合现实,即对象性的真实性问题。
法国的奥古斯特·科尔纽曾是东德柏林洪堡大学文化史教研室教授,他撰写的多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界有很大影响。在第三卷第三章中他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笔者注意到,在长达14页的论述中,科尔纽一点儿也没有提到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关于第二条,他明确指出:“费尔巴哈因为不理解实践的作用,所以……他不能解决理论问题,特别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这证明他是不可能把唯心主义彻底驳倒的。……并不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是对于感性现实的直觉供给我们它的客观存在的确实性,这种确实性是只能由与实践活动相连接的思维供给给我们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就是说,要知道认识是否与客观现实相符合的问题,事实上,只有从实践的观点去说明才能弄清楚,因为人凭着直觉和直观是认识不了世界的,而必须把世界作为人的活动的客体,人才能认识世界。……因此,思维确实存在于它同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之中。至于是否能存在着一种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思维方式的问题,这就又扯到纯粹思辨上去了。”笔者认为,科尔纽的这一分析是很深刻的,符合马克思的原意。(www.zuozong.com)
(原载于《东南学术》2013年第6期)
【注释】
[1]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Ausgew hlte schriften in zwei Bnden,Dietz Verlag Berlin,199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20页。
[12][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管士滨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第163—16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