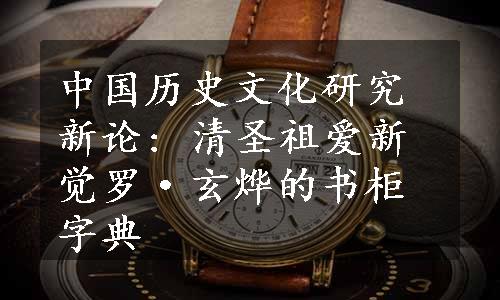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就是说,正儿八经的皇帝,在这个朝代里就要消失了。一般来讲,如同垂死之人,还有一个回光返照一样,这皇帝一路做下来,到了清朝,还真出了几个集大成者。限于篇幅,前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有顺治等皇帝,我就说一句话,他们都还是不错的“主儿”。这里要说的清圣祖,说什么爱新觉罗·玄烨,有些绕口,像个老外的名字。说到康熙,就如雷贯耳了。其他不说,单凭他在位六十余年,就了不起。
最早知道康熙的,是那本《康熙字典》。相信很多旧式文人的书柜里,都有这本书。字典是集字的大成,而康熙,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集了皇帝的大成。两千多年下来,历代皇帝都做出了经验,形成的资料也愈来愈多,让我们对皇帝的了解,愈来愈方便。但是,权威性相对弱一点了。实际上,就缺这种字典的权威。
关于康熙皇帝,正史里有许多东西,民间里还有更多的东西,都说着这位皇帝的了不起。因此,这也让我这一类的闲话,无从说起了。正经话被史籍讲完,不正经的话又被民间接着说,我夹在中间,说什么都多余,只能闲扯了。我就按照字典的风格,扯到哪里就到哪里吧!
康熙是顺治的第三个儿子,据说,他从小好学,喜欢骑射,不爱喝酒,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康熙即位的时候,还不满八岁。也就是小学二年级的年龄,但超过了小学二年级的水平。他与辅政四大臣之间的权力争斗,被史学家们奉为政治游戏的经典。康熙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完全掌握了朝政,将善于玩弄权术、骄横跋扈的鳌拜等人,一一铲除。然后,以少年天子的翩翩风度,坐稳了皇帝这把交椅。这些历史,现在不用看书,坐在家里看电视,就能知道。
康熙亲政后最为惊心动魄的,就是“削三藩”,即镇压三个地方割据势力。他们是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人分别盘踞云南、广东、福建。这三位本来就不是“自己人”,虽然在清兵入关时立下汗马功劳,但终究是“叛臣”。既能叛明,肯定也会反清。只要迈开了第一步,下面的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是惯性了。康熙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以他少年人的判断力,以及对局势的总体把握,你还不能不说这是奇迹。当时的“削藩”,造成了大半个中国的动荡,对新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康熙坚持己见,严厉驳斥那些“护藩”的论调,他说:“三藩气焰日炽,撤亦反,不撤亦反。绝不能仿效汉景帝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的做法。”这孩子把历史读进去了。而且,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这里一定要说吴三桂,这位号称“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好汉,在他的晚年,被少年康熙逼得如同一只疯狗,闹出了许多荒唐的事。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看大势已去,急忙命人在衡阳草草修建了百余间庐舍,并用黄漆涂满屋面,权且作为皇宫。到了三月十八日,这位吴兄又匆匆祭了天地,封了皇后,把一顶皇帝的帽子硬戴在自己头上。巧的是,此时风雨大作,那些临时的庐舍朝殿,被风刮得东倒西歪,那些象征帝王的黄色油漆,也被雨淋得面目全非。大家十分败兴。是啊,各种借口,毕竟是借口,永远不会成为结果,或成为真正的理由。吴三桂是做了五个月的皇帝,从过瘾的角度来看,还算不错。史书上讲,他在六十七岁时,死于中风噎嗝症。这种病,是气出来的。
这场“削藩”的战争,前后持续了八年,将康熙的政治才能和军事远见,发挥得淋漓尽致。它不仅仅是一场内战,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康熙一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影响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因素,从来都源于内部。接下来,康熙出兵收复了台湾,事关国家主权,康熙寸土不让。接着的抗俄战争,以及平定噶尔丹的叛乱,也就小菜一碟了。政治斗争的过程,往往是一顺百顺。只要路线、方针对头,人又肯吃苦,取得胜绩,就是时间的问题。(www.zuozong.com)
康熙一朝的“安内”和“攘外”,使他的政治手段日趋艺术化,可以作为教材或范例。战争只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则是在处理和协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矛盾上。
别的不说了,就说康熙如何对待明朝遗老遗少的。改朝换代,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家常便饭。时间一长,习惯会成自然。不太能习惯的,是一些文化人。他们的固执,同样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看过朱耷的画的人,都能看出他的一枝竹子、一只鹰或者一块石头,始终在生气。这种生气有道理,但不解决问题。清朝是满族人甩着辫子建起来的,而康熙同样甩着辫子,想如何把它弄得牢固。他始终认为,“士为四民之首,要争取民心,扭转汉族人民的反清立场,关键在于促使汉族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化。”为此,他做了一系列的动作。他南巡时,多次拜谒明太祖的陵墓,亲笔题写了“治隆唐宋”的匾额,挂在陵前;他跑到孔庙,大搞祭祀活动,并对孔子的后裔遍施恩宠;他专门设立了“博学鸿词科”,千方百计吸引明朝遗老参政。有意思的是,在康熙十八年,也就是1679年的体仁阁考试中,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学者,不仅给应试者发了可观的返路费、衣食费,还亲自请他们吃饭,并象征性地阅改考卷。一些文人故意把文章做得不通,康熙也一概录用,而且统统都是一等。高官厚禄,使大部分家伙放弃了吃辛受苦的遗老身份。从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原则问题了。天下一家嘛!
当然,这些放弃“原则”的文人,大部分都是二、三流的。真正一流水平的,如顾炎武、黄宗羲、李 等等,因为他们是一流的,因此始终不会流入清廷。其中有一些有趣的事。当年,关中大儒李
等等,因为他们是一流的,因此始终不会流入清廷。其中有一些有趣的事。当年,关中大儒李 ,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拒绝应试,被强行抬到西安。李
,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拒绝应试,被强行抬到西安。李 绝食六天以示抗议,官府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康熙来到西安要见他,李托病不见,他也只好作罢,还悻悻地写了一块“志操高洁”的匾额送给他。太原的傅山,也是被人抬到京城的城门口,赖在轿子里拒不进城。京中的王公大臣慕名来看他,他就装傻。弄得康熙无计可施,只好随他去。康熙之所以能容下这些人和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名满天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只著书立说,对政权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十分透彻。
绝食六天以示抗议,官府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康熙来到西安要见他,李托病不见,他也只好作罢,还悻悻地写了一块“志操高洁”的匾额送给他。太原的傅山,也是被人抬到京城的城门口,赖在轿子里拒不进城。京中的王公大臣慕名来看他,他就装傻。弄得康熙无计可施,只好随他去。康熙之所以能容下这些人和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名满天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只著书立说,对政权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十分透彻。
有水平,还要廉政、勤政,才能把事情做好。康熙在这一方面,也堪称楷模。他在位的六十一年如一日,有奏必阅,有阅必批,从不让人代笔。即使外出狩猎,也秉烛批签,常至深夜。要忙这么多事情,提这么多意见,然后再通过文字,把意见传达下去,光写字就能把人累死。事情不大,但足以见其作风。
《清史稿·圣祖本记》说:“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赐。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为开创焉。”这个评价,并无过多的溢美之词,很朴实。如同书架上的一本字典。平时站在那里不吱声,到了有用的时候,就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还是一种规范。
一个朝代的兴衰,都不是孤立的,都有着深刻的前因后果。康熙一朝的长治和久安,与他相对稳定的施政方式,以及特有的个性和原则分不开。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执政的时间长了,很多东西成了惯性,不需要动脑筋,这也失去了创造性。很多事情都是两难的。
世界上的每一本字典,都需要不断修订,使之日益完善。初版的,也许当事人看不到了,而后来者的任务,一个是学习,另一个还要继续创造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