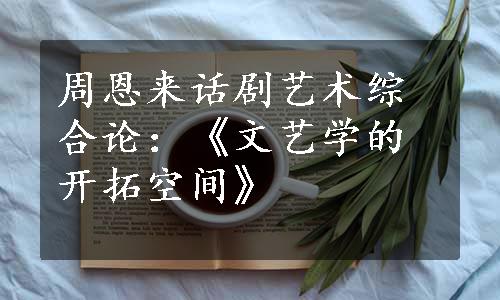
杜寒风
话剧艺术是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艺术形式,对于时代的发展及人们的审美活动发生着独特的作用,话剧融合了文学、表演、音乐、美术、舞蹈等成分,话剧有其独特的魅力。周恩来早年曾经作为话剧的一个业余表演者、编导者上过舞台,一生当中就其文艺活动来看,对于话剧如同他对电影等艺术那样十分爱好,喜欢看话剧,具有丰富的观赏经验,对话剧艺术的综合性有他的基本认识。本文是对周恩来的话剧艺术综合论所做的勾画、研讨。
话剧有话剧自己的基本规律,周恩来充分认识到话剧艺术有它自己的艺术要求,有其艺术的特色。如果不承认话剧的基本规律,不搞基本训练,抱有演话剧很容易,只要会说话就行,那势必不能演好话剧。把话剧艺术简单化,自是不尊重话剧的规律。周恩来说:“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1)可见周恩来对话剧艺术的把握上是很到位的,承认它是一种综合艺术,是由不同艺术的元素综合而成的舞台艺术,话剧不是简单的说话,说话谁都能说,话剧之所以是艺术,而不是普通的说话,就在于它所具有的艺术性。周恩来讲,毛主席不爱看话剧,因为话剧太像生活,又因为语言不够好。毛主席看戏不像我们,他看戏主要是为了休息。戏剧不是把生活搬到舞台上去就行了的,戏剧与实际生活是有区别的(2)。毛主席曾说,话剧没什么看头,就跟平常说话没什么区别。所以,毛主席总不喜欢看话剧,这也是一个原因。毛主席的意见表明,我们话剧的表演中还存在着若干自然主义的地方,应该杜绝这些毛病(3)。周恩来还指出,“中国话剧的好处是生活气息浓,但不够成熟,话剧台词就像把现在我们的说话搬上了舞台。”(4)如果话剧不从综合艺术的角度来认识,只是满足于说说话,表演时自然状态的东西多,就难以吸引广大的观众进到剧场观看。不同话剧中多种因素的综合性是服务于不同话剧的具体要求的。话剧也要像戏曲那样,要能听,还要能看。话剧是视觉与听觉的结合的一种综合艺术。周恩来深有体会地指出:“我觉得话剧很有讲究,通过语言来教育观众,这不是每一个会说话的人都能做的工作,而是一项专门的学问。”(5)话剧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剧种。这个剧种充满了学问,艺无止境,需要不断钻研、探索,从而不断把话剧的发展向前推进。
“话剧要写出艺术的语言。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语言、严谨的政治语言,又不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而是要提炼成真正的舞台的语言、银幕的语言。”(6)舞台的语言、银幕的语言,是加工了的艺术语言,经过了编剧、演员、导演等创作人员的处理,乃至于精心的锤炼,就语言说,正是话剧这门艺术区别于政治语言、日常生活语言的重要方面。当然,话剧的艺术语言是从生活语言中加工提炼而来,可以使用政治、科学技术等等术语概念,这是基础。生活语言是话剧语言创作的源泉,脱离了它,话剧语言的才思就会枯竭。周恩来看了《同志,你走错了路!》这出戏,在他思想上解决了一些问题。过去,他总是在想,将来这话剧、电影怎么办?他主要指的是语言问题。这语言问题有两个内容,一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语言,我们有我们的术语、习惯语言。经常说的话,跟外边不一样。如果把国民党在某种场合常用的语言,搬到我们的戏里,那我们就不伦不类了,那样不行。这回,他看戏里所用的语言,都是我们的“土产”。另外就是这“舞台腔”怎么办?大家都曾发过愁,不论什么人出来,都是学生腔、学生调,中不中,洋不洋,拿着一个腔调。这回,他一看,戏里解决了这个问题。戏里,有河北人,有山东人,有四川人,也有湖南人,都是一口的家乡话。咳!听起来亲切、真实,南腔北调,这就是我们的队伍嘛!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样!(7)周恩来认为这出戏很成功,这是第一次让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我们真实的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形象。过去,在舞台上也曾表现过共产党人、八路军、新四军,但无论在形象上还是语言上都不行。而《同志,你走错了路!》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形象、语言符合实际,人物、故事真实可信(8)。话剧使用的语言,要符合所表现内容的需要,脱离具体的生活,使用语言不当,就难达真实可信。表演当中,舞台腔也同样不利塑造人物,千篇一律,就没有特点。话剧语言的艺术性,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周恩来对于戏剧大师曹禺的作品比较欣赏,对之评价不低。他说,“曹禺同志剧本中的语言,有些好的台词,我们能背出来。鲁妈对周萍说的一句话:‘我就是你——你打的那个人的妈。’这是名句,被新的导演删去的。邓颖超同志发现的,向导演提出以后,才又恢复。好台词是百读不厌的。其他作家也有好语言。”(9)好台词是好的语言,经过锤炼,成为人们喜欢的东西,乃至于可以成为经典。话剧的经典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是一些应时剧,没有经过精心的创作而昙花一现,成为过眼云烟,经典话剧的语言,更是有讲究,它独有的艺术魅力决不是政治语言、日常生活语言所能带来的。
话剧在周恩来看来,它不同于活报,他说:活报是游行配合任务的一种宣传形式,一出场就可以看出哪是好人,哪是坏蛋。话剧是一种舞台艺术,使人看了以后,既受到教育,又留有回味(10)。他是反对把话剧当成是活报来演,这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不能混淆。周恩来认为,话剧和电影比较接近。承认它是和电影一样的综合艺术。“在文艺界我发现个问题,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也不管谁,自己搞自己的:导演搞导演的,灯光搞灯光的,布景搞布景的,服装搞服装的,这样不能创作出好的东西来。话剧是综合艺术,各人搞各人的,怎么可以呢?”(11)话剧艺术既然是综合艺术,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艺术整体观念,不能各行其是,各行其是就割裂了整体,破坏了艺术的有机统一。服从整体的艺术需要,就要有通盘的考虑、设计,才能避免出现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分割局面。整出戏就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作品,协作是必不可少的。各自为政,各搞各的,就无法在综合性上实现较为完美的统一,取得协调一致的艺术目标。说明周恩来对话剧艺术有一种较为综合的捕捉,有整体的意识。
话剧作为舞台戏之一种,是要表现戏剧冲突,不能回避矛盾。剧本写冲突,写矛盾,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无冲突无矛盾就无戏,是有一定道理的。周恩来了解话剧需要有起伏,有变化,高潮出现,正是逐步形成的,话剧绝对不是平铺直叙的。“剧本要写冲突,要写矛盾。冲突本身必然要发展,不然形不成高潮。从头到尾冲突不突出,或突出而不发展,都不好。《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好处,就是有认识的发展。因此写冲突,一要突出,二要发展。”(12)1960年1月29日,周恩来审查话剧《文成公主》彩排后,召集开座谈会,指出:戏要写得更有发展些,自始至终围绕民族团结亲好做文章(13)。1963年的1月,周恩来在上海看过上海人艺演出的话剧《第二个春天》,他对该剧的结构、冲突、基调都作了细致的研究(14)。《看<豹子湾>战斗后的谈话》中,周恩来分析剧中人物说道:丁勇通过实践提高认识,再实践,不断飞跃。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但不是矛盾的重复。人物要有发展。不但丁勇要有发展,指导员的工作也要有发展;高大力、王二保、吴彩凤、朱老爷爷、朱小兰都应当有发展。不要重复前面的矛盾。丁勇在第三幕对纺线的抵触,不要和第一幕一样。丁勇对纺线任务可以抵触:“老娘们干的活嘛”。但思想应当通得快些。指导员不必等丁勇说那么多才发言,也不要等指导员说多少次丁勇才觉悟;应当是指导员一点,丁勇很快地就觉悟,就去请战。现在就太作戏了。不要停留在笑声中,人物要向前发展。周恩来结合人物讲了辩证法,讲了人的认识过程,这样做是有利于刻画好丰满的人物形象,有利于戏剧冲突的有序展开。话剧里的人物是有发展的,重复前面的矛盾而没有新的矛盾,就没有新的发展。老矛盾重复来重复去,就没有什么吸引观众的地方了。而为了取得某种剧场效果,搞噱头过多,太作戏也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话剧也有个时间问题。“总不能太长,使演员、观众都不要太累,看完后才觉得余味未尽,有个咀嚼。时间问题,也就是整个剧本的结构问题”(15)。剧本有一定篇幅的限制,受到了舞台演出的制约,剧本要适合舞台演出的需要。
我们常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话剧的质量、格调等。毋庸置疑,剧作家的文学剧本的底子就是举足轻重的了。周恩来对于话剧的一剧之本十分重视,没有好的剧本就不大可能产生精品意义上的话剧作品,在话剧文学上就站不住脚,根基不牢。剧作家要敢于写,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是搞好话剧创作最首要的工作。周恩来以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党员曹禺为例,说明剧作家不能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批评了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思想意识。曹禺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与过去相比,曹禺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周恩来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周恩来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16)。周恩来虽说是不留情面地检视了曹禺在解放后创作上的失误,但不是完全否定一切,也有肯定,反映了他是以观众的角度、以朋友的角度来分析作品,不是由上至下下命令看待作品,是比较能为剧作家接受的。其目的是用以让大家解放思想,不要为新的迷信所束缚,有勇气、有自信心,敢说、敢想、敢做,在创作上才能有收获,有进步。
周恩来阅读过剧作家的剧本,即使剧本在舞台上演出过,他还要提出一些修改的建议,当然他是建立在尊重作者劳动的基础上的,他既是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视野看话剧的,也是从一个有高度艺术修养的欣赏者的角度看话剧的。这样他所做出的有关建议,就有别于专业的话剧工作者,有周恩来独特的地方。周恩来写过《对<棠棣之花>的意见——致郭沫若》,谈了读过剧本《棠棣之花》的一些修改意见,指出该剧有刺耳的地方:“所谓刺耳,非刺我耳,乃刺人耳也。”周恩来在字句上做了仔细的斟酌。第二幕、第三幕、第四幕、第五幕都有周恩来修改字句的意见。周恩来以为,能改得不句句刺耳,似较妥。从修改意见中,可见周恩来的文学素养及政治素养等等。周恩来在看过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后,写过《期待在付印前读到剧本——致姚仲明、陈波儿》,信中对姚仲明创作的话剧剧本《同志,你走错了路!》的修改很关心,也可见其一斑(17)。周恩来讲:“比如最近演出的一个话剧,写得很实际,但严格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还不够高。有的戏过了一个时候再看,就不那么动人了,不能持久。这说明加工修改的重要,要继续丰富和提高。”(18)
在修改剧本中,对他人的意见也要有分析,毕竟是剧作家的精神劳动,这种精神劳动以剧作家个体为主。“就是集体创作吧,总得有个人执笔。如果你写一笔,我写一笔,那就不成其为剧本,而成了记录了。我们的老舍同志有这个经验,《方珍珠》前一段很好,后一段由于听了人家好多意见,结果把它改坏了。”(19)修改剧本,既需要剧作家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也需要剧作家有自己的主见,努力遵从艺术规律去修改,就不会破坏剧本。
“服装,总要跟剧情统一,还有个时代问题。”(20)即使对于舞台上人物的服装、打扮的一个细节,观众不大注意的地方,周恩来观察得也很仔细。1956年5月他观看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演出的《日出》,看完后与大家交谈时就陈白露头上插的花儿,建议应该戴一朵白颜色的花儿,插一朵粉色的花儿不适合这个人物。他对大家讲了陈白露的出身、性格、旧社会对她的逼迫等一系列简明精辟的意见,说基于此,戴白花能反映她的性格(21)。《霓虹灯下的哨兵》女特务曲曼丽穿了一身考究的裙服,总理马上指出:“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是不会穿这种服装的,最好改穿工装裤,要朴素些。”导演遵照总理的意见,让演员换上了工装裤。不久,总理又来看戏,发现曲曼丽的裤腿改得又瘦又短,看上去像个阿飞,他马上又提出来,裤子要改一改,既然给她穿工裤,就要像个工人,不能妖里妖气,不要一出场就让人看出她是个坏人,应该随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加深,逐步揭露出来,不然就看不出她的伪装(22)。政治上伪装,外表要像个正派人,通过行动,逐步暴露(23)。即使是反面人物的服装、化妆也需要好好研究,不能做简单化的处理。演员不能脸谱化,服装上也要符合人物的身份。
灯光也是需要注意的方面。周恩来从观众观看的角度出发,主张灯光要适当,不要发暗,影响观众的视力所及。他观看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杜鹃山》,说“《杜鹃山》的灯光太暗了。暗得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很反感。观众也有这样的反映……灯光是配合戏的,不能自搞一套……我们演戏是为了观众看的,你让观众看不见,戏到底宣传什么呢?你们这里是不是导演说了不算,要听灯光的?”(24)灯光不能完全喧宾夺主,摆错了自己的位置,让观众看不清,是不对的。除非是追求特殊的艺术处理,带来特殊的艺术效果,是为了剧情的需要。周恩来讲,“《杜鹃山》这个戏的第五场,现在线索太乱,再加上灯光太暗,戏的头绪就更看不清了。杜小山怎么又回到他家?乌豆先下山的,怎么贺湘会先到这里?乌豆哪里去了?敌人为什么没有埋伏,而贺湘他们倒埋伏得很顺利?总之,看不明白。灯光暗得看不清,看了半天才明白是自己人。”(25)“灯光,当然可以有明暗之分,但基本上是明朗的。因为要让人看动作和表情,并不是要进入自然主义。”(26)灯光须为观众服务,不能对观众的看戏产生阻拒作用,让观众如坠雾中,看不清舞台上的布景、人物等等。针对《杜鹃山》这出戏观众反映灯光暗看不见的意见,周恩来说:“为什么不加亮、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呢?是否这是专家的意见呢?专家的意见也需要三结合,而三结合中最基本的是群众的意见”(27)。周恩来在此是心系群众,为群众着想,很尊重群众的意见的。
对于话剧中的音乐,周恩来同样是从服务群众的观点出发。话剧中的音乐也存在着问题。周恩来指出,“如《杜鹃山》第一场乌豆与杜鹃妈妈一段话,突然出来音乐,为什么?看不出道理,反而搞乱了戏。过去搞话剧像《蜕变》、《北京人》等都没有配音乐,反而使我们能很安静的欣赏艺术。《屈原》是到了最后‘雷电颂’才有一点音乐配合朗诵。后来赵丹演《屈原》搞的大乐队,我看反而没有以前的好。为什么现在的话剧都必须有音乐呢?是不是向苏联学的?受苏联影响?不要学这些!花钱请乐队更不必要了。现在每场戏都加音乐,有的也不调和,声量大,太刺激人。话剧就是话剧,音乐加得不好,反而影响了戏。”(28)对话剧来说,音乐同样也不能喧宾夺主,影响观众对话剧的欣赏。合适的音乐会有助于台词的表达,而过头的音乐不会起到好作用,会给观众添乱。“音乐,用民族调子,就一切服从民族调子,旋律要比较民族化,不要搞一点西洋调子进来。”(29)1953年6月16日周恩来观看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练的《屈原》,接见导演、演员等人时曾说:新创作的《屈原》音乐风格不调和,最好用些箫、笛、琴、琵琶等中国乐器,现在的音乐将来可以独立演奏成为《屈原组曲》(30)。对于音乐,周恩来对民族音乐是情有独钟的,不以西方音乐代替民族音乐。
关于布景道具,周恩来指出,“布景道具,又有真门,又有假门,一会儿真,一会儿假,看着不舒服。”(31)希望布景道具也风格一致,弄得不伦不类,同样破坏整体的艺术氛围。195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完后,周恩来上台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布景和道具,对布景等给予了肯定(32)。
周恩来说,舞台戏“唱腔、动作、灯光、音乐、布景道具、服装六个问题,总要统一和谐”(33)。话剧没唱腔,但有说话,也是要统一和谐的。周恩来强调,“最低限度是统一和谐,进一步还要明确生动,目的性非常清楚。不能弄得晦暗,要人来猜。艺术的表现形式,要统一、和谐、明确、生动。这样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教育我们同时代人和后一代青年”(34)。1963年2月周恩来在北京连着看了三场由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记得是第三次看演出那天,周总理边看边作指示,漠雁在小本本上记下了三十五条意见,对该剧的主题、人物、情节、台词、服装道具、音响效果等都一一作了具体的指示(35)。周恩来以为,一个戏要统一、和谐,不要脱离主题(36)。综合艺术的话剧,可以从整体上做到几个环节的一体交融。
周恩来主张话剧、电影都要考虑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既要有独特的风格,又要兼容并包(或叫丰富多彩)。独特风格是主导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个性,不然为什么叫‘剧种’呢!……学人家的是丰富自己,但自己没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样的艺术就会消亡。”(37)每个剧种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剧种的地方,不同剧种是有不同的限定,但又不是固步自封的。他举例说,他看了江西弋阳腔排演的《昭君出塞》,觉得很好,也觉得有些话剧色彩。到后面去看到了石凌鹤,才知道是他排的。石凌鹤从重庆时期排《棠棣之花》,到这台《昭君出塞》都很成功,就因为有独特的风格(38)。话剧作为一个剧种,使它与其他剧种相区别。周恩来的意思是,即使是在话剧的内部,也要允许不同导演风格的存在,表演风格的存在,风格的多样,可促进话剧艺术的繁荣。另一层含义是,戏曲与话剧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影响、交融可形成独有的风格,再扩展地说,话剧艺术与姐妹艺术之间完全可以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从而促进各自艺术的发展。周恩来曾说昆曲《十五贯》这个戏的表演、音乐等,既值得戏曲界学习,也值得话剧界学习。“我们的话剧总不如民族戏曲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有些外国朋友认为,中国话剧还没有吸收民族戏曲的特点。”(39)如果我们的话剧艺术能充分吸收戏曲等民族艺术的特点,在世界话剧舞台上我们的特色就更加鲜明、更加彰显。作为综合艺术的话剧与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戏曲不同,在于它的艺术语言的不同,艺术特色的不同,艺术规律的不同,自然话剧在舞台上塑造的形象就与电影在银幕上塑造出的形象不同,也与同为舞台演出的戏曲在舞台上塑造的形象不同,重在语言艺术的表达,重在戏剧冲突的展现,重在与时代生活的联系等等,都使话剧艺术散发着迷人的光芒,而让人在剧场中流连忘返。
(作者杜寒风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注释】
(1)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参见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48页。
(3)参见周恩来《观话剧<雷雨>后的意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04—205页。
(4)周恩来:《<十五贯>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周恩来文化文选》第155页。
(5)周恩来:《<十五贯>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05页。
(6)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56页。
(7)参见王永芳《这沉沉的花圈……》,陈荒煤、陈播主编《周恩来与电影》第150—1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8)参见王永芳《这沉沉的花圈……》,陈荒煤、陈播主编《周恩来与电影》第149页。
(9)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56页。
(10)参见白刃《感想与回忆》,陈荒煤、陈播主编《周恩来与电影》第467页。
(11)周恩来:《对话剧<杜鹃山>剧本及演出处理的意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62页。(www.zuozong.com)
(12)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几个原则》,《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93页。
(13)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85—2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4)参见漠雁《周总理领导我们写现代戏》,《解放军报》1978年2月24日。
(15)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几个原则》,《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94页。
(16)参见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41—242页。
(17)参见周恩来《期待在付印前读到剧本——致姚仲明、陈波儿》,《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8)周恩来:《<十五贯>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周恩来文化文选》第155页。
(19)周恩来:《关于戏曲改革的几个问题》,《周恩来文化文选》第121页。
(20)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几个原则》,《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94页。
(21)参见李默然《是总理,更是朋友》,陈荒煤编《周恩来与艺术家们》第53—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2)参见陶玉玲《辛勤的耕耘才会有灿烂的未来》,陈荒煤、陈播主编《周恩来与电影》第375页。
(23)参见漠雁《周总理领导我们写现代戏》。
(24)周恩来:《对话剧<杜鹃山>剧本及演出处理的意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60页。
(25)周恩来:《对话剧<杜鹃山>剧本及演出处理的意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61页。
(26)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几个原则》,《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94页。
(27)周恩来:《对话剧<杜鹃山>剧本及演出处理的意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63页。
(28)周恩来:《对话剧<杜鹃山>剧本及演出处理的意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62页。
(29)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几个原则》,《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94页。
(30)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31)周恩来:《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周恩来文化文选》第186页。
(32)参见李树谦编著《春风化雨——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第81—8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33)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几个原则》,《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94页。
(34)周恩来:《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周恩来文化文选》第186页。
(35)参见漠雁《周总理领导我们写现代戏》。
(36)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75页。
(37)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几个原则》,《周恩来文化文选》第294页。
(38)参见荒煤《永远铭刻在心间的会晤》,陈荒煤、陈播主编《周恩来与电影》第52页。
(39)周恩来:《<十五贯>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周恩来文化文选》第15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