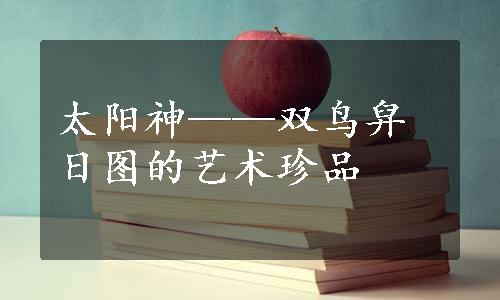
“双鸟舁日”,就是本书开卷描述过的那件绘刻在蝶形象牙块上的画面。凡是看到过这件作品的人,无不为它的艺术魅力所倾倒。作者大胆巧妙的构思,娴熟流畅的线条,主题之明朗,艺术形象之完美,不但在璀璨的河姆渡艺术长廊中堪称精品,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称得上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双鸟舁日图》绘刻在一件蝶形象牙块上,发现于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充满画面的是两只巨鸟,拱护着中间一个光焰熊熊的火球搏击升空。巨鸟利喙长尾,昂首奋翼,显示出无比雄健与伟力;火球从中心圆点出发,向外连续辐射出五个同心圆,加之在外圆的上方添上几笔腾腾的烈焰,感觉热力逼人,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那个万物赖以生存的太阳。对这件超现实的作品,已有颇多研究者论及,一些文章中名之曰“双凤朝阳”,另一些文章则名之曰“双鸟朝阳”“凤”与“鸟”看似有别,但在对这件作品的动态解释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朝”。
在考释一件远古时代的艺术品并作出相应结论的过程中,正名是第一要义。如果命名不当,其引申出来的辨析难免会偏离事物的本原,导致南辕北辙。名之不正,是由于义之不明,其义一明,其名自正。
诚然,要探索远古时期人类的艺术创造,探索原始人心灵活动的隐秘,探索对神灵的崇拜和宗教信仰,其难度远比考析他们创造的物质文化要大得多,正: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哈斯说的,古代文化“有些模式可望由考古学家们在考古发现中得出,有些模式则不能。一般说来,他们越是研究‘人类文化多层饼’的较高层次,即从基础到一般结构,再到上层建筑,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个诫示性的警告对任何涉足史前文化研究的人都是有用的。因为生活于20世纪的人是无法再返回到五、七千年前的史前时期,当然也不易复制初民们那种幼稚、率直、神奇、荒诞的想法和行为由于有些研究者囿于生活经验的局限,而多数人又缺乏作野外考察和民俗调查的条件,对某些史前文化现象的探索,就难免发生偏颇。
“双凤朝阳”与“双鸟朝阳”显然是一个文明人的概念。诚然,以现代人所熟悉的名词来命名史前艺术的某些作品也未尝不可,而且有的还颇具精妙,使文明人与原始人的巨大时空差一下子得以拉近,但这应以合乎事物的原来特征为前提,不然会给人以“原始人穿时装”之感。以“双鸟朝阳”或“双凤朝阳”命名河姆渡这件象牙圆雕之所以不当,毛病在于一个“朝”字。在这里,“朝”的特定含义与我们习惯上所熟悉的“百鸟朝凤”、“诸侯朝天子”这类词语中的“朝”同义,具有“朝拜”、“朝见”的意思。这显然偏离了河姆渡初民创作这件作品的原意。因为第一,从画面构成观察,处于太阳两边的相向的两只巨鸟,是紧贴着太阳的,昂起之首稍高出于太阳,其胸膈几乎和太阳连成一体,画面展示的态势显然不是“朝见”或“朝拜”而是呈现出“拱护举”、“扛”、“抬”的形状。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画中的一对神鸟与太阳,应是一个整体,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特定的构图中,太阳是作为一个发光发热的球体,而双神鸟是太阳赖以飞升天穹的运载工具。
神话故事,神灵崇拜,宗教信仰,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应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它们包含着超自然或神圣的力量;二是表达了信仰者的思想意识,无论这种表达方式具体与否。而神灵崇拜(超自然力的崇拜),则既有人的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因素,又具有人的心理因素,可以说它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产物。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虽已步入了农业文明时代,其人工栽培稻谷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稻谷生产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谓之“原始农业规模阶段”),成为氏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但整个生产力仍是极其低下的。太阳对于原始人来说,它的重要性不知要比现代人高出多少倍。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恒星、行星等天体运行的规律,只觉得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的大海中升起,逡巡天穹,傍晚又落入西边的群山中,往复循环,周而复始,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力量能使这个炽烈的圆形球体升上天穹,常令他们想入非非在原始人的直观中,只有有翅膀的动物才能离开地面升上天穹,而鸟又是飞行生灵中的佼佼者,一击双翼扶摇直上,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对一些南来北往的候鸟,更是充满神秘之感,因而他们想像一定有两只巨大的神鸟,每天从大海中舁起太阳,运行于天穹。
“双鸟舁日”正是原始人直观与神奇联想的复合,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太阳与神鸟是宇宙中最高神灵特意安排的,一个发热发光,一个负责运载,两者是一个统一体,不存在朝拜与被朝拜之关系。“双鸟舁日”构图严密,造型神奇,刻线自然流畅,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在远古,它一定倾注了那个艺术大师全部的崇敬和虔诚。
由此不难推知,关于神鸟舁日的最初神话,它的产生与流传恐怕要大大早于河姆渡文化时代,比之这件象牙圆雕出世的的年代更要早得多,到了河姆渡文化时代已相当完整,才能创造出在思想和艺术上如此成熟和谐的杰作。它实际上神的产物。
蕴含着一个关于一太阳神的最原始的神话故事。这是人类崇拜太阳我国古代典籍上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关于太阳神的故事,有许多是源于河姆渡的双鸟舁日的。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一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关于太阳里有一只三足金乌的传说,由此而形成的具象,是将“双鸟舁日”的日外之双鸟,转化为日中之金乌,使炽烈的太阳与有生命的神鸟(金乌)完全融为一体。无论从思想内涵和艺术形象,后者均比前者前进了一大步。“日”之古象形字为“ “,中间符号“Z”即是飞翔中的金乌的形象。另一神话传说也是继承于河姆渡双鸟舁日的内涵,‘爰止羲和,爰止六螭,是为悬车。”《淮南子》记载的就是“六龙驭日”的故事,六螭就是六条龙。与许多事物一样,神话故事也是在不断流动变化着,这个时期,大概人们对龙的神威的崇拜大大超过了其他灵物,关于运载太阳的重任,当然非龙莫属了。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总是将“金乌”和“六龙”作为太阳神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贯澒蒙以东竭兮,维六龙于扶桑”(《楚辞》刘向《九叹·远游》)。“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韩愈《李花赠张十二署》)。均是前人将“金乌”及“六龙”作为太阳代称的证明。由此也可推及,河姆渡“双鸟舁日”中的双鸟也具有“金乌”“六龙”相似的涵义。由“双鸟舁日”→“金乌载日”→“六龙驭日”,是关于太阳神的神话和具象的合乎中国文化思想逻辑的发展的。前者与后者具有源与流的关系。
“,中间符号“Z”即是飞翔中的金乌的形象。另一神话传说也是继承于河姆渡双鸟舁日的内涵,‘爰止羲和,爰止六螭,是为悬车。”《淮南子》记载的就是“六龙驭日”的故事,六螭就是六条龙。与许多事物一样,神话故事也是在不断流动变化着,这个时期,大概人们对龙的神威的崇拜大大超过了其他灵物,关于运载太阳的重任,当然非龙莫属了。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总是将“金乌”和“六龙”作为太阳神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贯澒蒙以东竭兮,维六龙于扶桑”(《楚辞》刘向《九叹·远游》)。“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韩愈《李花赠张十二署》)。均是前人将“金乌”及“六龙”作为太阳代称的证明。由此也可推及,河姆渡“双鸟舁日”中的双鸟也具有“金乌”“六龙”相似的涵义。由“双鸟舁日”→“金乌载日”→“六龙驭日”,是关于太阳神的神话和具象的合乎中国文化思想逻辑的发展的。前者与后者具有源与流的关系。
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在进化过程中,对一些相同事物的看法,大致经历了相似的思维发展阶段,尽管此类进化与思维经历并不总是同步的。太阳怎样运行于天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为之设想的具体方式虽各有不同,但这轮炽烈的火球需要借助运载工具才能升空运行的想法,却往往是不谋而合。如古埃及和古希腊人也都认为太阳是借助其他运载工具才能逡行于天穹。前者认为太阳是由一艘船载着驶过蓝天的,后者则认为是由一辆长有翅膀的驷马驾车载着横过天穹的。地中海沿岸一带国家民间绘画或雕塑的太阳神,更是直接给太阳安上了一对鸟的翅膀;一个有翼的太阳(神)在极大多数地中海东部国家受到崇拜。上述国家和地区对太阳神的塑造虽比河姆渡文化时代晚了许多,但彼此对太阳运行的理解却又如此惊人地一致,由此也可证明,将河姆渡太阳神象牙圆雕称之为“双鸟舁日”并非是笔者的杜撰。
破释史前文化的神秘之谜,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这把金钥,去打开一重重为岁月尘封已久的大门。但这样做需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从那个特定的史前时期的文化延伸到今天的文化之链应是相对地连贯的,也就是说没有发生过足以中断这条文化之链的重大缺环,不然的话,金钥也会有可能开错了门而误入歧途。太阳是如何升起来的,又如何运行于天穹,这类今天连小学生都能回答的问题,在浙东一带,尤其是四明山一带的民间,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仍然坚信太阳是神鸟从大海中背负上来的古老神话,时至今日,如果有孩子问上了年纪而又一字不识的爷爷,太阳是怎样升上来的,老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太阳是神鸟从大海中背负上来的。类似的回答绝不是个别的。这是因为四明山地区比较封闭,因而一些古老的文化氛围得以传承下来。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史前艺术品并非总是寓有象征或崇拜,以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艺术品而言,具有这类属性的器物只有屈指可数几件,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几,大量的是属于审美方面的。如何来判定它们的不同属性,下述三条当可作为衡量之参考。第一,这件原始艺术品与后来史籍记载的特定神话传说或神灵崇拜是否存在着源流关系;第二,它在当地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中能否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三,它的直观具象是否具有超真实的怪诞形象和神秘氛围。河姆渡双鸟与太阳的象牙圆雕完全合乎以上三个条件,作为太阳神的具象应是没有疑义的。
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本文开头的正题,也就是说根据这件圆雕所展示的具象以及它的内蕴应该正名为“双鸟舁。舁,古文为“舁”。《说文》:舁「共举也。”段玉裁引徐注:“共举,非一人之辞也。”用在这里没有其他文字比之更为贴切精当的了。这里笔者还想简单阐释一下关于这件作品的“凤”、“鸟”之争的看法。即对于舁日之双鸟,有的文章泛指为“鸟”;有的文章专指为“凤”。“双鸟舁日”之鸟是否是一对凤凰?“双凤舁日”说是否说得通?在我国古籍的记载中,除了“凤凰朝阳”表示祥瑞的成语外,很难再找到关于凤凰与太阳关系的故事传说,因而“双鸟”不可能是凤鸟。那末是否会是一对“金乌”呢,但跟画中双鸟的具象又相去甚远。从一些古籍的记载中,倒是跟鸾极为相近。在我,鸾是与凤并列的神鸟。《说文》:“鸾,赤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春秋·元命苞》:“离为鸾。”“离”是卦名。《易·说卦》:“离为火为日。”后汉《荀爽传》说得更具体:“在天为日,在地为火。”将上述记载列出公式:鸾=离=火=日。鸾即是太阳。但人们对此比较陌生,没有金乌那样影响深远。此外,鸾之作为一种运载工具,也是见诸于古人的文字:"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唐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将鸾描述为驾车的神鸟。能够驭车当然也能舁日,在河姆渡初民的心目中,这对舁日的双神鸟也可能是“鸾”。但这仅是推测,在没有作更深入考证之前,似不宜匆忙地下结论,还是以“双鸟舁日”为当。
“双鸟舁日”也可径直称之为太阳神。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这是人类最早创造的具有完整形象的太阳神具象。河姆渡是太阳神的故乡。
人类将一些重要的自然现象视作神灵,并加以崇拜,是与人自身在进化过程中所萌生的灵魂观念有密切的关联,也是人同自然环境这一对主体与客体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难解情结的产物。人一方面对超自然力充满畏惧,一方面又希冀通过对神的崇拜以求得其佑助。至于信仰何种神灵,则往往受环境因素和人的心理特征的制约。而其缘起,可能由于一种极偶然的触发。河姆渡初民将太阳的逡巡与鸟的运载结合只是一般的思维联想,它之最后构成“双鸟舁日”的具象,其过程无疑要复杂得多。比如,可能有人看到太阳冒出海面的辉煌瞬间,恰有一对巨大的海鸟从日影里掠过;也有可能碰到日食,原始人以为末日将临惊恐万状的当儿,瞥见了横过天空的巨鸟将太阳带出了黑暗的阴影;也可能是氏族中某个长者或巫师梦中的幻象;等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史前时期,双鸟舁日的联想,是合乎人类一般思维发展规律的。对河姆渡遗址的这件“双鸟舁日”,我们的探索不应仅仅停留于初民们对太阳运行的具象描述上,而须作其意蕴方面的进一步考析。对神灵的崇拜和祈求,说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处于极其低下状况下对超自然力现象的神化,希冀通过某种仪式以沟通人神感应,达到一定的祈求目的。“双鸟舁日”之作为太阳神的整体具象,无疑属于一种神(巫)器,在祭拜祈求活动时作供奉之用。
河姆渡初民向太阳神诉求什么?
这是“双鸟日”的深层次内涵。有的论者认为它“象征地表现了河姆渡人祈求丰收的愿望,但同时还可能表现了他们祈求降雨的愿望。”[1](——着重点为笔者所加)“祈求丰收的愿望”,这个推测当是不错的,至于作者用很大篇幅阐述的“祈求降雨的愿望”,这就值得商榷了。
在我国古代人的感知中,太阳总是与晴、热、火联在一起,所谓“大阳之精不亏”。河姆渡“双鸟舁日”中的日之外圆上部熊熊的火焰便是一例,认为火由日生,或日能生火。在前面引用过的《易·说卦》:“离为火为日”,和后汉《荀爽传》之“在天为日,在地为火“,也认为日与火同出一源。向太阳求雨,无异于向火神求水,向龙王求火;祈善神施凶,祈恶神赐善。诚然,这种两律背反的求神现象在历史上并非绝对地没有,但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个别事例,并不合乎河姆渡初民祈日的原始动因,如果将此视作普遍存在的现象并由此立论,则有悖于人类信仰求神的一般规律。作出向太阳祈求降雨的推论,其出发点当是河姆渡人为祈求稻谷的丰收。这个观点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搞清楚7000年前河姆渡一带制约稻谷丰歉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才能进而揭示河姆渡人祈求太阳的真正动机(愿望)。
我们在探索考析某些史前文明现象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仍将其置回到那个时代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中去加以综合考察,恢复其原本的位置,这样才有可能接近事物的本质特征。考析“双鸟舁日”的功能,也应该将它重新置回到7000年前河姆渡氏族这一特定的社会地理环境中去,以求得较真实的解读7000年前的河姆渡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呢?第一,以骨相为主体的大量骨器的发明和应用,将稻作推进到了一定规模生产阶段。人工栽培的稻谷已成为人们的主粮。第二,与稻谷同时发现的,已采用榫卯结构并在地面约1米处铺有一层木板的半楼式地面木构建筑群,其中有一幢延绵百米,分间多达38间,证明已建村落定居,且已具相当规模。第三,据地质探测表明,遗址及其周围系沼泽地,地势低洼,第四层居住面(生土)比今天的海平面还低1.8〜2米,而且四周湖泊河流交错。第四,据有关专家分析,当时气温要比今天高1℃~2℃(一说3℃〜4℃),南山森林茂盛,雨量充沛,而又集中于稻谷生长期内。
太阳之对于人类,在人的直接经验和感受中,原始人较现代人重要得多。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太阳不但驱走黑夜(而黑夜意味着黑暗,寒冷,饥饿和毒蛇猛兽袭击的恐怖,等等),而给人们带来光明,带来温暖,带来食物,同时也带来祥和与希望。早在人类初期,人类赖以生存的采集、渔猎,也主要在晴天进行。因而可以说,原始人对太阳的崇拜源于对太阳的需要和亲切感。
河姆渡文化时代已进入稻谷规模生产和村落定居,稻谷的收成直接关系着氏族的生存,而太阳紧紧连系着稻作的丰歉,从这一点说,天气现象对于农业时代的原始人远较采集、渔猎游动时期重要。但是,一些不太熟悉河姆渡气象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的研究者,一提到稻谷,马上便联想到今天遍布江南的水稻,总以为是水决定着它的丰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便引发出河姆渡初民崇拜太阳神是祈求降雨的臆测。殊不知在一个河网交错的沼泽地区,在雨水远较今天充沛的河姆渡文化时代,决定稻谷丰歉的主要是太阳而不是雨水。考古学家和农学家们对河姆渡遗址出上的稻谷不称“水稻”而称之为“稻谷”,这是很有见地的。这是因为原生野生稻谷就有山地早稻与宜干宜湿地区稻谷之分,“水稻”是人工栽培之后长期驯化变异的结果。河姆渡初民虽然人工栽培稻谷已进入规模阶段,但当时还未拥有人工灌溉工程和工具,在这片沼泽地上栽培的应是一种宜湿宜干的稻谷,其生命力尤其是耐旱力要比今天的“水稻”强得多,反之,多雨、低温、水涝、海浸等对稻谷构成的威胁更频繁,程度也更加严重,有时甚至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大量新鲜稻谷以及苇席等被湮埋,证明这是一次突发性灾异造成的,而这肯定不是旱灾而是水灾制造的恶作剧。
到了当代,“稻谷”虽已驯化为“水稻”;但在河姆渡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下,稻作之需要太阳,仍远远地超过雨水。“十旱九丰,十涝十歉。”是当地农民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因之是“谈水(灾)色变”。如春天,稻谷下播育苗亟须晴暖天气,但春天偏偏多雨、低温的日子居多,造成烂秧,俗称“未种三分歉”。稻谷生长发育期既需一定的雨水,更需要充足的光照和一定的积温。而春夏之间这一带也常有长期淫雨而低温,农谚“六月盖被,有谷无米”,“六月不热,稻谷不实”,“黄鱼打冻,早稻白种”,等等,就是长期阴雨低温、阳光不足对稻谷构成危害的真实写照。稻谷的孕穗扬花期,更须晴好的天气,若是遇上骤雨狂风,便会产生大量的枇子,俗谓“种种一大畈,收收一小担”,那境况可惨极了。到了稻谷收获季节,太阳晴好才能收割、晒燥、贮藏,以备一年之口粮,如果阴雨连绵,或突来台风暴雨,成熟的稻谷轻则倒伏发芽霉烂,重则刮落于地,造成丰产而不能丰收。而暴雨酿成的洪涝,更会给这片低洼地上的稻谷带来灭顶之灾。太阳之对于稻谷,可谓成败攸关。
因此千"年来,在当地流传着这方面的许多农谚,诸如:“头八晴,好秧性,二八晴,好种成,三八晴,好收成。”(注:农历正月每旬的八日)“冬至牛辗塘,谷米无处藏。”这是以太阳(晴、暖)预兆各个农时环节和一年的好收成。“雷响惊蛰前,七七四十九日不见天”;“三日正东闪(电),大水没屋檐”;“虹高日头低,大水没道地”,等等,这是阴雨可能会给稻作带来灾害的警示性农谚,提醒农民及早防备。
当然,旱象并非对稻作一点也不构成威胁,连续数月的亢旱也会造成严重减产,但这样的大旱在河姆渡一带概率极小,只是百年或数十年一遇,而水之为害,却十年九涝,甚至有一年数涝的,既频繁又惨烈。一则是雨水充沛,二则地势低洼,地下水位几与地面持平,短时期的干旱,不但不会导致水稻减产,反因阳光充足,积温高,促使稻谷生长良好,结实饱满,获得意想不到的丰收。“十涝十歉,十旱九丰”,确是河姆渡一带稻作生产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以推知,河姆渡氏族崇拜和祈求太阳神,乃源于稻作文化;在这多雨易涝的环境中,为了稻谷丰收,祈求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当是为了祈晴,而不是相反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在河姆渡文化时代,作为行云布雨的主要神灵——龙的具象已经在华夏大地出现。在江南稻作区,良渚文化也已有玉雕龙纹出现。按照一般的理解,神灵是有分工却又各司其职的,原始人当不会舍弃雨神——龙而去向太阳求雨。但南方稻作区龙的具象出现比北方和中原地区为晚,这可能与南方多雨常涝,北方少雨易旱这一总的地理气象因素有关。
人类在造神过程中,总是将自己的需求与塑造的神灵(或超自然力现象)相对应,很少有相反的情况出现。如秧有秧神,仓有仓神,田里神则有田公田婆,乃至饭镀神,米缸神,碗神等。这里有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整个龙属中,余姚地方有一条独特的“犴龙”,民间也叫“露龙”。在余姚有的地方,在干旱严重的时候,白天烈日当空,万里无云,夜晚也满天星斗,但到了第二天清晨,田土却一派湿润,稻叶上缀满了晶莹的水珠,像刚下过一阵细雨一般。这原是一种气候与地理的综合现象,因这一带地下水位极高,土质粘腻,白天烈日虽将田土的表层烤干,一到夜晚,地下水通过泥土的毛细孔又慢慢地向上渗透散发,形成雾露(农民称这类土地为“夜潮地遇上亢旱,稻谷也不至全部枯死,若适逢甘霖,则稻禾大发,大获丰收。但是农民们觉得不可理解,以为一定有一条在夜间能化雾下露的神龙在暗中侑护,于是神造出一条狞(露)龙来。犴龙以竹蔑为骨架,周身用布套裹,形状似龙非龙:其头似狗,亦略似狐,喙分上下两颌,中间露舌,下颌有红色短须,上颌有鼻,左右双眼,眼圈生黑毛,眼球呈黑球状,头生两角两耳。头部红色,身黄色。身段似龙状,但无鳞,背脊上有华须分披两边,尾分上下两叉,首、尾共七节,全长约15米。祭龙时作龙舞,有犴珠引导,另有黄、蓝、白、红三角旗各一,分别添上“金、木、水、火、土”字样,代表五行,列阵成梅花状。基本舞蹈动作有“吃珠、转身、三跳、进阵、串旗、甩尾、收场”等阵法,并伴以大锣大鼓及招军等器乐演奏,旧时还点燃香烛,舞蹈动作粗犷野性,气氛庄重神秘。由此也可窥见人造神灵与自然对应之一斑。犴龙盛行于有余姚粮仓之称的马渚一带。日本国也有类似的汗龙舞,据说正是从中国浙江一带传过去的。(www.zuozong.com)
祭日求晴,祭龙祈雨,这是稻作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
推断“双鸟舁日”是河姆渡氏族祭日的神器,仅仅根据这件象牙圆雕本身尚显得依据不足,但下述两方面的发现为这类活动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佐证。一是乐器的发现。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骨笛160余支,陶埙数件,木笛20余枚。音乐(乐器)起源于劳动和生活,发展于娱乐,而其完臻则有赖于宗教祭神活动。一般地说,进行祭神祈祷活动是离不开乐器的伴奏的,“鼓之舞之以尽神”(《易·上传》),将人的愿望和企求,通过供奉神灵的具象和一定的仪式去感应真正的神灵,在这类仪式中音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乐能通神”。
另一重要发现是,河姆渡遗址的墓葬中已有随葬品,证明当时已有了灵魂观念,而人的灵魂观念是形成各类神灵的内在机制,神灵是人的灵魂观念的外延。在初始,他们往往将祭神与祭祖混在一起,只是到后来才逐渐分开。祭坛的出现更能证明这类祭神活动在当时已形成为神圣的制度。祭台在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中虽尚未发现,但在最近,在距河姆渡遗址不到2公里的东面,发现了一处叫鲞架山的遗址,其年代经测定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的第二、第三文化期。从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该遗物的居民当为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氏族的后裔分支。鲞架山遗址在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处人工填筑的红烧土台遗迹,直径达340厘米,红烧土最厚处达75厘米。这是一处供祭祀用的祭台。祭台周围按一定间距布设着四组刻花陶器,每组5件,可以推定这是原始人供奉祭品的器具。由此推测,紧傍河姆渡遗址的东南面小山岗,原来有10余米高度,应是一处天然的祭坛,极有可能是河姆渡先民举行祭日活动的场所。此外,相邻的奉化市茗山后遗址也发现经过夯土的祭坛。茗山后遗址距今5000〜6000年,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第三层的年代,该遗址一般被认为是河姆渡氏族的支裔。
去河姆渡遗址西北约百公里的良渚文化,更发现了大瑶山和反山两处大型祭坛和墓葬。最近,余姚梁辉镇老虎山上也发现了商周至魏晋的墓葬群。这些祭坛和墓葬群,都建筑在高出四周的向阳山岗上,极可能与祭日活动有关。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祭日活动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礼记・效特牲》:“郊之祭,迎长日之到这是关于古代帝王冬至日祭日的记载。在古代,祭日和祭天是同一回事,“天秉阳,日者众阳之宗”(《礼记集说》)《礼记,郊特牲》详细记载了周王祭日活动的盛况。
冬至这一天清晨,周王戴冕旒,穿衮服,率领着衣冠楚楚的群臣,通过铺垫了新土的道路,在象征日月等旗帜的引导下,浩浩荡荡地来到南郊祭日(天)。祭坛上供奉着周身皮毛赤色的珍贵的全牛(特牲)。郊内六乡之民,几乎在半夜里就起来了,家家在田头设烛照明,将道路和四周照得一片通亮,以恭迎周王一行的车驾。在国内,这一天不论死了什么人,不发丧,不穿凶服,也不敢哭泣,以免冲撞了神圣的祭日活动。这些均达到了“弗命而民能听上”的程度,也就是说老百姓习以为常,习惯而成自然,没有上面的命令,也都能自觉做到。可见祭日活动影响之深远。明清时兴春分祭日,仪式也相当隆重。建于明嘉靖九年的北京朝阳门外的日坛,每逢春分日,皇帝就遣专官祭日。到了清代,每逢甲、丙、戊、庚、壬年的是日,皇帝亲往祭日。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祭日者身份的变换,后来祭日的涵义完全离开了史前原始氏族祭日之原始蕴涵。
但在民间,祭日活动仍沿着古老的传统和习俗传承下来,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均要进行一些传统的祭日活动。遇上“天狗吞日”(日食),人们更是自动焚香点烛,击鼓鸣金,燃放爆竹,祈祷念咒,以拯救受难的日神。
本文至此可以作出如下归纳:一、河姆渡遗址双鸟与太阳象牙圆雕正确的命名应是“双鸟舁日“,也即是太阳神的具象二、河姆渡文化时代已有祭日活动,祭日是为了祈求它赐予保障稻谷丰收的好天气,因而可以说是稻作文化的产物。
这里想附带说一下龙。与对太阳的需求相反,雨水是原始人对另一自然现象的需要。于是龙这行云施雨的庞然大物也被塑造出来了。龙其实也是农业文明,尤其是稻作文化的产物,因为水稻无水不活,缺水不长,而水太多了也会被淹死。但龙不同于太阳有具象可供描摹,而风云雷电变幻无常,无固定的具象。龙的最初的成象,可能出于原始人对一种自然景观“挂龙”现象的观察。
这是一种极其壮观而又神奇的现象。笔者曾亲眼目睹过它的发生。那是60年代的一个夏天的下午,笔者在余姚市一个乡里工作,那天天气湿热难当,黑云低垂,大白天得开着电灯才能看清文件。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阵阵喧哗。
有人喊:“挂龙啦!
挂龙啦!”我出去一看,好几十人一齐仰望东北方向的天空。我顺着望去,只见在一片墨云和灰色云层的交界处,垂下一个黑乎乎的圆柱状东西,那东西上大下小,看上去也只有一丈来长,但它以极快的速度向下延伸,宛如从云中挂下来的一条巨蟒,最后终于将“龙尾”探到了海上,约摸又过了两三分钟,忽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那条巨蟒似的“龙”也隐没在晦暗如磐的风雨中。我虽然不信神龙之说,但对此还是震撼不已。这种“挂龙”现象在沿海一带常有发生,自然会引起原始人的种种联想,幻化出龙的具象来。1987年,河南省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约6000年)45号墓穴出土的蚌壳盘嵌的一虎一龙,是我国发现的龙的最早具象,它已跟北京故宫中明清时代龙的形象近似。到了距今约5000年的浙江良渚文化,已有雕塑精致的玉龙纹出现,证明龙在我国有广泛的地域影响。就龙的整体而言,即使在远古的大自然中也是没有这种生物的。但就局部而言,它的所有肢体在今天的自然界的生物中依然有迹可寻:马首;鹿角;虾(蟹)睛;驴嘴;羊髯;蟒身;鱼鳞;鹰爪;鲸尾。它的主体“蟒身”,就是“挂龙”现象的移用,再加上其他动物局部肢体的拼凑,才成为“能幽能明,能细能巨,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形貌奇特的神物,于是有了制龙、雕龙、凿龙、求龙、舞龙、祭龙等种种活动,无非是想讨得龙的欢喜,希冀它赐予人类风调雨顺,从而达到五谷丰登。这些在今人看来是没有争论的。那末,河姆渡人制作这件《双鸟舁日图》的牙雕,是否也有后人创作龙那样的动因及用途?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太阳由两只神鸟舁着飞上苍穹,这恐怕在河姆渡文化时代以前的原始人中已经口碑相传了。当人类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尤其是人工栽培稻谷的发明,太阳的活动对人类可谓利害攸关。如播种时的阴雨会使谷芽冻烂;扬花期的阴雨会使稻谷成为枇子;收获时的阴雨又会招致谷粒抽芽变质。他们可能认为,长期的阴雨是由于神鸟遇到了某种麻烦,不能行使使命,或者是一觉睡过了头,忘了每天例行的公事,必须运用某种仪式使它们能听到人类的讯息。于是挑选了最好的材料,推选出氏族中最优秀的画家,制作出这块《双鸟舁日图》,并供奉起来,举行祈祷活动,并伴以骨笛、木筩、陶埙等的吹打,用以感应神鸟和太阳,重新出现于他们的头顶。牙雕蝶形器上的双鸟舁日,就是太阳神的图腾。
关于“太阳神·双鸟舁日”的讨论已相当深入,但因为这件象牙圆雕是迄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太阳神像,而其艺术造型又是如此独特,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因而引起了众多学者专家的关注,以各种不同的视角,作出了种种推论,这里择要录之,并加以简短的评析。
一是肯定双鸟太阳纹象牙圆雕是原始人的太阳崇拜物,由此推而广之,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批器物上的圆圈纹,皆属太阳崇拜的产物。如一件标本T17④:37的木质蝶形器(又称鸟形器),蝶翼左右两侧上角各有一圆形浅凹窝,凹窝外圆糅有一圈深黑色的漆,被认为圆形凹窝和凹窝外的宽边黑圈共同表现为太阳形象,是对太阳的崇拜。
另一种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上的所谓太阳纹应为“涡纹”(也即圆圈),是“沼泽环境中水涡的形象描摹,都形象地表现了遗址周围的沼泽环境,它们并不是对太阳的摹写,甚至连河姆渡的鸟纹恐怕也与太阳无关,它是河姆渡人通过观察鸟类,而对双体繁殖的感悟”。因而属于“湖沼崇拜”。[2]
此外,有的似乎观察得更仔细,观察出那件“双鸟舁日”牙雕中的双鸟是左鸟高于右鸟,因而左边一只应是雄性,右边一只属雌性。还有人更进一步,认为太阳纹的五道同心圆的中间那点“刻点”,是原始人通过观察太阳黑子活动记录下来的“太阳黑子”。等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关于“太阳纹”和“涡纹”之争。对于由数道圆圈组成的图像,一个认为是太阳纹,象征着原始人对太阳的崇拜;一个则截然相反,认为是水中的涡纹,是住在沼泽地区的河姆渡人对湖沼的崇拜。关于同一图像,为什么会产生“水”、“火”(我们姑且将太阳称之为火)不相容的对立的观点,这大概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能解释得通的。那么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呢?
首先,大概是对原始人所画(刻)的圆圈的真正内涵没有搞清楚。河姆渡人在器物上画(刻)的圆圈,没有人怀疑是他们从观察大自然中得来的,如天上的太阳、满月,水中的涡纹,树上的果子……这是人类从三维空间观察来的众多的圆状自然物转移到平面上的一种抽象,也可以说是表示一切圆状物的符号,但又并不表示某个具体的事物。圆圈的全部涵义就是一个圆圈。只有当它与某种事物发生联系的时候,才会产生具体的形象,如挂在天空的是太阳或满月,生在树上的是果子,镂刻在木鱼、陶鱼身上的是鱼鳞或鱼眼……此外,河姆渡人也把多道圆圈刻画在其他动物身上,这有两种情况,一是为动物身上原本有的形象,如前面提到的标本T17④:37蝶形器,其两翼上角之凹窝及凹窝外的宽边黑漆圆纹,应是蝴蝶原有的花纹。这样的蝴蝶在今浙东四明山一带仍到偶尔可见。二是动物身上原无此类圆纹,为原始艺术家们加上去的装饰纹,如标本T243④:71陶林上野猪腹部的圆纹,标本T234④:235陶兽臀部的多道圆纹,都是为了达到审美效果而对圆纹的一种艺术运用,并非什么湖沼(涡纹)崇拜或太阳崇拜。河姆渡的艺术家们对圆纹和由圆纹变演出来其他诸如弦纹、旋纹等,在艺术上运用已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为各种器物增添了美感和愉悦感。
由此可以看出,河姆渡遗址的圆纹,是对自然物的一种抽象,本身只是一种符号,只有当它与某种事物联系起来时,才会产生具体的形象或达到审美效果。
其次,将圆纹不作区别地视作某种崇拜,乃是过于迷恋于要所谓探寻原始人的“深层意蕴”,以为原始人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深藏着某种神秘的“密码”,于是作出种种推断。有的纯粹是为了获取某种轰动效应。结果将一大批只具审美功能的原始艺术品解释得面目全非。以那件标本T17④:37为代表的一批骨质、石质、木质蝶形器为例,《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统称为“蝶形器”,这是第一次直观得到的印象,较为真切地描摩出器物本身的形象,但后来大概出于“鸟崇拜”的呼声甚高,也随之改为“鸟形器”,这样的改动其实是不足取的。
人类创作第一件原始艺术的内在动因是什么,是愉悦激发的冲动,还是崇拜引起的行为,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得出结论,即在迄今发现的史前时期众多的原始艺术作品中,占有很大一部分当属于审美功能的艺术,只有较少一部分才属于信仰崇拜的神巫艺术。原始人创作艺术品的动因十分复杂,有的纯粹出于愉悦和好玩,如我们在《雕塑艺术的滥觞》中提到的那些小陶杯、小陶釜等,应是人类好玩天性的产物,制作时并不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有的则已具有较明确的审美观点,如河姆渡遗址第四、第三层出土的陶釜口沿上多达70余种的纹饰,显然是为了美观而有意识地刻画上去的,但其初始可能是为了手捧釜沿时起到防滑作用,后来见其有审美功能,才作为装饰艺术刻意创作,变幻出无数花样,成为陶釜上一项专门装饰艺术。再一种才是有深层意蕴的神巫艺术品,如“双鸟舁日”象牙圆雕。正确分析原始人艺术创作的动因,有助于较为科学地区分原始艺术品的审美与崇拜属性。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双鸟舁日”图中两鸟的雌雄问题。这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因为一,无法推测原始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否有雌雄之分;二是即使有雌雄之分,今人又如何分辨?这使人想起《木兰诗》中著名的诗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两鸟比翼飞,又有谁能辨其是雄雌呢。
至于太阳纹的中心圆点是否是原始人观察到的太阳黑子爆炸所记录的“太阳黑子”,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它超越了人类对天文科学的认识水平。根据史籍记载,我国在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对于太阳黑子爆炸的记载,是世界公认的最早记载。
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又怎么能知道太阳黑子活动的情况呢,退一步讲,即使他们观察到过太阳黑子爆炸的现象,但太阳黑子爆炸所产生的黑子在多数情况下是“成群”出现的,旦往往发展形成为两个具有相反磁极的大黑子,大黑子周围还有许多小黑子,单个黑子存在的概率极低,而且从地球上观察到的太阳黑子,也并不一定处于太阳中心位置。“太阳黑子”云云,显然高估了原始人对天文的认识水平。那末,太阳纹的中心圆点究竟为何物?笔者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太阳之核。不过这并非是指现代人所认知的原子核之核,在原始人的感知中,其意义相当于果核之核,他们从果子结构推测太阳也会有一个凝聚着巨大热力的“核”,这从原始人围坐于篝火四周时感受到篝火一波一波向外辐射的热力,认为太阳也是像篝火一样的炽烈火球,第五道外圆上方熊熊的光焰便是最好的佐证。太阳的热就是从那个中心圆点辐射出来的。这样的推测并非杜撰,我的论文《七千年前的太阳神・河姆渡“双鸟舁日”探幽》在《文汇报》发表并经《新华文摘》转载后,有个收藏家给我寄来了一幅古瓷盘上的描摩图像:一边是一只象征月亮的蟾蛛;一边是一个太阳图像,其形象中间也是一个圆点,由圆点引出一道弧线,弧线成晃动状,顺时针方向从内到外连绵向外成圆状辐射延伸。似可为“双鸟舁日”太阳纹的中心圆点做一注脚。另一可能是,这个中心圆点并无什么特别的涵义,它只是那位原始艺术大师作画时所取的中心点,使从内到外的五道圆纹成为同心圆,从直观上更具太阳形象。
其实,对任何一件原始艺术品的品评均不能离开其整体形象,我们这样的讨论已经有一点钻牛角尖的味道。诚然,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对社会科学的探索,是需要一点钻牛角尖的精神的,因为有些看似“牛角尖”的事物有着暗藏的通道,锲而不舍地钻下去,有可能曲径通幽,豁然开朗。孙悟空如果没有勇气穿过那道飞泻的瀑布,就不可能发现里面别有洞天,也就没有了能与花果山相映成趣的水帘洞。但是钻牛角尖的方法却是不可取的,它容易导致偏离事物的客观性。当然这已是题外之义了。
关于这件象牙圆雕上的双鸟和太阳纹图像,大概是由于视角和思维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五花八门。如有的对于从中心圆点向外辐射出去的五个同心圆,认为是双鸟在水中交感激起的“涡纹”;外圆上方熊熊的光焰,则是双鸟的“尾翼”。有的认为双鸟中间的五个同心圆不是太阳而是一个“鸟蛋”,因此这件象牙圆雕也可称之为“双鸟朝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只要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你如果能从整体形象观察并且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得到的第一直观印象只能是双鸟和太阳。我曾将此件的照片叫两个上幼儿园大、中班的幼儿辨认过,其中一个明确无误的回答:“两边是两只鸟,中间是一个太阳。”另一个则回答中间那个是“火球”其实,幼儿园里年龄段相似的五六岁幼儿,在看过照片之后,大都能作出同样明确的回答。因此,对于这件双鸟太阳纹象牙圆雕,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讨论还是在“双鸟朝阳”与“双鸟舁日”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神·双鸟舁日”的论点已广泛深入人心,并日益为学界所认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