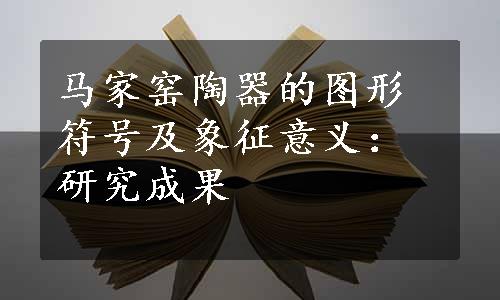
(一)马家窑图形符号概况
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彩陶文化在青海、甘肃、宁夏地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家窑彩陶文化分布在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北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甘肃中南部地区。分布区内有着以黄河为主流,黄河的支流湟水河、洮河、大夏河等在内的众多河流。马家窑文化受仰韶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有着非常明显的传承关系,因为这种文化制陶业继承了仰韶文化以及庙底沟类型简明爽朗的艺术特点,而又比仰韶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手法比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彩陶图形更为精细,形成了非常典雅、绚丽的艺术风格,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彩陶图形艺术成就达到了早期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马家窑陶器的图形大多是用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通常呈橙黄色,器物表面被打磨得非常细腻光滑。在许多马家窑文化的遗存中,除了大量精美的彩陶之外,还发现了遗留的陶窑、窑场、颜料、研磨颜料的石板以及调色陶碟等。马家窑彩陶早期的彩绘花纹一般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发展到中期的时候加入了红色,形成了黑、红两彩相间的绘制花纹;而在马家窑彩陶晚期,黑、红二彩均等的使用,形成了更加丰富的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制陶工艺技术大大提升,轮修坯技艺已被大量使用,利用转轮绘制出平行线、同心圆纹、弦纹等装饰纹样,表现出非常娴熟的绘画技巧。而这一时期彩陶的大量生产,则说明了制陶过程中出现了专门的绘制工艺,制陶的社会分工已经开始走向专业化,这种特点标志着原始社会逐步走向解体和中国文明曙光的来临。
(二)马家窑彩陶图形符号的渊源及其特点
马家窑文物彩陶上的图形纹样,是装饰图形符号继承仰韶文化基础上的发展。马家窑彩陶艺术最大的特点是纹样比较优美,布局非常完整,色彩鲜明,结构丰富,手法多样,技巧精湛,形式感比较强,因此著称于世。比如,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手拉手舞蹈纹盆,这些陶器虽然风格迥异,但纹饰相同,也有彩陶瓮和双人抬物盆等。双人抬物盆的内壁上绘有四组双人抬物图案,图案中用圆形表示人的头部,用细线描绘出人的四肢,而粗线则是按照起伏描绘表现人的躯干,图形用非常简洁和传神的几笔就把两人抬物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这幅图的内容表现出远古人类的生活活动,有人认为这反映了祭祀时的场景,也有人认为这是真实劳动生产场面的反映。有的学者指出,这个图案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舞人纹有着密切联系,表现出当时人类社会中已经有了舞蹈和音乐这两种艺术。因此可以推断,横亘中亚草原的文化交流通道也许比已知的更早,而并不是从西汉的“丝绸之路”才开通的。
西部陶器图形符号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关于他们象征的具体寓意,可能是工匠或原始画家们的签名或记数、氏族徽号、萌芽的汉字、部落图腾(孟伟哉《彩陶符号,萌芽的汉字》),抑或是与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的文字有关,个别符号甚至被认为源自“原始本的巫书”。学者们普遍认同这些彩陶符号具有一定的记事功能,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彩陶符号形象与甲骨文或铭文中的部分文字完全相同,从而初步推断青海彩陶符号很可能是一种古老文字的雏形。《甲骨文字典》《简明金文词典》从字形上与彩陶符号做对比,意在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者们对青海彩陶符号的关注与重视。
同一符号有时被认定为不同的文字,或者不同的符号被认定为同一个字,可能是一字多义等缘故,青海彩陶符号同样也存在这种情况。青海柳湾彩陶符号里不能判断或暂无资料对照的符号还有60多个,约占柳湾139个彩陶符号的43%,由此可见,陶器图形符号的认定仍然存在诸多疑问。
青海彩陶符号都是以单独纹饰形式出现,无法组成完整的句式。李智信先生认为:“彩陶图案和彩陶符号都是文字的来源之一,图案的简略形式具有文字的功能。”青海彩陶上的符号图形有几百种,这些符号均可能表达着不同的文化内容,是否已经具备了较高的记事功能仍不确定。所谓记事功能正是文字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青海彩陶符号可能正是沿着从图案到符号再到文字演变过程发展而来,因此对这些符号的深入探究对我们了解制陶时期人们的生活文化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知道,一种文字的起源是多元的,青海彩陶上的部分符号图形与甲骨文中部分文字结构相一致,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传承的关系呢?从时间上推测,青海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距今约4000多年的历史,比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要早400多年,据此是否可以推断,彩陶符号应该也是古老文字的一种,至少它对某种文字的产生和传承有着很大影响。
在青海彩陶符号中,出现了极似生产工具的图形,以此推测当时的青藏高原农业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同时兼营渔猎业的生产。从青海柳湾墓地出土的农作物“粟”和青海民和啦家遗址出土的天下第一碗“面”,都可以为青海彩陶符号上的生产工具图形作注脚。在原始氏族公社阶段,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在青海柳湾墓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的原始居民已经开始使用各种不同形式的简单符号,代表一定的客观事物。这些图形符号极少数画在器物的底部,大多数图形是被画在陶壶的腹下部,还有极个别图形被画在器物的颈部。这些符号都是在陶器未入窑前用毛笔之类工具画上去的,简单而规整。
1.马家窑彩陶及其图形符号统计
马家窑彩陶中,目前出土的有符号的陶器总共有679件,大多数是出土于226座墓葬中。这些墓葬除了少数分布在南方以外,大多数都在墓地中区的北部。各墓出土画有符号的陶器数量非常庞大,其中出土1件陶器的墓葬有88座,出土2件的有54座,3件的有24座,4件的有25座,5件的有22座,6件的有3座,7件的有4座,8件的有3座,9件的有5座,10件的有3座,12件的有1座,14件的有2座,15件的有1座。可见,各墓出土画有符号的陶器以1至2件者为多数,10件以上者为少数。(www.zuozong.com)
在679件画有符号的陶器中,符号图形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几何形符号,二是动物形符号。几何形符号共674件,动物形符号共5件。在几何形符号中,剔去重复符号,共有139种不同的符号图形,它们皆由点、横、竖、斜等笔触组成。动物形符号图形有犬、鸟、牛、羊、虫等五种,绝大多数是一件器物上画一种符号,画两种符号的器物仅是个别的。若从符号图形繁简上看,在几何形符号中,笔画简单的数量最多。如“十”字形符号出现的频率最高,达116件之多;笔画繁复的只有虫形符号等数件。具体如下。
几何形符号,共674件,其中,圆点形符号共13件。圆点形符号又有单一圆点形、圆点上接一斜粗线、圆点下接人字形线、双点间加一弧线、圆点上接六条竖短线等五种;横线符号共67件,可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五线、八线与多线等七种,其中横短线相接符号共7件,横、竖相接符号共29件,横、斜线相接符号共4件,横、弧线相接符号共7件,横线与曲线相接符号共2件,竖线形符号共35件,竖线与人字形相接符号共5件,曲线符号共14件,折线符号共22件,人字形符号共27件,十字形符号共116件,斜叉十字符号共52件,三角形符号共14件,五字形符号共10件,大字形符号1件,丰字形符号1件,“卐”字形符号共26件,巾字形符号共2件,中字形符号共2件,井字形符号共7件,工字形符号1件,方格形符号共16件,綯( )形符号共30件,雷纹符号共2件,箭形符号共11件,半圆形符号共17件,圆形符号共95件,方形符号共34件,椭圆形符号共2件,镰刀形符号共1件,异形符号共2件;动物形符号共5件,其中犬形1件,鸟形1件,牛首形1件,羊形1件,虫形1件。由此可见,在彩陶图形符号中,集合图形符号占了大多数。
)形符号共30件,雷纹符号共2件,箭形符号共11件,半圆形符号共17件,圆形符号共95件,方形符号共34件,椭圆形符号共2件,镰刀形符号共1件,异形符号共2件;动物形符号共5件,其中犬形1件,鸟形1件,牛首形1件,羊形1件,虫形1件。由此可见,在彩陶图形符号中,集合图形符号占了大多数。
2.马家窑彩陶图形符号种类
马家窑文化中的螺旋纹彩陶壶的特点是鼓腹双耳,通高侈口,颈部斜十字纹(即大网格纹),陶壶肩腹部饰竖向的“S”形螺旋纹,两个相连的螺旋纹之间又饰有小旋纹。马厂类型陶器上出现最多的是网纹,图形绘制线条细如毫发,横竖交错,严谨规整,一丝不乱,充分凸显了图形纹饰的精湛技巧。其次是螺旋纹演变成的圈纹,折线纹,锯齿纹,鱼纹等。此外还有三角纹、网格纹、人字纹、水波纹和回纹、涡纹等,这种图形纹饰符号简单质朴,将当时人的审美和对美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几种特殊图形,比如“卍”字纹,这种符号从诞生之初在陶器上的运用到科技文化发达的今天,在宗教、组织、符号装饰方面经久不衰;圆圈纹,是由三个到四个不等的大圆圈组成,我国古人讲究天圆地方,因此认为圆环状如同天空,而几个套嵌的原型符号比单个圆形更具动感,这样的组合象征无始无终的永存,因而在古今中外,圆形均是宇宙、上天和最高神权的象征。回纹装饰图案,除了在陶器纹饰上的应用意外,早在中国周代,祭祀用的青铜器上就已经频繁出现,直至现在。由于回纹是由商代的象形文字演变而来,象征着滚雷和浮云,因此又称“云纹”和“雷纹”,寄托了先民对生命之雨的期盼。中国人自古用连续不断的回形纹象征长寿,一般多出现于老人的衣物上,寄托晚辈对长辈健康长寿的美好祝福。后来回形纹传入西方,演变成希腊式回纹,与其他复杂的图形符号交织在一起,成为欧洲古典建筑的主要装饰图形。
在陶器的纹饰中,比较常见的还有篮纹。这种纹饰最初是用芦条、柳条等编成的编织品组成的各种有规律的几何形纹样。笔者认为,这种篮纹一方面象征着食物丰产,又提示绘有这种纹饰的器皿是用来盛放食物的,盛满果蔬食物的器皿象征着丰产,有时它们被置于神的头顶上。此外,水波纹和涡纹也是彩陶纹饰中常见的纹饰符号。彩陶器物上涡纹和水波纹的组合,结构巧妙,流畅生动,彩绘的涡卷、勾连的弧线形成一种生生不息的态势,富有强烈的动感。涡纹、水波纹是古代陶工们对母亲河黄河的崇尚和敬畏之情的象征,也是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礼赞。在有的涡纹、水波纹图案中还加上了一些小圆圈,即在平行的波线中,等距离地点上几颗小圆点,如同旋涡中溅起的水珠,富有流畅的艺术美。这些图案体现出的审美尺度和审美情趣不同于中原半坡类型的静态四等分的画面。这类纹饰符号装饰的陶器出现在中国远古时期的彩陶之上,还出现在欧洲和非洲的几个文明中的器皿上,并一度成为西方文化中克里特风格陶器上的主要装饰符号。
仰韶文化晚期步入衰落时期的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是对马家窑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并处于承上启下阶段的文化存在。石岭下类型生产的彩绘陶器占本时期陶器的25%左右。这时期的彩陶均为橙黄色泥质陶,器表打磨光滑。彩绘图案都施在器物外表,大部分纹样绘在器物的颈部与上腹部,但已经出现器物通体绘彩和少量器物内部绘彩的迹象。颜色以黑彩为主,兼施少部分红彩。纹样以直线、弧线、圆点、圆圈、网格纹等单个符号通过各种方式相组合而成的整体图案为主,动物纹饰中又以抽象鸟纹和鱼纹为代表。在此时期彩陶中出现的鱼纹,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人面蛇身的形象,其实代表着伏羲;也有人认为这种纹样是远古时期龙族图腾的雏形。鸟纹在庙底沟时期相对比较写实,发展到石岭下时期时则变得抽象,一般是运用圆点、圆圈、弧线三角等几何图形组合构成鸟的形状,这种形状非常抽象,难以读懂。石岭下类型彩绘图案为以后各时期的彩陶构图开辟了广阔路径,拉开了马家窑文化各个时期彩绘陶器的序幕,奏响了甘、青地区彩陶绘画艺术的篇章。
马家窑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中辉煌的一页,它是在中原地区彩绘陶器逐渐走向衰落时,在黄河上游产生的科技发达的史前文明。手工制陶业在这个时期已经十分发达,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熟练地用细泥红陶制作彩陶,有的彩陶还用少量的泥质灰陶和夹砂制成。器型主要有壶、瓶、缽、盆、罐、碗,这些陶制品器表打磨得十分光滑,制作非常精细,彩绘纹饰大多是弧线纹和旋纹。除圆圈纹、旋涡纹、圆点纹、水波纹、弧边三角纹之外,还出现了一些较为抽象的动物纹样,比如鱼、蛙、鸟、鼋等。“鼋”亦称鼋鱼,俗名鳖,系爬行纲、鳖科。其吻小眼大,背甲近圆形,正面暗绿色,腹部、前肢外缘及蹼均呈白色。生活在气候炎热的南方淡水河中,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国语·周语下》中有载:“我姬氏出自天鼋。”联系我国古代相关典籍,鼋与周朝的起源有着非常大的渊源,鼋与整个周王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代周朝的青铜器上,象征一个家族的族徽就是天鼋的形象,这种天鼋形象与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中的天鼋形象非常相似。而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中的“鼋”与周族青铜器上的“天鼋”形象之间是否一脉相承,仍然有待考古人员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出现了一批以舞蹈纹彩陶盆和二人抬物彩陶盆上的人物写生为代表的人格化纹样。这一时期,在器皿的内部绘彩以及“满彩”,多以平行线纹、旋纹布满器壁,在器壁上比较常见的还有圆点纹、圆圈纹、“十”字纹和“S”字纹。这些纹样大多以黑白两色为主,有的是纯黑单色,有的是黑白相间,扣人心弦的黑、白兼施双彩图案以及撩动人心的浓黑如漆单彩图案,让马家窑彩陶熠熠生辉。这些纹饰独特精美的彩陶在远离马家窑文化的当代社会,依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图形符号文化是一个地区和国家历史的缩影,也是时代文明的一面镜子。马家窑文化时期的文明高度发展,而这一时期的图形符号则是新石器时期华夏文明晨曦中非常绚丽的霞光,也折射出我国远古先民在生产和发展中产生的非凡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仅表现在文化、审美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从侧面折射出当时科技、生产技术以及生活方式所达到的高度,为我们当代人追根溯源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马家窑文化时期彩陶上不同的非语言符号充分体现了远古时期众多非常神秘的社会、文化信息等,也创造了在中国画历史上发现最早的艺术形式。马家窑文化彩陶图形符号最主要的特点,是以毛笔为主要的绘制工具、以黑色(同于墨)作为主要基调、以线条作为造型手段,纹饰图形符号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承载着远古时期人们的精神向往和艺术追求,也在某些方面体现出图腾崇拜等对非自然力量的敬畏,为中国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画都以线描为主要手法进行创作。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彩陶图形符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根基之一,是中国画绘画的根源。以民族文物为载体的图形符号文化将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图形符号中创造出的众多形式多样的形状,让后期中国画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了可能,而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图形符号,就是神奇丰富的史前“中国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