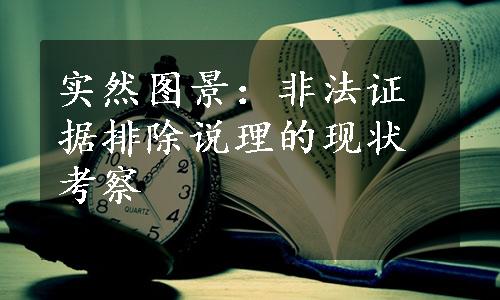
为全面了解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情况,笔者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刑事判决书”“非法证据排除”等关键词,并将时间范围限定为“2014 年1 月1 日至2018 年1 月1 日”,共查询到2468 个裁判文书。经梳理,显性特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涉主体和程序上来看,基层法院、一审程序案例众多。这与各审级法院不同职责定位有关,也指明了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说理规范化的关键在基层法院和一审程序(见图1、图2)。
图1 涉主体分布
图2 涉程序分布
(2)从区域分布来看,各地分布不平衡。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遍布大陆各个省份,但以四川、云南、广东、湖南、江苏五个省份居多,占比接近40%(见表1)。
表1 涉地域分布
(3)涉嫌罪名广泛。除贪贿罪外,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乃至非暴力犯罪中,或多或少涉及非法证据。其中,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和侵犯财产罪占比最多,分别为34%和31%(见图3)。
图3 涉案由分布
(4)从相关案例年度数量来看,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总体呈上升趋势,2016 年、2017 年较之前两年增幅高达73%,反映了被告人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见图4)。
图4 涉年份数量变化
(二)实证维度二:典型案例的深度解读
继对涉非法证据排除文书的全景扫描后,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希冀一步步接近问题本质。
1.程序视野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与审查
(1)举证责任分配的“错位”。
【案例一】谢亚龙受贿案
谢亚龙当庭翻供,指控受到刑讯逼供并叙述了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人员,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法庭要求其提供相应证据,谢亚龙称无其他被审讯人在场,无法提供证据。法院认为,公诉机关庭前已经调查能当庭举证。谢亚龙虽以刑讯逼供为由推翻大部分有罪供述,但无法举示证据及理由,故不予采纳其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回应: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并提供线索后,法院应启动调查程序审查所涉证据的合法性,但本案却将非法证据的举证义务分配给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举证责任错配的表现。
(2)被告人程序救济的“缺位”。
【案例二】张百章受贿案
张百章上诉认为侦查机关取证违法,其是在受误导、欺骗以及刑讯逼供情况下作出了供认,同时认为公诉机关既未当庭出示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也未能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程序违法行为。浙江高院审查后认为,根据审讯笔录及案发经过说明上诉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证人是否需出庭作证、同步录像是否当庭播放均视案情而定。[71]
回应:被告人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法院不予查实,仅依审讯笔录和案发经过的一纸说明判定不存在非法证据,是侦查中心主义和卷宗中心主义的体现。
(3)法官中立立场的“越位”。(www.zuozong.com)
【案例三】严厚全受贿案
一审中,辩护人指出控方对严厚全的供词收集程序违法,属于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72]舟山中院审理认为控方播放的部分讯问录像显示其严格遵守传唤时间时限,没有刑讯逼供、诱供等情况,严厚全供述的获取依法、真实。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同步审讯录像,检察机关并未实施刑讯逼供、疲劳审讯,严厚全有罪供述均系在适当休息后自愿作出。
回应:二审裁定书简单重复一审的理由,一审说理不能说服被告人,同样的文字表达非但无法获得信服的力量,法院的中立角色遭受质疑。
2.裁判文书说理视角下的涉非法证据排除说理
(1)不予认定的“斩钉截铁”。
【案例四】张忠元受贿案
对于张忠元及其辩护人提出侦查程序违法,张忠元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极不稳定,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上诉、辩护意见。法院认为,侦查机关对张忠元讯问程序合法,无证据或线索表明其受到或有可能受到刑讯逼供,故张忠元及其辩护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73]
追问:讯问程序如何合法?是否所有证据或线索均表明张某未受到刑讯逼供?法官尚不能说服自己,又如何说服申请人和社会大众?
(2)不予排除的“欲言又止”。
朱海洋上诉提出其系在被刑讯逼供后作出有罪供述,应予排除。二审法院认为,朱海洋体检表证实入所时无外伤,侦查机关讯问在看守所进行,并录有同步录像,且一审庭审时对辩护人提出的排非申请召开了庭前会议,综合在案证据难以证实朱海洋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在刑讯逼供后所为。[74]
追问:讯问有同步录像、一审召开庭前会议就能证实侦查机关不存在刑讯逼供?证据合法性心证历程应形成于同步录像的完整性、庭前会议的实质运行中,而非形式上的有无,“难以证实”显示法官否认非法证据时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说理不得不欲言又止。
(3)排除说理的“浅尝辄止”。
【案例六】韦志刚等故意杀人案
韦志刚认为有罪供述是在受公诉机关刑讯逼供情况下作出的,应予以排除。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提供了同步录音录像、韦志刚的入所体检表等证据。韦志刚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并不是刑讯逼供的非法方法取得,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75]
追问:同步录音录像、入所体检表如何体现被告人没有遭受刑讯逼供?宏观概括而未对相关证据详细解构,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浅尝辄止的排除说理的说服力难逃质疑。
(三)非法证据排除与说理实践问题归纳
透过程序视野、说理视角下涉非法证据排除的外在表征,进入更深层次的观察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出期待的效果,亦未有效融入裁判文书说理规范中。证据裁判规则确定的由证据说理指向真实、发现真实的功能发挥受挫。
(1)非法证据认定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运行与理想愿景鸿沟巨大。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或忽视当事人的程序权益拒绝启动,或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引发对法院中立地位的怀疑等,实践运行中受阻严重,偏移了法规范确定的既定轨道。
(2)非法证据排除不畅:非法证据排除审查被随意安置造成程序资源的浪费。在审查证据合法性与否过程中,法官甚至先行对证据举证、质证后,再对审查申请人的排非申请,即先行审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再审查证据合法性。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的本末倒置或者说混乱无序,无法为文书说理提供畅通的证据运行程序。
(3)非法证据排除说理表达粗疏:未在非法证据排除与说理间建立有效连接。突出表现在不予认定为非法证据的文书中,多只言片语以“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或“不予采纳”一笔带过,无对证据证明能力的论证分析,说理浅尝辄止,说服力度明显薄弱。裁判文书作为司法终端产品,无法通过“结果回溯过程”再现程序动态运转。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