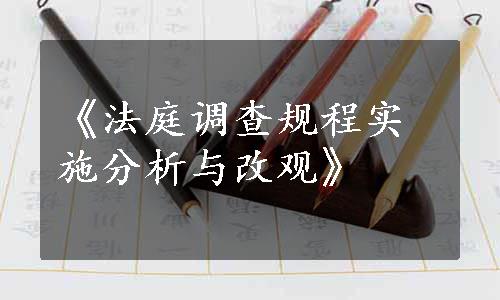
2017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在全国部分法院开展“三项规程”试点的通知》,确定18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其所辖的部分基层人民法院为试点法院,于6—8月期间为每项规程各选取10件以上(一审)案例进行试点。各试点法院均高度重视,按照司法证明、控辩对抗、依法裁判实质化的要求,精心组织,精准推进,统筹安排,周密部署。在省高院的指导和各政法机关的配合下,完成了试点任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此一部分将对《法庭调查规程》的实施状况做一分析介绍。
1.《法庭调查规程》适用情况概览
(1)证人等出庭作证的实证分析。从试点法院工作总结报告可以看出,各试点均将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以及被害人出庭作证作为试行《法庭调查规程》的工作重点。表3是对试点法院证人等出庭作证情况的简要统计:
表3 试点法院[60]证人等出庭作证量化统计
续表
注:表格中数据除广州市外均来源于各试点法院“三项规程”试行总结报告。
〔60〕 王珊珊:《广州中院深入开展“三项规程”改革试点工作》,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8月10日,第1版。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其一,在表3的统计中,个别试点单位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典型案件少、重视不够等因素,在其试点总结报告中未反馈证人等出庭作证的具体数据,故此一内容暂付阙如。其二,有些试点法院地区案件量相对较少,如海口中院在试点期间受理的刑事一审案件数只有22件,可以适用“三项规程”的案件仅有11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三项规程”的试行,未能达到开展试点工作的最大效果。其三,以上统计数据并未区分证人等出庭作证的申请主体,未能直观地反映控辩双方申请证人等出庭及其实际到庭的对比情况。笔者试作一推测,控方申请或法院通知证人等到庭的实现率应高于辩方。
表4 证人等出庭作证庭审效果一览
续表
续表
续表
注:表格中案件均来源于各试点法院“三项规程”试行总结报告。
涉及关键证人的典型案例及评析。阿卜杜沙拉木·阿卜杜克力木故意杀人案[61]中,关键目击证人沙吉旦木·热依那洪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分别对证人进行发问,证实案发时被告人在刺戳被害人后还有一个“拧”的动作,加重了被害人伤势,最终导致其死亡。被告人王燕青故意杀人案[62]中,关键证人出庭,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案件客观真实性。被告人陈建楠故意杀人一案[63]中,被害人以证人身份出庭,经控辩双方对被害人简明扼要地逐一发问,使被告人陈建楠实施犯罪的发展经过、具体细节等清晰地展现在法庭之上,便于法庭查明事实。在成都中院一起贩卖毒品的试点案件中,购毒者系关键证人,经法院通知后拒不出庭。法院签发强制出庭令,并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但法院和公安机关均未再查找到该证人。最终,法庭因无法查实证言的真实性而未采信该证人证言,且作出因证据不足、指控的贩卖毒品罪不能成立的判决,被告人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由上可见,关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对于查明关系定罪量刑的事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最终判决。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法庭更加清楚直观地了解相关事实,使证据更加确实、充分,最终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侦查人员出庭的典型案例及评析。被告人张雅俊贩卖毒品一案[64]中,侦查人员隐蔽出庭作证在公诉人举证阶段顺利进行,被告人在公诉人作证以后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整个庭审过程非常流畅。被告人张涛涛、丁玉奎抢劫一案[65]中,被告人、辩护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因本案客观证据较少,仅现场一枚指纹指向一名被告人,故二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至关重要。庭审中二被告人翻供并作无罪辩解,要求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公诉人就被告人供述的取证合法性出示了入所体检表、审讯视频等进行举证、质证,辩方对被告人供述及同步录音录像提出强烈质疑,控方申请7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证明取证合法性并对瑕疵证据作出说明,控辩双方充分质证,经合议庭休庭评议后,当庭确认二被告人供述并非刑讯逼供所取得,该证据取证过程合法。该案件的“排非”程序持续时间长达半日,在庭审当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面对被告人、辩护人的直接发问,倒逼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真正做到合法取证。上诉人刘宝来受贿案[66]中,两名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收集行贿人证言的情况,但其只是原则上说明是依法取证,对取证的具体过程等相关情节和对辩护人发问的相关问题并未予以回答,最终,行贿人证言被法庭排除。此案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诉讼中,行贿人证言也未能进入法庭调查程序。因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仅有利于法庭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对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更在证据较为单薄的案件中起到加强证明的作用,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另外,在毒品等特殊案件中,为保护侦查人员而采取隐蔽出庭作证,相比之前一概使其免于出庭也是一大进步。
(2)庭审程序规则适用的实证分析。除证人等出庭作证外,试点法院在庭前会议与庭审的衔接、关键证据与争议证据的举证质证以及讯问、发问的程序规则等方面也根据《法庭调查规程》的规定积极探索试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见表5):(www.zuozong.com)
表5 质证等程序规则适用效果一览
注:表格中案件均来源于各试点法院“三项规程”试行总结报告。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不同法院的实际情况和效果不尽相同,多数法院试行状况成效明显,但也有法院试行工作缺乏实质内容,收效较小。但总体来看,证人等出庭作证状况较以往有了显著改观,证人出庭率及出庭作证案件数明显提升,侦查人员出庭也成为刑事庭审的新常态。而且,细化后的程序规则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与实践性,给庭审中的诉讼主体以明确指引,尤其是质证规则的完善大大提高了庭审效率,进一步推动庭审有序高效进行。然而,除上述庭审效果较为理想的方面外,《法庭调查规程》的试行也反映出不少问题,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
2.《法庭调查规程》试行所反映的突出问题
虽然《法庭调查规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进了庭审实质化的落实,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细节性问题,有些是业已存在的顽症痼疾,有些是试点发现的新问题。《法庭调查规程》的试行,为学界及实务界共同探讨这些问题开放了一个路径:
(1)关于庭前会议与庭审的衔接问题。首先,部分权利是否需要在庭审时再告知?通常情况下,对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已达成一致的程序性事项和决定,在法庭调查开始前,审判长只需要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即可。但是针对回避权,尽管庭前会议中被告人及辩护人没有提出回避请求,但庭审中有可能会再提出回避申请。对此,在庭审中,是否要再详尽告知被告人及辩护人有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公诉人等人员回避的权利,并征询其是否提出回避申请?如果要告知,怎样告知?《法庭调查规程》对此没有明确,实践中每个法官对操作方式的理解也不一样,如何做好二者的衔接需要进一步明确。
(2)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参与庭审的问题。《法庭调查规程》主要是在传统控、辩、审模式的基础上对法庭调查予以进一步细致规定,对被害人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法庭审理的仅在第7、9、12条中有所涉及,其余规定仅是针对被害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因此,在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出庭的新型刑事诉讼模式下,如何有效展开法庭调查,是试点法院所面临的新挑战。对于被害人参加法庭审理的,其是否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庭审而本人不出庭?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在庭审及文书写作中如何称呼?称为被害人、附民原告人或被害人及附民原告人?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是否需要在委托合同中明确授权其同时代理刑事和民事诉讼,或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分别提交委托手续?试点中也有出现被害人参与后,庭审效果适得其反的情况。如非法集资类案件中,确实被害人有较强的意愿参加庭审,但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往往年龄较大,如果准许其中的代表参与庭审,一方面由于其作为当事人情绪激动,可能影响庭审秩序;另一方面这些被害人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即使参与庭审,对于查明案件事实、维护被害人群体合法权益的作用也不大。因此,关于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参与庭审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
(3)证人出庭难仍然是审判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事实上,在试点过程中,证人、侦查人员、鉴定人的出庭率和出庭作证效果与庭审实质化改革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多数试点法院证人等出庭率仍然较低。首先,出庭作证的多为公诉方申请或法院通知,被告人、辩护人申请的相对较少。其次,控方协助有关人员到庭的积极性不高。《法庭调查规程》第13条第5款规定:“人民法院通知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等出庭的,控辩双方协助有关人员到庭。”但控辩双方如何协助、证人如果不配合如何处理等并没有明确规定,以至于实践中检察机关常以缺乏具体措施、《法庭调查规程》系法院内部规定为由推脱履行责任。例如在兰州中院试点案件宋心民故意杀人一案中,辩护人申请本案的关键目击证人出庭,该目击证人的证言能直接影响本案的定性。其证言支持公诉方的指控,属于对控方指控有利的人员,而控方以该证人已有证言在卷为由,不愿履行相关协助义务。再次,侦查人员出庭,其出庭身份、发问规则、如何着装等具体规定尚待明确。此一问题在本文第四部分“《非法证据排除规程》的实施状况”中有更为详细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最后,有专门知识的人提供质证意见或解释意见,其出庭应安排在什么时间?比如,是否在公诉人出示鉴定意见并申请鉴定人员出庭后,有专门知识的人就可以出庭?还是等辩方举证时才出庭?这些程序需要进一步合力构造。
(4)当庭异议的规范问题。首先,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如何提出异议?采用口头提出“我反对”,有模仿影视作品中西方庭审模式之嫌,不够严肃,且口头打断易扰乱庭审纪律;采用举手的方式,有时可能审判长没看到,或故意视而不见,导致异议制度落空。其次,辩护人在质证过程中滥用质证权、异议权如何进行规制?在兰州中院试点案件林秀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陈伟安骗取出口退税一案中,经过两次庭前会议,控辩双方已经达成集中出示大部分证据,对辩护人要求单独示证的部分证据逐一出示的意见。但在庭审中,辩护人要求所有证据一证一示一质,有借庭审逐一示证补其阅卷不力之嫌。对于此种拖延诉讼进度的行为,暂无相关规定予以规制。类似情况发生在成都中院的一起试点案件中,无论公诉方主张什么,辩方都提出异议,严重影响了庭审秩序。最后,审判长对异议作出处理后,申请方不服的,应当如何处理,目前也无规定。
(5)对控辩双方无争议的关键证据的质证方式问题。《法庭调查规程》第31条规定:“对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充分听取质证意见。对于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性证据,举证方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其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对方可以发表质证意见。”根据该条规定,即使控辩双方无异议的关键证据也应当单独举证、质证。但试点法院报告表明,控辩双方的依据不同、标准不同、诉讼目标不同,所指向的关键证据也不相同,对此很难达成实质的统一。大多案件是法庭将许多客观证据归纳为关键证据,而多数现场勘查笔录、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虽关系到定罪量刑这一实质问题,却又与控辩双方的证据争议意见、焦点问题不交织。从庭审效果来看,控辩双方无异议的关键证据一证一质,与控辩双方有争议的关键证据一证一质,其对抗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前者不仅弱化了实质对抗效果,更严重影响了庭审效率。是否对所有关键证据均单独举证、质证,值得商榷。
(6)法官的庭外调查权问题。根据《法庭调查规程》的规定,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问题可以简化调查和辩论,但实践中也存在辩方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而法庭认为指控罪名不当,或控辩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法庭却有异议的情形。当指控的罪名较轻,法庭拟认定更重的罪名时,应当如何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调查?对于控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和证据,法庭对其展开调查的依据及边界如何?控辩双方与法庭的观点不一致时,法庭是否需要在调查和辩论阶段详细阐明理由?这些问题仍值得深入研究。
(7)关于独立量刑程序的完善。关于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法庭调查规程》仅在第44条中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量刑事实、证据的调查,不影响无罪辩解或者辩护”,但并未系统构建定罪和量刑相对独立的法庭调查程序。是围绕定罪展开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后,再围绕量刑展开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还是在法庭调查中分别就定罪、量刑展开调查,后在法庭辩论中再对定罪、量刑展开辩论?目前该问题尚无具体规定。
(8)法庭认证问题是实践中的难点,即在庭上对不采纳的证据如何准确说明理由。例如案件中被告人认罪悔罪,但辩护人提出证据收集上存在一系列瑕疵,需要作出说明和解释,但这种证据问题在庭前会议中一般不会提出,证据的补强、完善工作往往不到位,导致在法庭上认证难以完成,这也使得一审案件当庭宣判难以实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