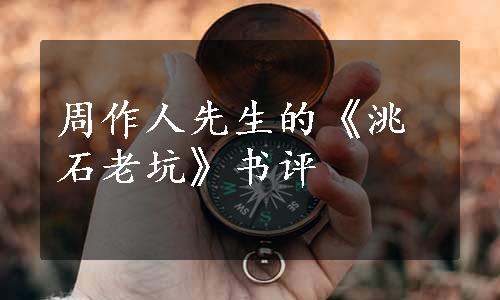
通常,一部书里写在正文前面的话叫序言,而缀于其末尾的则是跋语了。对于这两种文法由喜欢读到喜欢做,感触颇深并视为畏途,且说得很好的,我以为当首推周作人先生。他说:
“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稍长,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于中国的序跋也感到兴趣。桐城派的文章固然无聊,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吴挚甫的《天演论》序与林琴南的‘哈氏丛书’诸序,虽然有好些谬语,却是颇有意思。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好做,于是改而写跋。
“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跋则只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感地写出一点印象,所以比较的容易了。但是话虽如此,我却恐怕连这个也弄不好。”知堂老人所说的话对我而言都很确当,因为我经常面对作文题目,总显得十分枯窘,憋上半天的时间,竟写不出几句话来,很像老笑话里秀才赶考,肚子里一时拼凑不起来三四百字的尴尬情形,曾暗下决心痛改,可仍没什么明显长进。但读者倘若相信了知堂老人针对自己所说为文的“弄不好”,那就大上其当了,曲折荡漾,欲擒故纵,是他叙事说理抒情的渊博文风,现今能出其右者恐怕见不到的。不过俞平伯先生曾讲过,文无定法,文成则法立,在他这句话的鼓励下,尽管自己写点文字的畏难情绪没有改变多少,可师友的盛情难却,总得硬着头皮拼凑下去的。
阮煜兴先生的洮艺情缘,我是近几年通过媒体一篇篇的报道以及和他多次深入的交流了解到的,唯觉着可惜的是,报上专稿记述的仅局限于屈指可数的细节,挂一漏万,倘若读者以为从那些个白纸黑字里就可以知道阮煜兴先生做人做事的思想全部,实在有点儿雾里看花了。我觉得这部文集中的砚石即是卓尼洮乡的土地上滋养的精灵,又承载着阮煜兴先生生命的苦乐是不容怀疑的。只是我与洮河石砚的缘分很浅,仅存的一方偶尔摆放在案头,虽然因了把玩会莫名产生情感的波动,提起喇嘛崖与水泉湾也能感到一种遥远的亲近——本来很是荒寒的藏地竟不觉得怎么陌生,但这些终属于脑海里的幻想,荡胸生层云罢了,缺少了身临其境下的跋涉和体悟,同阮煜兴先生式的衷心爱好,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曾经读过一些慨叹洮石生得不是地方、质地上乘却名实不符的文章,常常不免被作者掀动起酸楚的意绪。无须回避,我是乡土气息很浓重的人,非常关心甘肃历史文化的过去、现状,特别是和阮煜兴先生接触多了,对洮砚我所不懂的东西和我所渴望的信息,都想千方百计地存储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有如若干年前看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努力叫自己记住里面主要人物的绝世功夫与男女间爱恨情仇的故事,专备闲谈时他有来言我有去语的大众知识上的满足。由此可知,《洮石老坑》所能给予的恰恰是我所缺失的,他不肯流俗的创新智慧以及人格魅力,我尤为喜欢。
2012年11月28日,阮煜兴洮砚作品研讨会上,我称他的制艺已趋向文人化的路子,渐渐从传统的龙凤、宗教、传说等图案中走了出来,吸取自宋元以降的山水人物花卉画的养料,将绘画元素融入作品中,让洮石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陈师曾语),而且他已经在部分作品中做到了,如一对上刻蜘蛛的“知足砚”,阴刻的蜘蛛网下利用石面天生的一条垂直的丝线,于下方连接处再浅浮雕出一个悬挂着的蜘蛛,颇具生活哲理的创新,尽管此类的神作在这部书里不是很多,它却印证了脱胎换骨的不易,扯不断理还乱的勾连。近几天来,无论看实物还是翻阅其他的洮砚图录,我发现仿古、写实占据着绝大多数,刀法细致,形象逼真,还结合石形石纹石色,似乎潜藏有与时俱进的新发展,却又不尽然——盲目地攀比大而全,追求百龙砚千龙砚,刻意讨巧政治,注重轰动效应,而不专在高雅不趋时上下功夫,我想这种争创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举止可以打住了。图案的求新,必须要有文化的底蕴,要删繁就简略含涩味,才值得让收藏者反复去读,所以砚工的视野必须开阔,仅靠大是无益的。以追摹传统石砚为根本,旁及古玉、瓦当、雕塑、青铜器、书法篆刻、山水花鸟画等领域,再用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给予杂糅调和,不拘泥于陈规,不蜕变成野马,让学养与情趣统领布局的经营,方能打造出耐人思量的意味来。我说意味,旨在强调人生历练中取像于花择音于鸟的一种静虑,并不要那些个老生常谈的谐韵,或者摆出一副副乖戾的面孔。阮煜兴先生的洮砚近两三年便多有静虑的意味,这正是他近于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正果的地方。唐僧取经,暂且撇开宗教的色彩不言,无疑是他实现志向的具体行为,人格的特征是独立的,丝毫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不仅如此,中国最早的诗歌,即强调诗言志的重要性,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掌握了写诗技巧的人,他的叙事说理抒情,必须表达出自己观察、思索后的态度,否则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令人昏昏欲睡矣。无独有偶,相对于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明道”,至宋朝理学家周敦颐加以完善的“文以载道”来说,则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以传播儒家之“道”为目的,带有集团教化的性质。就此两者的倾向性我是赞成诗言志的,更乐意让身心浸在文学艺术的氛围里养成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明代的公安派凭抒情的态度写真实的个性表现,可以算作一例。文学或艺术的创作注重的是内心思潮的宣泄,绝非推进御用教化的工具。——从《洮石老坑》说到诗言志,又从诗言志说到文以载道,话题扯得比较远,实在我只想说明,已基本脱离实用功能的砚台,将来它的创作应是作者高雅的情怀与聪明的才智的融合,最终脱胎出自己的风格面貌。阮煜兴先生这部砚艺集是现今继承加创新的代表,文化视野超出一般制砚人的眼界,有跨越时代的潜力,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也就写下了以上的话。(www.zuozong.com)
张发栋
2013年1月24日初稿
2017年7月29日定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