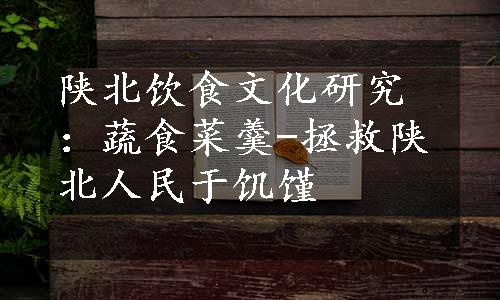
“拔下了苦菜度年馑,交下了朋友毁名声”。年馑,这个特殊的名词成为令陕北老一辈人不寒而栗的可怕记忆。至今陕北人珍惜粮食的习惯就源于遭受过饥饿折磨的陕北人心中悸动不已的梦魇……
民族记忆中的苦难就是历史最好的传承方式之一,它在一次次的讲述中被再次记忆,而关于这记忆载体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来源于陕北地区独特的山野菜文化。
3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关于灾难来源的解释已经有了明晰的看法。哲人老子曾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兵者,不详之器。”“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灾难是触动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深刻地印证了这些观点。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陕北就与灾难有着密切的联系。地处边境地带,自然少不了战火频仍。
陕北的历史充满了灾荒。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陕北的不幸。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大规模军屯等造成了原有自然条件的破坏,加剧了灾害的频度。从先秦直至清朝为防御外敌入侵,政府都曾在陕北地区大量驻军,开垦荒地,军屯民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榆林卫有屯田3500余顷,共计48100余顷。在这些卫堡中,驻守“官兵五万五千三百九十七名,马、骡、驼三万三千一百五匹”(《延绥镇志》)。庞大的驻军仅长期伐薪烧炭、烧火做饭一项,对山林的破坏之巨可想而知。
历史上,陕北发生最多的自然灾害是旱灾、风灾、霜冻、雹灾、虫灾、涝灾、地震、瘟疫、鼠疫等,呈现出极其复杂纷繁的状态。陕北人民在自然灾害、战乱、苛政、赋税、徭役等多重摧残下,流落他乡,致使陕北人烟稀少,满目凋敝。
历史的轨迹总是深刻而让人铭记的。在饥饿中,人们要想继续存活下去,就必须想办法填饱肚子。因此,他们从不在乎吃食的好坏,味道如何,只希望能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安顿自身基本的温饱。在这种环境下,陕北人民养成了制作山野菜的饮食习惯。
与此同时,凡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每年都念叨着要存粮,以防来年收成不好,没有粮食度日,这用陕北人的话说就是“跌了年成活不了”。因此也就有了“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的俗语。如果有年轻一辈不懂得积蓄粮食,不按照老人的指示做,就会遭到训斥。在陕北的南部,各家各户都有存粮的窑洞,窑洞中有硕大的架囤,一个囤子少则存十几石粮食,多则存几十石粮。如果每家每户都存满粮食,差不多就要存上3000斤到上万斤粮食,如果按照一个人年食用粮400斤,五口之家每年消耗粮食两千斤,三年消耗粮食6000斤。陕北大多数家庭都要攒够三年的粮食,所谓的大户人家,不是金玉满堂,而是余粮满仓,仓廪充实。陕北北部气候干燥,因靠近沙漠,粮食收成更差,他们存粮用大缸,有粮食的存几缸谷米,没有粮食的存几缸谷糠,大户人家有时也存一些谷米谷糠,以备荒年饥馑。陕北中部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各家各户开荒种地,一家人种地一座山,广种薄收,打下的五谷杂粮土豆红薯,埋藏储存。挖个大坑用谷草铺垫,倒入粮食,壅土掩埋,就把粮食存在地里,来年春天用毛驴驮回家里。
每遇到荒年的时候,陕北的人们储存的粮食都不足以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为了不被活活饿死,只能另寻出路,因此,陕北的大人小孩每当看到一种植物时他们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这能不能吃?能不能下饭?他们总在尝试着选择新的可食用野菜。刚刚长出的荞麦芽、制作扫帚用的扫帚苗等都是他们尝试采摘的对象。陕北的山上最常见且能吃的植物一般有蒲公英、茵陈、苦菜和田苣等。
茵陈 陕北人叫它“白蒿芽”,这是春天的第一道山野菜,大地刚刚解冻,阳洼洼上最先露头的就是白蒿芽子,灰白色的小小的叶枝,陕北人就开始拔它。拔回来后,洗净、去根、切碎,与土豆丝一起拌面粉,上笼屉蒸十五分钟,是陕北最常见的吃法——蒸闷饭。白蒿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草药的味道,大家用蒜汁、酱油、辣椒、西红柿酱调着吃,倒也没觉得难吃。吃它的原因是陕北人认为它可以防病治病,可以护肝健肾等等。陕北人没有看错,茵陈确实是一把仙草,春天万物复苏,病毒活跃,人需要防疫治病,我们查了一下医书药典,茵陈也确实有一定的地位。全草入药,可预防流感,治中暑、感冒、头痛身重、腹痛、呕吐、胸膈胀满、气阻食滞、小儿食积腹胀、腹泻、月经过多、崩漏带下、皮肤瘙痒及水肿等症,其散热发表功用,尤胜于薄荷。专家也提供了数种食疗菜谱,其中食疗汤水最经典:以茵陈、煎好的鲫鱼用猛火煲一小时饮用,可有效疏肝、清肝热,是广东人常用的食疗汤水。茵陈清热利湿、退黄,主治黄疸、小便不利、湿疮瘙痒、传染性黄疸型肝炎等。药理学研究有利胆、保护肝功能、解热、抗炎、降血脂、降压、扩冠等作用。春天,陕北人吃的第一种山野菜,除了充饥还有防疫的功效。
苦菜 陕北一种最常见的野菜。很多人分不清苦菜和田苣,认为它们只是因方言的差异而叫法不同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谓苦菜,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生长,而榆林地区的各县区苦菜生长甚多。中国地域广阔,苦菜随地域的差异所指植物自然有所不同。据记载,全国叫“苦菜”的野菜有十几种,再加上各地植物种类繁多,因此我们很难分辨出谁是正宗。就拿陕北近邻山西来说,他们所指的苦菜其实就是田苣。
关于苦菜还有一个典故,话说清末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城,慈禧太后为保命向西出逃,途经关中时,饥饿难忍。此地的地方官进献了用苦菜做成的苦菜团子,慈禧尝后大为赞赏,后来一直对苦菜团子念念不忘。由此可见,苦菜还是能招待客人的上好食物。
陕北人说的苦菜,其实是苦苣菜。陕北人吃苦菜,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传统了,掏苦菜的活计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干的。每年三四月,只要有时间,拿上小锄头或者铲子,提上筐子就可上山掏苦菜了。如果动作快,不一会儿就能掏一大筐。拿回家后,摘掉根茎,拣出里面的枯叶,用开水焯一下,然后放在冷水盆里浸泡,用这种方法来去掉苦涩味效果明显。在用何种方法吃苦菜的问题上,有句话道出了答案:“清油调苦菜,各人取心爱。”这句话说的是,苦菜既可用清油调,也可用盐拌,再倒点醋就行了。两种吃法都极简单,一点儿都不费事。如果喝小米稀饭时加上凉拌苦菜,别提多美味了,清爽之间略带些许苦味,简直令人身心愉悦,感觉惬意非常。
除了凉调,苦菜还能和洋芋搭配,这就是陕北的菜品——苦菜燃洋芋。陕北本就盛产洋芋,用洋芋做成的饭食五花八门,数不胜数。而将洋芋和野菜作为原料做成苦菜燃洋芋,是再普通不过的了。其具体做法是把煮熟的洋芋捣成泥状,拌之以苦菜,加入适量香油、盐以及其他佐料就成。吃的时候鲜香入口,绵软细腻,滑而不噎。
苦菜承载了陕北人太多关于苦日子的记忆。“三月三,苦菜芽芽爬上山”。在饥荒年代,陕北的三月是最难熬的。上一年的存粮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而新种的粮食还在地里发芽。青黄不接的三月可以用来填饱肚子的东西很少,陕北民谚中讲道:“肥正月,瘦二月,不死不活三四月。”旧时有陕北民歌也在叹息缺粮少食的艰辛日子:“神府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正是因为没有吃食,需要男人奔波在外,而女人和孩子则漫山遍野挖苦菜来给一家老少填饱肚子,日子过得极其困苦。春季在陕北是一个特殊的季节,男人春耕播种,收获只能等到秋季,顶天立地的男人也无奈时令季节的等待,也无奈家中余粮无以为继。这时家里比较稳定的饮食来源来自婆姨和女子的采集。青黄不接的季节,婆姨、女子变成了家庭的支柱,这时的妇女在家里相对具有发言权,她们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有更多自由外出的时间,呼朋唤友,叫上姐妹,上山下洼,难得空闲自由,野菜挖着,野花采着,山歌唱着,好不快活。这时的陕北由于世事艰难,婆姨得到短暂的解放。
我常常在想,陕北人对于苦菜的感情一定是不同于其他人的。它是陕北人饥饿困苦日子里的大救星,是上天赐予陕北这片土地拯救万民的“精灵”。它在陕北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骄傲而顽强地生长,不怕旱,不挑土,自由肆意地释放着生命力。尤其是惊蛰刚过,下过一场春雨,漫山遍野的苦菜就疯长起来。
如今,苦菜已经成了陕北各大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特色菜品。人们喜食苦菜,上山掏苦菜的也不仅仅是农村人了。每年到了春夏之际,很多城里人趁着节假日,开着车载着老婆孩子到城郊去掏苦菜,享受山野之间的自由,呼吸渴望已久的新鲜空气。回去的时候带上自己亲手掏的苦菜,无疑是一件让人身心快乐的事。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种难得的劳动体验,更是一种与自然亲近的机会。村里有亲戚在城里住的,通常会让人捎一些给他们,成了送礼的不二选择。我记得母亲也曾给西安的叔叔伯伯们捎过,婶婶们吃过之后都要打电话来感谢一番,谢谢母亲挂念着她们,让她们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我们平常说到苦菜的时候,总免不了提到田苣。五六月在新耕的地里,可以挖到许多苦菜和田苣苗。两种植物的生长习性十分接近,猛一看确实很相像。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的不同。从外形上看,苦菜的叶子发灰,呈锯齿状并且弯曲;田苣的叶子翠绿中带一点紫红色,叶展齿状幅度较小。从味道尝,苦菜怎么做都很苦,而田苣做好之后稍微有一点甜味。
田苣 又叫“甜苣”。田苣和苦菜去除苦味做法并无区别,吃法也相同。只是在陕北,榆林人比较喜欢吃田苣,延安人喜欢吃苦菜,仅仅是喜好不同而已。
沙盖 学名叫沙芥,又叫“三盖”,也有地方称为山萝卜、沙萝卜、沙白菜、沙芥菜等。十字花科。叶片肉质肥,有芥辣味,风味极香。它分布在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多生长在沙丘上、山坡脚及半固定的沙丘上。沙盖的叶子可以翻炒食用或凉调拌食,也能将其腌制或晾干待用。总之,它是靠近沙漠、半沙漠地区人们喜爱的一种野菜。
对于许多外地人来说,沙盖或许很陌生,但是在陕北人,尤其是神木人的眼里,沙盖却是人人称赞的美味野菜。因此在陕北,不管是在大酒店还是小餐馆的菜单上,你都能看到“沙盖”二字。用沙盖制作的饭食里,最受欢迎的要数沙盖拌疙瘩了。
起先的做法很简单。在灾荒年里或者是贫困的那些日子,人们吃不上蔬菜,除了上一年冬天腌制的酸白菜外,没有别的菜可吃,只能想办法到地里弄点野菜调剂一下家里的伙食。四五月,沙盖长起来的时候,地里干活的男人们利用休息的间隙去割些沙盖,等到劳动完将它们带回去给家里的婆姨。婆姨们看到沙盖便心中有数,麻利地将它们摘拣干净洗好,开始做沙盖拌疙瘩。首先将沙盖、葱切成小碎块,待锅里的油烧热了之后,倒入葱、沙盖翻炒,然后加入适量的水烧开。接下来便是拌疙瘩,在大瓷碗里倒入少量面粉,一边拿着水杯往碗里滴水,一边用筷子在碗里不停地快速搅拌。一定要注意滴水的时候要细、要慢,切忌心浮气躁。最后将搅拌好的疙瘩均匀地洒在锅里,等到锅里的水再次滚开后放入盐、味精等调料就能食用。需要强调的是,要根据水量制作疙瘩,太稠或者太稀都不好吃。还有要注意的是拌的疙瘩不能太大,不然不容易熟;疙瘩拌完之后不能有干面粉,否则容易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玉米面饼子或者窝窝头,喝着沙盖拌疙瘩,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其乐融融,这就是莫大的幸福。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变好,可供选择的蔬菜等食物多了,沙盖拌疙瘩的材料也变得丰富多样。在拌疙瘩里加入了西红柿、青椒、鸡蛋等,这样做出来的沙盖拌疙瘩,红、绿、黄等颜色分明鲜艳,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清淡爽口,鲜嫩多汁,滋味无穷。
小时候吃惯了沙盖拌疙瘩的孩子,长大出门后在外游学打工总忘不了当年的那个味道,看到异乡的餐桌上有“沙盖”的字样,都会忍不住吃上一口,却不是记忆中那个熟悉的滋味。他们忘不了的不仅仅是家乡的味道,更是对家中父母浓浓的思念与感恩。
蒲公英 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陕北人叫“黄花菜”,也有人叫“婆婆丁”“黄花地丁”“华花郎”等,陕北南部人叫“圪奴”。它与苦菜一样属于长在山坡、路边、田野、河滩等处的植物。它是一种有圆锥状根茎、波状齿叶子,并且叶子向四周摆开,叶子中间有长茎托举着一朵黄色小花的植物。有的地方也称它为“推推菜”。小时候,我曾掏过黄花菜。那时候家里不富裕,平时没有零花钱,我就和伙伴们上山掏黄花菜,拿回家晒干之后可论斤卖给收购的小贩。
平时我们只知道它可以下饭,查看医学书籍发现蒲公英是一味珍贵的中草药,性味甘、苦、寒,具有清热解毒、消痈散结、消炎、凉血、利尿、利胆、轻泻、健胃、防癌等多种功能。主治急性乳腺炎、腮腺炎、淋巴腺炎、瘰疬、疔毒疮肿、急性结膜炎、咽炎、感冒发烧、急性扁桃体炎、风湿性关节炎、急性支气管炎、胃炎、肝炎、肺炎、胆囊炎、急慢性阑尾炎、泌尿系统感染、骨髓炎、阴道炎、盆腔炎、十二指肠溃疡、痤疮、粉刺、结石症等数十种病症。它具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维生素C及矿物质,对消化不良、便秘都有改善的作用,另外叶子还有改善湿疹及舒缓皮肤炎、关节不适的净血功效,根则具有消炎作用,可以治疗胆结石、风湿,花朵煎成药汁可以去除雀斑。《本草纲目》有句云:蒲公英嫩苗可食,生食治感染性疾病尤佳。蒲公英不仅营养丰富,植物体中还含有蒲公英醇、蒲公英素、胆碱、有机酸、菊糖等多种健康营养成分,而且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是成熟之后的蒲公英,随手摘一朵花絮,用嘴一吹,小绒毛就会飞得到处都是。如果站在长满蒲公英的地方,遇到风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漫天随风飘舞的蒲公英,景致实是令人心旷神怡。成熟之前还处于生长期的蒲公英是可以做成饭食的。记忆中饥饿的时候,村中人们就摘取黄花用来做成“和菜汤”。蒲公英的花可以做酒,叶子拌上油和醋可以生吃。当然,叶子也可以烹食,油炸、煮粥、煲汤都行。
小蒜 陕北人一向爱吃芫荽、葱花等调味品,喜欢切碎盛在小碗或者小碟子里,吃饭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添加,小蒜便是其中的一种。有人云:“三月小蒜,香死老汉。”小蒜又名山蒜、野蒜,古时称为“荤菜”,外形与大蒜相似而较小,后因汉朝与西域通商,胡蒜传入中国后,为有所区别,遂以小蒜为名。它的根茎没有大蒜那样的蒜瓣围簇,而是和洋葱的结构一样被层层包裹起来。它与我们平常所吃的蒜,功用相同,但其辛辣气味要强于大蒜。它可以炒着吃,也可腌制成小菜。
用盐腌制而食,是陕北人普遍的吃法。人们去地里干活的时候,顺带掏一把小蒜带回家。主妇用做饭的间隙拣好,洗净切碎,放入适量的盐等佐料,大约腌制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吃饭的时候挑上一筷子放在碗里,清香无比;或者拿个馒头,从中间掰开,夹上一些小蒜,吃法类似于我们常见的菜夹馍。也有大量挖掘小蒜,切碎用坛子腌起来,或腌成咸口味的,或腌成酸口味的,吃面、吃馍均是上好的小菜。十几年前村里人山上干活的时候总会带着馍馍和腌制好的小蒜,中午饿了,席地而坐啃着馍馍嚼着小蒜,这便是顶好的午饭了。民间谚语说:“麻汤饭和小蒜,老婆吃了打老汉。”麻汤饭是用小蓖麻出过油的麻子汤熬的粥饭,味道香浓,再佐以下饭的小蒜,吃得老婆都会与老汉打情骂俏。
现如今的小蒜也算得上是餐桌的常客了。它能做成小蒜摊饼、夹馍、小蒜炒肉等等,还在有些汤里承担调味的功能。
地软 学名地钱,俗称地木耳、地脸皮,是地衣类植物。说起地软,陕北人都是知道的,在很多地方都称之为地耳。城市里的人们经常会误认为地软是生长在地上的一种青苔。它平常很少见,一般在大雨过后出现在没有污染的山坡草地上,成群体状或者团状,乍一看和木耳倒有些相像,故此得名,但它比木耳更加细嫩、柔软。(www.zuozong.com)
捡地软是一项老少皆宜的活动。尤其是刚下过雨之后,空气清新,在屋里待久了的人们特别想出去活动活动筋骨,捡地软无疑是一项最佳选择。小孩们会挎着小竹筐,三三两两结成团,争先恐后地奔向有地软的山间草林。大人们则会在干农活的时候,路上遇到便随手捡一些揣在兜里带回去。总之,陕北人民对这个天然的食材很是喜爱。
如何将捡回来的地软清洗干净,可是个麻烦事。因为地软比较脆,又比较软,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揉成碎末。通常这个活计是由母亲自己动手,不让我插手。她总是说,好好的东西不能白白让我糟蹋了。那时候我总不以为意,认为母亲小气。如今想来,她是见识过陕北闹荒年的,亲身经历过那个可怕的没有吃食的年代,所以才会珍惜一切能吃的食物。生活在陕北的人对食物一直都有一种敬畏的情结,他们很感激大自然的馈赠。小孩如果剩饭或者挑食,都会遭到大人的训斥。归根结底,大家是被灾荒闹怕了,不想让历史重演,因此对于节俭自然具有一种责任感。
地软在经过清水淘洗数次后,可以做成不同样式的食物,炒食或做汤或加肉炒食都行。
在灾荒年代,地软的做法极其简单,无非就是将地软洗干净炒熟就可以拌饭吃了。流传下来的吃法就是地软燃洋芋了。和苜蓿炒洋芋一样,也是要将洋芋煮熟弄成粉末,放在锅里爆炒后搅拌均匀就可出锅。值得指出的是,地软洗干净后要在水里泡上几个小时,目的是除去雨水与泥土混合的味道。
地软包子有些食堂就叫“草包”,这是用地软做的最好吃的一道食物。它在陕北远近闻名,人人都喜欢吃。母亲是全村做饭手艺较好的,做地软包子更是拿手。地软包子现在可以包各种馅料,但是陕北人最拿手的就是洋芋丝包子,洋芋加工成扁牙丝状过水去淀粉,加入地软,再加入少许铡碎炼出油的猪油渣,放入调料,包成包子,醒好蒸十分钟即可。土豆丝保留一点脆感,猪油渣也有一点脆爽,地软软软绵绵,味道口感绝对上乘。地软每次做好之后,留下家里吃的,其余便分给左邻右舍们尝。当然这种礼尚往来的做法,有点交换饮食的默契,陕北的俗语说:“一碗来,一碗去,一碗不来断了气。”陕北农村民风朴厚,百姓纯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爱陕北的农村、喜欢陕北饮食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我自己是陕北人,而是陕北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虽然是粗茶淡饭,却让我深切感受到来自村里人内心的温暖与关怀。在陕北的饮食里,你能吃出他们的善良与热情,感受他们的勤劳与质朴。
地软炒鸡蛋是一道由地软做成的夏季时令家常菜,绵软适口、鲜香美味、口感醇厚,非常适合下饭。将地软、韭菜、辣椒等都切成小块,呈半碎状态,接着打好鸡蛋,加入盐搅拌均匀,撒上葱花;同时,锅里倒上适量油后,放入鸡蛋翻炒,然后加入切好的地软等材料,大约翻炒片刻即可出锅。地软炒鸡蛋虽然做法简单,但这道食物营养价值极高,且具有明目降火的功效。
地软豆腐是先将地软洗干净待用,然后将豆腐切成小块放入锅中煮一下立马捞出来,然后在锅中倒油烧热之后,爆葱花,倒入豆腐,添加配料盐、味精和水适量直到煮沸,最后将地软放入锅里文火慢炖,等两样食材相互入味之后就可出锅。
苜蓿 俗称“三叶草”,这是陕北地区种植喂养牲畜的牧草植物。榆林与内蒙古接壤,属于半农半牧区,历史上与少数民族融合,受到其影响,畜牧业比较发达,因此很多地方都养羊、牛等牲畜。苜蓿作为防风固沙、绿化山区与贫瘠地带的一种优良品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生长周期又短,割了一茬后很快就会再长出来。春夏时节,山上长满了苜蓿,郁郁葱葱,放眼望去一片翠绿,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绿色屏障。
那些年家里养了几只羊,母亲就经常打发我去山上的苜蓿地里割苜蓿。等我筋疲力尽扛回家后,邻里就都会来我家要点苜蓿。母亲为人豪爽,各家都会打包很多回去,不一会儿,整整一筐就见底了。我一看自己割的苜蓿没有了,外面羊圈里的羊还在“咩咩”叫,就躲在屋子里生闷气,责怪母亲把苜蓿分完了。母亲就会笑着提了草筐,拿着镰刀又上山去割。
如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好笑,有什么可生气的呢?本是山里长出的草而已,不过是费了些力气罢了,于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村里人之所以吃苜蓿,倒不是天生爱吃,只不过旧时的陕北没有菜品,有人看到苜蓿颜色翠绿可人,便尝试着做成菜品。
事实上,苜蓿做的菜品是挺好吃的。前些年我家里还会经常做苜蓿炒洋芋。在山上挑一些较嫩的苜蓿头掐回家,摘拣干净,洗好后放在开水锅里焯一下,大概八成熟即可捞出,随后切碎备用。紧接着将土豆去皮后煮熟,用擦子擦碎。锅里倒油,待油温足够热后放葱花爆炒,接着倒入苜蓿和洋芋搅拌均匀,三到五分钟就可出锅。米饭配苜蓿炒洋芋是最绝妙的搭配。我记得村里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做的,这样既不失苜蓿的青草香味,又可以尝到新鲜菜品,如果手艺拿捏得当,简直是人间的美味佳肴。
除了苜蓿燃洋芋,用苜蓿做的菜品还有许多,如苜蓿麦(闷)饭、苜蓿饼、苜蓿炒肉等。麦(闷)饭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洋芋擦擦。陕北人最讲究饮食搭配,一荤一素相结合,营养更为均衡。荤肉与苜蓿搭配,去除了肉的腥味,将苜蓿的清香渗透到肉里,口感俱佳,让人回味无穷。苜蓿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野菜,它没有怪味,可以和许多食材配合,包饺子、包包子、炒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蒸在锅里时院子里能闻见香味,放在餐桌上时,大门口能闻见香味,香飘满村一点都不夸张。
马齿苋 也叫马苋。叶子像马齿,故而得名马齿苋。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生长,是田地里、路边上随处可见的一种野菜。它叶子很小,根茎很大片地铺在地上,手感柔软;它耐旱,生命力很强,即使把它连根拔起,放在太阳下面长时间晾晒也不会枯死。
马齿苋的吃法很多,除去根部洗干净后,可以直接炒着吃;也可以将它放入烧开的沸水中焯一下,切碎拌菜吃,还可以做汤、饺子馅等。以前在农村,人们会把马齿苋挖回家后,洗净晾干储存下来以备冬天的时候食用。马齿苋的味道不怎么好,当农村的生活变好了之后,人们就不太愿意吃它了。现在,城里掀起一股吃野菜的风潮之后,吃马齿苋又风靡起来。
槐花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洋槐树也许就是一棵树,供观赏。而对于陕北人而言却是不同的。面对饥饿,他们想方设法在绝境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当看到院子里或者山上的槐树,白色的槐花挂满枝头,香味飘散整个村庄时,被饥饿禁锢的味蕾受到了刺激,他们便本能地摘了槐花吃。后来,人们不忘槐花,试着将槐花放在各种饭食里面,也创造出了不少新的吃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逐渐增多,很多事情已记得不太真切,但儿时的记忆却越发清晰。那时候的每年4月,槐花开放时,空气中就散发着槐花沁人心脾的清香。槐花如雪,村子里、公路上到处阵阵幽香,那味道真是让人心醉。小时候我所见到的大多是白色的槐花,也有紫红色的(不可食用),却并不多见。小孩们对于捋槐花这件事总是充满了兴致,大约是在父母的允许后就可以明目张胆地爬树了。凡是被小孩子捋过的地方,槐花散了一地,如遇有风,便吹得到处都是。小孩们把槐花当作了嬉戏玩耍的工具,大人们则用他们灵巧的双手制作槐花饭食。
玉米面蒸槐花,就是将槐花骨朵捋下洗干净沥干水分,然后放进开水里焯一下马上捞出,随即倒入凉水中泡一遍,控干水分待用。接着在盆内倒入玉米面,拌入槐花,搅拌均匀后放在锅里蒸上十多分钟。最后调配料,蒜蓉、醋、盐等依口味添加即可。
槐花洋芋擦擦,也叫槐花麦(闷)饭,是一种充满槐花香甜的饭食。陕北洋芋擦擦的各种做法,万变不离其宗。槐花洋芋擦擦也是如此。想要做槐花擦擦,选槐花是关键。捋的槐花不能开得太过,否则甜味变淡入口难吃,要选似开非开、含苞待放、色鲜花嫩的槐花。槐花捋回家后,将枝叶上的槐花轻轻摘下,洗净待用,然后将洋芋去皮后,用擦子擦成丝,拌入面粉。最后将槐花和洋芋擦擦搅拌好,撒上适量盐,放入锅内用旺火蒸,蒸七分钟即可。熟了之后可以浇西红柿汤汁吃,也可以放在锅里炒着吃。
我们所知道的槐花饭食,除了前面介绍的之外,还有很多,如今的槐花饭食更是开发得非常齐全。人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将槐花与粗粮、细粮搭配,营养风味别具一格。做成各种各样的营养美味食物,如槐花糕、槐花炒鸡蛋、槐花烙饼、槐花烫面、蒸饺,还有用槐花制作的汤或者粥等等。洁白胜雪的槐花,在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还能制作不同口味的美味,给人们以时令的享受,真是与时同乐了。
榆钱 除了槐树,榆树也是陕北人喜爱的树木。在陕北的村里村外、公路街道两旁都有它,这是极平常的树木。榆树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它耐寒、耐旱、耐瘠薄,不择土壤,适应性很强,即使在灾荒年代也可以生长。说到榆树,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榆钱。榆钱本是榆树的种子,因其外形圆薄如钱币,因而得名,又由于它是“余钱”的谐音,所以大家都叫榆钱。过去五六月粮食紧缺的时候,满树的榆钱就是自然的恩赐。
依旧记得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榆树,比窑洞还要高出许多,树干很粗,大概需要两个小孩才能抱得住。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串串榆钱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曳,整个院子沉浸在淡淡的清香里。这时,我就会忍不住想要捋下榆钱去尝。它的味道甘甜,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榆钱的吃法花样繁多,除了生吃外,还可煮粥、蒸馒头、蒸包子等等。宋代就有用榆钱煮粥的记载,大文学家欧阳修曾吃完榆钱粥而意犹未尽,留下了“杯盘粉粥春光冷,池馆榆钱夜雨新”的诗句,可见榆钱粥的美味是流传已久。它的具体做法是将葱花炒后加水烧开,用小米煮粥,米将熟时放入洗干净的榆钱继续煮十分钟左右,加适量调料就能食用。榆钱粥里既有小米的味道,也有榆钱淡淡的清香甜味。
榆钱饭既是穷苦人家的救命粮,又是人们调节口味的时令风味。用榆钱和面粉制作的饭食要数榆钱玉米面馍馍了。其做法和玉米面蒸槐花的做法一样,将树上的榆钱摘下洗干净,和玉米面拌起来放入蒸笼蒸熟就行。其实这些都是当年陕北人流传下来的吃法,做法并不复杂,人们只是想把家里的粮食做得更好吃一点。现如今的榆钱玉米面馍馍做法虽与过去差别不大,却更加香甜。厨师们或者主妇们都选用了上好的玉米精粉和榆钱,在此基础上添加各种佐料,而做好的馍馍酥软香甜,比起旧时,真的是天差地别。现在最常见的榆钱做法就是榆钱麦(闷)饭,做法与蒸洋芋擦擦一样,吃法相同。榆钱因有榆树的黏性,故吃起来口感软糯。
榆钱汤是现代人用榆钱制作出的新吃法。第一步,准备食材,包括清洗干净、沥干水分的榆钱,洗净切成块的西红柿,橙子等适合煮汤的水果切成的薄片等;第二步,汤锅里加水烧热,分别放入榆钱、西红柿和其他水果,用中火煮沸;第三步,加入白糖,待白糖溶化后,用少量淀粉在锅里勾一下芡,形成糊状即可。榆钱汤色泽鲜艳、美味香甜,具有健脾补虚、养血安神的功效,是滋身进补的良方。
榆钱包子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怀念。我最早吃的榆钱包子是外婆做的,那个时候外婆已是七十多的高龄了,不像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清闲。她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在我的记忆中,外婆好像从没有在灶台和院子两处地方停止过。舅舅、舅妈上山干活,外婆则在家里做饭、喂猪、打扫院子等等。因为某些原因,舅舅家里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水平相对差一些,可外婆总是能用她灵巧的双手把家里仅有的东西做出很多花样来。山里的时令野菜,像苦菜、黄花菜、小蒜等都会被外婆拿来做菜,所以只要看看外婆做的菜就能判断出月份来。到处可见的榆钱自然也是外婆的食材。外婆每次做榆钱包子,总要给我和表弟讲一讲她经历的困难时期,人们生存如何艰难,啃树皮,吃草根,直言那时能吃上榆钱简直就是最幸福的事。
外婆的榆钱包子是用玉米面做成的。先将磨好的玉米面倒在盆里和好发酵;再制作包子馅,把事先捋好的榆钱拣好洗干净切碎,锅里放入葱、姜、蒜爆炒,然后倒入鸡蛋、榆钱翻炒,炒至八分熟倒出,加入盐、味精等佐料拌好就可以包包子。现在肉类产品随处可见,如果想吃肉馅,可以将猪肉剁成粉末和榆钱搅拌。包子放在锅里蒸上十几分钟,就能闻到香喷喷的味道了,馋得我和表弟一直在灶台旁边打转。那种味道,我至今难以忘怀,因为那是属于记忆中外婆独有的味道。
这样的制作过程,陕北的妇女都烂熟于心,每一道工序、每一味调料都掌握得很好。对于陕北人而言,山野菜不只是一种食材、一类商品,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一个地域民间文化的缩影,是老百姓思想风俗的体现。不论是对自然的敬重崇拜,还是对祖先的缅怀和敬仰,山野菜制作的各类饭食都体现着陕北人朴实、简单的情感——敬重自然与感恩生命。时过境迁,野菜早已不是当初抵抗饥饿的救命饭,而是融入了百姓的生活,成了日常的食物。在自家锅灶里用山野菜做出美味的食物供一家老小吃,对于主妇们来说是最大的满足;对经历过灾荒的老人来说,是最大的慰藉。
对自然的崇拜,对生灵的敬重,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或多或少影响着当地百姓的饮食习惯。在城镇的小巷里,我们常常能看到民间小吃。那些民间小吃通常都是再平凡不过的食物。我们现在或许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但还是可以从老年人的讲述中去追寻。对于这个时代与地域来说,忆苦思甜是个永不褪色的话题。
记忆是有味道的,即使有一天我们年华老去,两鬓斑白,但也不会忘记那记忆中亲人相伴的甘甜;而味道也是有记忆的,味道中的家乡记忆是每一个离家游子心间最为珍贵的留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