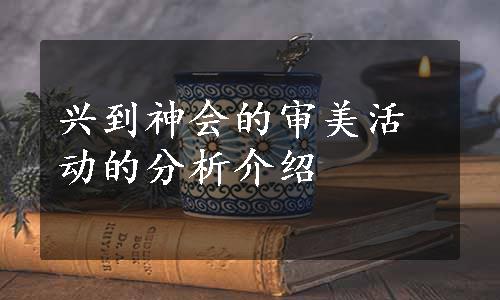
在审美心理活动中,理智并不作为抽象的逻辑形式出现,而物象又不是照相似的机械反映到头脑中。当心物感应时,物作为心理活动的对象被反映到头脑中,成为情志所依托的意象。而对于这些被反映的事物的认识,又不是靠纯理性的判断,而是在保持了直觉活动所具有感性的、形象的特征时,对事物之趣或道德伦理意义,有所觉悟,有所感触,潜移默化。这种艺术思维活动,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有的称之为“兴会”,有的称之为“妙悟”,有的称之为“神遇”。总之,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推理的思维活动,是一种兴会神到、心领神会的审美心理活动,在我国古代文论中,不少人特别重视这种审美心理活动的分析,接触到审美心理的内部规律。但是,由于对这种审美心理活动现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所以有时会陷入神秘主义的迷宫,对此,我们今天就要做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工作,继承其中合理的因素,防止简单肯定或否定。关于“兴到神会”的审美心理活动,我们首先就会想到庄子的“神遇”和“意致”说。庄子学说中的认识论是非理性主义的,他认为对于“道”的认识,不是靠耳闻目见,而是凭“神遇”。《庄子》中有些寓言,如“庖丁解牛”、“拘楼承蜘”、“吕梁丈夫蹈水”等说明的是一个普通的道理:任何技艺,只要肯钻研,勇于实践,久之则熟能生巧。但是,这简单的道理,却被解释为神秘的“神遇”,进而用之于认识活动,就提出所谓“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的“心斋”说,否定了人的认识是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而把它看做是一种孤立的神秘的意识活动。因此,庄子进一步否定知识和理性认识的可靠性,提出了近乎直觉活动的“意致”说,他认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又说:“书不过语,语有贪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从而进一步提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结论,这种理论说得玄之又玄,似乎很难理解,但联系其全部哲学思想仔细揣摩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思维活动带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是偶然性。庄子说的‘神”和“意”,似乎可以离开五官感觉而自由存在,它的活动似乎可以不循一定的认识规律,其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第二是直觉性。排除了语言文字概念的认识,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排除理性的认识,把“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视为认识的最高阶段,这实际上是近似直觉活动,这种意识活动中所认识的事物,具有整体性和具体直观性。第三是任意性。庖丁解牛所谓“官知止而神欲行”,在文艺创作和美的鉴赏中就是由某种诱因的感发而引起无限联想和想象活动,浮想联翩,不是抽象的推理,而是天马行空,神游万里。具有不受视听之区限制的任意性。庄子的这些理论,对我国古代审美理论有很深的影响。诸如应感、神思、妙悟、兴会等等理论,无不与此有关或者类似。
我国古代不少文论家已意识到审美心理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思维活动,力图去解释这种特殊现象,并对它作了精彩的描述。《文斌》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谈到创作中的“应感”问题时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这里所说的“应感”,就是我们常说的创作灵感和美感的冲动。这种审美活动,有时通,有时塞,通的时候则“天机骏利”,塞的时候则“六情底滞,志往神留”。这种看来似乎是独立存在,忽然而来、忽然而去的艺术思维活动,在创作中或审美鉴赏中,表现出偶然性和任意性的特点,其实是创作准备条件成熟与否的表现,也和是否有诱发因素有关。了解这一点,其在“应感”中的“开塞之所由”并不是不可知的,正如庄子说的“神遇”是长期实践的结果,而创作“应感”的开和塞,是酝酿构思到何种程度的表现,同时又和有无诱因感发有关,因为审美活动不是抽象推理,而是要靠具体事物的诱发,即所谓感兴,引起联想和想象,进行形象思维。对这种现象的认识比较全面、解释也比较确切的是把艺术思维活动(也是审美活动)叫做“神思”,其特点是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有鲜明的形象性,也表现出一定的偶发性,有通有塞,有迟有速。但关键在于平时“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神思》。没有把“神思”活动神秘化,认为这是“神与物游”的一种思维活动,把握住了审美心理活动的主要特征。再说到“妙悟”,用佛家参禅作比喻,说明学习和领悟诗法的道理,这里说的“悟”,实际上是说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掌握,也涉及艺术审美活动的特征。讲“入神”,“入神”是诗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艺术美的境界,这种境界在人们的审美心理活动中,排除“理障”和“事障”,也不停留在语言文字之表,而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呈现出这样的审美特征:“……透彻玲珑,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具备这些条件,艺术才能给人以“兴趣”,也即产生美感。艺术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偶然性、任意性,以及联想和想象等等特点,许多艺术家都有过切身的体验,而且不断加以研究和总结,到明清之际,不少艺术家对这种审美活动,有了进一步深入的认识和阐述。王夫之论诗,在强调“以意为主”、情景交融的同时,特别重视“兴会,和终神理”。他说写诗“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又评谢灵运诗《登上石鼓山》:“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落笔之先,匠意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这就是要求情景两得,妙合无垠,俯拾即是,自然逼真,非人工所为,而是神理凑合。这种“神理凑合”又可称之为“兴会”,他批评皮日休、陆龟蒙的诗“差有兴会”,韩退之诗“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而黄庭坚、米芾诗则“益堕此障中”,他所说的“障”,就是严羽所批评过的理、事二障。所谓兴会,就是要“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可见,王夫之所谓“神理”“兴会”云者,一是要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二是在兴到神会之时,获得美感。神理兴会,具有偶发性、形象性的特点,这也是艺术审美活动的特点。兴会神到的审美活动,在叶燮和汪士慎的理论中,得到比较深入的阐述。叶燮论诗,以情、事、理为诗之内容所包,而以才、胆、识、力为写作之条件,但是,对创作的艺术思维活动及审美活动,他又很注意艺术本身的规律,即要“会其指归,得其神理”。在叶燮看来,写诗虽以情、事、理为主,但并非使人在诗中直接说理议事,而是要通过“默会意象之表”去领悟“至理实事”。他以设问的方式借别人之口提出:“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夫诗,则理尚不可执,又焉能征之实事者乎。”这些说法倒有点类似庄子的“意致”说,确已接触到艺术思维的某些特点,但绝对排斥理和事,就会陷入神秘主义。叶燮对诗中表现理、事、情则作了如下解释:“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他以杜甫诗“碧瓦初寒外”为例,说“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然示以默会相象之表……其理昭然,其事昭然也”。这也就是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审美心理活动,其特点是对意象的直接感受和默会,“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因此,诗中所写的文字,从表面看,可能觉得是违反生活常理,违反语法结构。可是,作为艺术品,它能使人在默会想象中得其事理。从审美的角度看,这是感觉的复合体,碧瓦凭视觉,初寒凭触觉,而内外远近是视觉、触觉互通所得一种印象,这些感觉都“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不是凭逻辑所得,这不正是艺术审美心理活动不受逻辑思维规律约束的最大特色吗?而这种“恍如天造地设”的意境,其妙处不就是“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吗?叶燮认为诗人“妙悟天开”,获得最佳境界,也就是“兴会神到”,而不是苦索强求。这种艺术境界的特点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正如他所嘲笑的:“此岂俗儒耳即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审美心理活动中的这种偶发性、形象性和默会暗示的特点,不是逻辑判断的结果。因此,我国古代不少文论家为之迷惑不解,把这些现象看得很神秘。叶燮能把问题说得这样深透,符合审美心理活动的特征,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对“兴会神到”这种审美活动,汪士慎有不少论述,但他是从“神韵”说的角度去领会诗歌的意境美,而缺乏叶燮以“理、事、情”为核心的理论基础,所以就显得有些虚幻,脱离现实。但是,就艺术审美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来说,他的见解也是有合理因素的。汪士慎非常赞赏严沧浪的羚羊挂角、镜花水月之论,这是因为严氏的理论符合“神韵”说的要求。“神韵”所追求的是脱离现实的所谓冲淡、清远、超诣的艺术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获得,是来自“飘渺如在天际”以至于“无香火气”的虚幻世界,只有在“兴会神到”之时,才能捕捉到这种境界。他说:世谓王右军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联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王维画“雪中芭蕉”事见沈括的《梦溪笔谈》,一般人认为不合时序,沈括却认为:“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这种得心应手之妙,就是“神会”,他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汪士慎是很赞赏这一观点的,他认为绘画如此,写诗亦然,故举王维诗为例,王维把不相关的几处地名写入诗中,在旧诗中类似例子也不少,诗人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去看,而是兴会所至,即可入诗。这些例子都说明艺术审美活动中“兴会神到”的特点,所以艺术欣赏,可以跨越时间、空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只求从兴象意趣中,获得美感,而不必“刻舟缘木”,拘泥于事实。这样,我们在欣赏张继的《枫桥夜泊》诗时,也只觉得兴会神到,意境浑成,正如汪士慎说的“神到不可凑泊”,根本就不必斤斤计较“三更不是撞钟时”了。上述三种情况,从审美心理看,各有侧重面,但在我国古代审美意识中,三者又往往是互相渗透的,由心物感应,引起情志的活动,而情志活动又往往是在兴会神到的情况下表现出来。这三种审美心理活动,还有几个共同之处:一是要求含蓄美,即要有寄托、比兴、意在言外,要有景外之景、象外之象。二是要自然之美,无论是写景抒情,都要自然天真,不假雕饰,兴会神到,更是求之自然。三是讲求兴趣、滋味,即是要有美感。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以审美主体的主观感受为主,以主观感受的表现为主,可以说,这也是我国古代艺术审美的民族特色。(www.zuozong.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