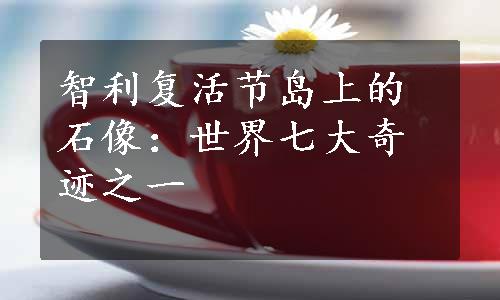
第三节 复活节岛上的石像
智利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像,直到今天它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复活节岛是智利的一个孤岛,也被称之为赫布亚岛,意即世界的“肚脐”,也就是世界中心的意思。面积为117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人。1722年4月5日,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根文(Jakob Roggeveen)于复活节之日来到该岛,因他的海图上并没有该岛的坐标,因此把它命名为复活节岛,岛名由此而来。他探访了岛上的波利尼西亚居民和巨人石像。1774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登上该岛,并绘制了它的海图。但在1858年到1870年间,智利的奴隶贩运船曾掠走了相当于该岛人口1/3的1000名居民作为奴隶,去充当采掘智利海岛鸟粪肥料的劳动力,就连该岛的土著部族的酋长及神职人员也被当作奴隶贩运到了智利,因劳动过于严酷,一年之后他们全部死去,因此无法弄清有关巨人石像被制造出来的原因。当时仅有15名幸存者因患天花而被遣返岛上,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死去。最后,复活节岛上仅存111人。岛上约有600具石像,高度从6英尺到30英尺不等。有的尚未完成,不知什么原因半途而废。
挪威人类学家和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曾于1947年和6名其他海员乘康—提基号(Kon-Tiki)木筏登上该岛(Kon-Tiki是传说中的印加神)。他们乘木筏航行了近8000公里。他在1950年出版了《康—提基号探险记》(The Kon-Tiki Expeditement),竟销售了400万册。1960年出版的《Aku-Aku:复活节岛的秘密》(Aku-Aku:The secret of Easter Island)一书。现在我们根据《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的中译本来了解一下它的内涵。中译本把“Aku-Aku”译为“阿古”。那么,“Aku-Aku”究竟是什么呢?
“我原来并没有阿古—阿古。(原注:阿古—阿古为复活节岛上的小型石像,传说神通广大,能守护洞穴、赐福于人。)”[66]“一个外国人,怎么能知道长着青草的地下埋有古物呢?除非他靠‘马纳’,即超自然的神力的帮助,直接掌握复活节岛的历史,不然,他是无法知道的。”[67]在复活节岛的土著居民看来,“阿古”的力量无所不在,它既是产生这些石像的原动力,也是使外国人能知道复活节岛历史的一种超自然的神力。“我们首次发现,在复活节岛神秘的历史上存在着三个划分得很清楚的时期。在第一个历史时期里,一个具有高度专门文化、掌握典型的南美石工技术的民族,曾在复活节岛从事建筑。我们用碳素测定法证实:本岛最早的发现者,比今天波利尼西亚居民的祖先早一千多年就来到这里了。……看起来,外形像祭坛那样,有一部分是带阶梯的要塞。但是,第二历史时期接着开始了。大多数早期的古典建筑被局部拆毁、改建,冲着面向内陆的陡壁,铺砌成一条斜坡。人们将巨大的石人像从拉诺拉拉库运了过来,并且把石像背朝大海竖立在这些重建后的庞大建筑物顶部。现在,岛民们经常在这些巨型建筑物内部发现葬室。在第二历史时期,正当那项艰巨的事业处于高潮之际,一切工作意外地停顿下来,战争和同类相食的恶浪席卷全岛。又过了好几代人的时间,罗格温船长于1722年率领欧洲人到达复活节岛。这种真正的波利尼西亚浪潮冲击本岛时,这里一切文化生活骤然终止,开始了复活节岛历史上悲剧性的第三历史时期。这时,谁也不再刻凿石像了,人们放肆地将雕像一个个推倒。”[68]雕凿一座石像,并不需要很多石匠。雕凿一座大约15英尺高的普通石像,只要6个人;二三百个石匠,足以同时雕刻相当数量的石像。[69]但是,复活节岛上的土著居民根本不相信这些石像是人类的创造物,就连石头也被认为是自己走到这里来的:“我曾经问过市长,石像是如何从采石场运走的。他的回答和其他人的回答一样:石像是自己走出来的。”[70]“我们已经证实了:180个当地人,饱餐一顿后,就能把一座12吨重的石像拖过原野;假如有木质的滑动装置和更多的人力,就能拉动大得多的石像。”[71]事实上,这些石头究竟通过什么途径运抵复活节岛至今仍然是个谜。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土著居民不避艰险,把12吨重的石像拖过原野?只有一种回答是可能的,那就是宗教信仰,更确切一点说,是对无所不能的精灵的信仰。当地人把这些精灵都叫做阿古—阿古。他们认为那天发生了一件前所未见的怪事,一个肉眼看不见的阿古—阿古帮助他们抬起了石像。[72]比起澳大利亚的“马那”信仰和非洲的“卡根”信仰来,复活节岛上的“阿古”信仰要具体得多,详细得多。它可以说是“前万物有灵论”的化石标本。
“‘不过,我也有马纳。’市长开始夸耀起他自己超人的神力,‘帮我们抬起石像的正是我的阿古—阿古。”[73]看来,就在当时,“阿古”也经常和“马纳”(即马那)相混淆。
上述的引文就足以证明:“阿古”是和“马纳”相似的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它可以为人、神灵或无生命物体所拥有,它也像“马纳”一样,可以有“善”的“阿古”,也可以有“恶”的“阿古”。埃杰顿·赛克斯在他的《非古典神话词典》中有“Akua”条:“Akua,系波利尼西亚神话中无处不在的神灵的名字。”[74]Aku和Akua是同一的。它们的拼法不同,可能是由于翻译上的原因。
海尔达尔不是一般的探险家,他还是考古学家。他最高明的地方,是培养了当地的土著成为考古学家,从而使复活节岛的考古工作能在他离去以后继续下去。美国怀俄明大学的考古学家威廉·马洛伊(William Mulloy)是和海尔达尔一起登上复活节岛的。所以他对复活节岛的看法尤为重要。在《Aku-Aku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中,海尔达尔曾多次提到马洛伊的发掘工作。(以下由于译名关系,将用英文本作为引文)。“复活节岛最早由阿德米拉尔·罗根文(即雅各布·罗根文)于1722年所发现,我们看了他所写的一本关于复活节岛的书,发现这里最早的土著居民用细绳把两颗蓝色珍珠,一面小镜子,一把剪刀挂在他们的小船的船侧。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些珍珠在阿纳基那(Anakena)的王室中被发现。”[75]“比尔(bill,即威廉·马洛伊)选择了一个使人振奋的任务,他是自著名的复活节岛上石像被毁灭以来,第一个着手研究工作的考古学家。”[76]“他首次发现,像谜一样的复活节岛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有着高度文化的人们,他们具有典型南美石匠的雕刻技巧,并在复活节岛上开始了他们的工作。经同位素碳测定,早在1000多年前他们就已经到达了该岛。(后来又经测定,为公元前1680年)。他们是现在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巨大而坚硬的玄武岩就像奶酪那样被切割下来,小心翼翼地被安放到另一些没有裂缝和洞眼的石头上。这些神秘的石块放置在陡峭的石墙上,看上去就像是祭坛,它们被搁置了很长时间,其中一部分成了有阶梯的堡垒。接着是第二阶段开始了:部分早期古典结构的石阶被拆除或更改,一条沿着斜坡的石道被建立了起来,就像是一面对着内陆的墙。一些具有人的形象的巨大石像从拉诺·拉拉科(Rano Raraku)运到了这里,它们背对着大海被竖立了起来。但好景不长,这些巨大的石像突然来到了这里,又突然停滞了。阿德米拉尔·罗根文于1722年来到复活节岛时,那已经是真正的波利尼西亚人到达之后的事情了,该岛所有的文化生活突然终止,悲惨的第三阶段开始。岛上再也没有一把像样的、能雕刻石像的工具,许多石像被推倒在地,在葬礼中,一些巨大的倒下的石像被暂时用来充当地下坟墓的覆盖物。”[77]
这一段文字初步把复活节岛上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后来的研究证明这种划分是对的。“夏至那天,比尔拿着他的测量工具,走向古典的台座,开始进行发掘工作,阳光正好成直角精确地照在印加类型的石墙上。秘鲁印加人的祖先信奉太阳崇拜,这使我似乎又回到了南美古老的文化。比尔发现了更多的东西,平坦的地面上躺着红色的柱形雕像,它们是从塌陷下去的神庙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神庙呈方形,约400×500英尺。围绕着它的土墙还依稀可辨。从人工所留下的燃烧物中提取的物质,经碳14测定为公元800年。这和蒂亚瓦纳科太阳神庙出土的红色的柱形雕像的年代相符。在石墙的前方,比尔发现了古代仪式的残留物,数量很多的焦褐色的尸体被埋葬,他们生前使用的捕鱼工具和他们葬在一起。直到现在,复活节岛上的火葬在考古学上还不为人所知。比尔绘制地图,研究老的巨石结构。在泰·皮托·库拉(Te Pito Kura)的台座上,靠近海边的最大石像被推倒在地,在石墙下面,他发掘出了一个葬礼用的地下墓葬。在已成粉末的人骨中,他发现了长耳朵人(Long-ears)的美丽的耳塞,它是用大型贝壳最厚的部分做成的。”[78]这段文字再一次证实,早期的石墙是用来观察夏至这一天日出方位的,它的建造和天文观察有关。长耳朵人来自南美洲,短耳朵人来自波利尼西亚,现在复活节岛上所有居民都来自这两个地方。有些石像十分巨大,以至于海尔达尔站在它下面很难看出来。见图194。

图194 复活节岛上的石像与人的大小比较
当地的土著居民告诉海尔达尔一个秘密:他们的祖先是用圆木作滚轮把石像从几公里之外的采石场运来,再用圆木作杠杆,把它们竖了起来。这和保罗G.巴恩的说法相一致的:“复活节岛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公元1000年到1500年,这是它的黄金时期。人们以巨大热情建造了更大更多的仪式性台子和几百尊巨大的人像。随着人口的兴旺,雕像也在逐步增加,公元1500年左右达到高峰,此时已建起了大约1至2万座雕像。……竖在台座上的雕像从2米到10米高度不等,最重的达83000公斤。……其中一尊‘埃尔·吉甘特’有20多米长,完成的时候它也许要重达274000公斤。”“有230多尊雕像是从很远的大采石场运到岛屿周边台座上的。”[79]石像制作时,当地土著居民还处于石器时代,其难度可想而知。很难想象,把这些巨大的石像从采石场运到海边,再要把它们竖起来,要耗费多大的人力和物力。毕竟“阿古”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它既不能真的使石像升高,也不能使石像移动。从搬运巨石,雕刻神像,再把石像运到放置的地方,其间不知要花费多大的人力和物力。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新的考古发掘,结果显示出现有石像群是第二次来自秘鲁的部族在毁坏了从前的石像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在未完成的石像中,有高达21米的。它们和祭台一起都建在火山的山腹中。威廉·马洛伊后来一直留在复活节岛上进行重建工作,他终于把一些台座修复了,并把石像重新竖立在台座上。
1978年,新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巨人石像的头部原来都曾镶嵌着由白色珊瑚石和红色霍山熔岩制成的眼睛。考古发掘者塞尔焦·拉普(Sergio Rapu)是复活节岛的当地人,也是海尔达尔亲自培养起来的考古学家,后来,在海尔达尔离岛很久之后,拉普和助手索尼娅·卡迪纳尔(Sonia Cardinali)在复活节岛的阿胡瑙瑙(Ahu Nau Nau)发现了一个较完整的石雕眼睛和4个眼睛的残片,从而证实了这些石像原来都是有眼睛的。新发现的石质眼睛埋藏在石头台座附近约20英尺深的地层下,眼睛的白色部分用白色珊瑚石雕成,一只完整的眼睛约14英寸宽,眼球的直径约5英寸,它是用普那帕乌(Puna Pau)地方的红色熔岩做成的,它可以准确无误地镶嵌到石像头部的眼窝中去。这种红色熔岩还被用来制作石像所戴的红帽子。它们的红帽子像它们的眼睛一样都已脱落。在《Aku-Aku: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中,海尔达尔曾多次提到塞尔焦·拉普的名字,但没有提到他发现石像眼睛的事情,因为那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这些巨人石像和复活节岛上其他一些镶嵌有眼睛的木雕像相似,这些木雕像是用白色的骨头和黑曜石做眼睛,目的是同样的:神也需要用眼睛来审视世界。但是,威廉·马洛伊后来竖立起来的石像都没有眼睛和帽子,可能是因为能找到的石质眼睛数量极少,根本不足以用来对石像加以修复。但和原来石像背向大海有所不同,它们都变成了面向大海。
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像实际上很可能和巨石崇拜有关:“当那些早期人类注视一块石头时,他们看到的并非是一块了无生气、千年不移的石块。它有力、永恒、坚固,是另一种象征着绝对的生命式样。”[80]更何况它以神灵的面貌出现了。在南美,还发现有几十吨重的石块叠在一起,它们之间的缝隙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这些巨大的石块究竟是怎样被叠在一起的,至今还是一个谜。
复活节岛上的原住民对“阿古”的信仰表明,在原始人那里,禁忌和敬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违反了不成法的法规所犯下的罪行比违反一种道德上的禁令会遭受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建立在禁忌基础上的各种戒律具有绝对的权威性。[81]这种强迫原始人不得不服从的种种禁忌,它后面的力量不是我们的眼睛所能见到的,因为土著居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无论是澳洲的“马那”,非洲的“卡根”,复活节岛上的“阿古”都是无处不在的神秘力量,它们支配着原始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复活节岛上的“阿古”信仰,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原始宗教的力量。石像并不仅仅是石像,正如其他的原始艺术一样,它是一种雕刻出来的祈祷,也是人类道德状态的一个阶段。
按照罗素的看法,野蛮人和原始人有着他们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为的准则有许多起源于宗教仪式,它们在野蛮人和原始人的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另一些道德准则,例如禁止杀人和偷盗,具有更显著的社会效用,因此虽然最初与之相关的那些原始神学体系衰亡了,它们却保留了下来。”[82]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道德状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经历了最漫长的阶段,它花去了上百万年的时间。没有这个阶段对自然状态下原始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作出严格的约束,人类是很难过渡到审美状态的。而从道德状态过渡到审美状态,充其量也不过花了几万年的时间。
【注释】
[1]保罗G.巴恩和让·韦尔蒂:《冰河时代的形象》,纽约1989年版,第26页。
[2]S.A.史密斯(S.A.Smith):《在昆士兰的塔尔加发现的人类头盖骨化石》(The fossil human skull found at Talgai,Queensland),载《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报告》,1918年,第208卷,第351~387页;参见M.布勒:《化石人》(Fossil man),1923年版,第370页。
[3]罗伯特·贝得纳里克:《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载《美术》杂志,1993年第8期。
[4]保罗G.巴恩编:《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中译本,第214~215页。
[5]T.K.彭尼曼:《阿兰达人的宗教》(The Arunta Religion),载《社会学回顾》(Sociological Review),1929年1月号。
[6]参见R.R.马雷特和T.K.彭尼曼:《斯潘塞的最后旅行》(Spencer's Last Journey),伦敦1931年版;R.R.马雷特和T.K.彭尼曼:《斯潘塞的科学一致性》(Spencer's Scientific Correspondence),伦敦1932年版。
[7]阿道夫.E.詹森:《原始人中的神话与祭礼》,芝加哥大学1963年版,第136页。
[8]赫尔穆特·彼得里(Helmut Petri):《澳洲的祭礼图腾》(Kult-Totemismus in Australien),载Paideuma,班贝格1950~1954年版,第5卷,第44页。
[9]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纽约1991年版,第38页。
[10]C.施特雷洛(C.Strehlow):《澳洲中部的阿兰达人和洛里查部族》(Die Aranda und Loritja-Stamme in Zentral-Australien),1910年版,第1卷,第2~5页。此外,可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译本,1981年版,第86页:“这些东西(椭圆形的木块和石块,通常都装饰着神秘的图案)极小心地保存在神圣的地方,妇女和儿童都不敢挨近这个地方。每个图腾集团有自己的珠灵卡……这是一些个体的体外灵魂;是祖灵的媒介,也许还是这些祖先本人的身体;这是图腾本质的精华,是生命力的贮藏器。”
[11]B.斯潘塞和F.吉伦:《澳洲中部的北方土著部族》,1904年版,第261、730~737页。
[12]A.B.库克(A.B.Cook):《马斯·德·阿齐尔洞穴的画卵石》(Les galets peints du Mas d'Azil),载法国《人类学》杂志,1903年第XIV期,第655~660页。之后,F.萨拉赞(F.Sarasin)也发表文章支持库克的意见。
[13]A.C.哈登:《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伦敦1898年版,第277页。
[14]转引自W.J.索勒斯:《古代狩猎者及其现代的代表》,纽约1924年版,第291页。
[15]爱德华·皮耶特:《马斯·德阿齐尔洞穴的画卵石》(Les Galets colories du Mas d'Azil),载《人类学》(L'Anthr)杂志,1895年,第vi卷,第276页。
[16]H.林·罗思(H.Ling Roth):《塔斯马尼亚洞穴栖居地和土著居民》(Cave shelt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Tasmania),载《自然》杂志,1899年,第IX期,第545页。
[17]参见杰拉德·戴蒙德:《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中译本,2004年版,第294页。
[18]B.斯潘塞和F.J.吉伦:《澳洲中部的北方土著部族》,1904年版,第308~309页。
[19]R.布里福(R.Briffault):《圣母们》(The Mothers),纽约1931年版,第2卷,第471页。
[20]赫尔穆特·彼得里:《澳大利亚西北部土著关于冥世的看法》(Sterbende welt in nordwest-Australien),不伦瑞克1954年版,第258页。
[21]保罗G.巴恩和让·韦尔蒂:《冰河时代的形象》,纽约1989年版,第28页。
[22]R.爱德华兹:《澳大利亚南部和中部岩雕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rock engravings in South and Central Australia),载《南澳皇家学会记录》(Royal Society of South Australia,Transactions),第90卷,第33~38页。
[23]玛格丽特·格罗夫(Margaret Grove):《布满岩画的大地》,载美国《考古学》杂志2002年,第9/10月合刊,第36~39页。
[24]C.芒福德:《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的艺术家》(The Artist in Australian Society),载玛丽安W.史密斯(Marian W.Smith)编:《部落社会中的艺术家》(The Artist in Tribal Society),纽约1961年版,第7~8页。
[25]F.D.麦卡锡(F.D.McCarthy):《土著的过去:考古学和物质装备》(The Aboriginal Past:Archaeology and Material Equipment),载R.M.伯恩特(R.M.Berndt)和C.H.伯恩特(C.H.Berndt)编:《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Aboriginal Man in Australia),伦敦1965年版,第90页。
[26]F.D.麦卡锡:《格罗特·埃兰特和卡瑟姆岛的洞穴岩画》(The Cave Painting of Groote Eylandt and Chasm Island),载《美国和澳大利亚对阿纳姆地科学考察记录》(Records of the American-Australian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Armhem Land),第2编,伦敦1960年版,第389页。
[27]F.D.麦卡锡:《格罗特·埃兰特和卡瑟姆岛的洞穴岩画》,载《美国和澳大利亚对阿纳姆地科学考察记录》,第2编,伦敦1960年版,第147页。
[28]载美国《考古学》杂志,1991年11/12月合刊。
[29]这幅插图中的中国岩画形象采自盖山林:《中国岩画学》,1995年版,第166页。盖山林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巫师的形象。
[30]C.斯特雷洛:《澳洲中部的阿兰达人和洛里查部族》(Die Aranda und Loritja-Stamme in zentral-Australien),1910年版,第2卷,第12页。
[31]H.格罗格尔—武尔姆:《土著居民树皮画中的图式化》(Schematisation in Aboriginal bark paintings)。载彼得J.尤柯编:《土生土长艺术中的形式》,新泽西1977年版,第155页。参见A.P.埃尔金:《如何去理解澳大利亚土著居民》(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how to understand them),1954年版。
[32]E.亚当森·霍贝尔:《人类学:人的研究》,明尼苏达大学1972年版,第627页。(www.zuozong.com)
[33]戴尔·布朗主编:《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中译本,2002年版,第190页。
[34]参见斯宾塞·韦尔斯:《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中译本,2004年版,第111~112页。
[35]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裸人》,中译本,2007年版,序。
[36]M.梅斯马谢尔(M.Messmacher):《墨西哥的旧石器时代艺术》(EI arte paleolitico en México),载《旧石器时代的艺术》(Arte Paleolitico),墨西哥UISPP编,1981年第XI期,第82~110页。
[37]N.吉东(N.Guidon)和G.德利布拉斯(G.Delibrias):《对32000年前美洲人的碳14断代》(Carbon-14dates point to man in the American 32,000years ago),载《自然》(Nature),1986年,总第321期,第769~771页。
[38]D.S.惠特尼(D.S.Whinty)和R.I.多恩(R.I.Dorn):《加利福尼亚东部岩画的年代》(Rock art chronology in eastern California),载《世界初始》(World Arch),1987年,第2期,第150~164页。
[39]罗伯特F.海泽和马丁A.鲍姆霍夫(Martin A.Baumhoff):《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东部的史前岩画艺术》(Prehistoric Rock Art of Nevada and Eastern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大学1962年版,序言。
[40]保罗G.巴恩:《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中译本,2002年版,第233页。
[41]这两幅插图均采自罗伯特F.海泽和马丁A.鲍姆霍夫:《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东部的史前岩画艺术》,加利福尼亚大学1962年版,第133、361页。
[42]插图采自保罗G.巴恩主编:《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中译本,2002年版,第233页。
[43]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猞猁的故事》,中译本,2006年版,第207页。
[4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裸人》,中译本,2007年版,序。
[45]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纽约1975年版,第110页。
[46]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裸人》,中译本,2007年版,第127~128页。在《结构人类学》的开头,斯特劳斯也采用了这幅海达人的鲨鱼形象作为插图。
[47]西奥多·科赫—格林贝格(Thodor Koch-Grunberg):《奥里诺科河的罗罗人》(Vom Roroima zum Orinoco),第6章第1节。
[48]欧内斯特·威廉·霍克斯(Ernest William Hawkes):《拉布拉多爱斯基摩人》(The Labrador Eskimo),载《加拿大研究报告的地质鉴定》,渥太华1916年版,第91期,第82页。
[49]莱昂哈达·舒尔茨—詹纳(Leonhard Schultze-jena):《危地马拉基切人的生活、信仰和语言》(Leben,Glaube und Sprache der Quiche von Guatemala),耶拿1933年版,第20页。
[50]W.J.索勒斯:《古代狩猎者及其现代的代表》,纽约1924年版,第420~421页。
[51]玛丽C.惠尔赖特(Mary C.Wheelwright)编:《纳瓦霍人宗教丛书》(Navajo Religion Series),第1卷,圣菲1942年版,第19页。
[52]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纽约1975年版,第323页;此外,E.亚当森·霍贝尔:《人类学:人的研究》,明尼苏达大学1972年版,第545页中也有一幅纳瓦霍人画沙画的照片。
[53]米尔恰·埃利亚代:《宇宙和历史:周而复始的神话》,纽约1959年版,第83~84页。
[5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中译本,2006年版,第2卷,第728~729页。
[55]保罗G.巴恩:《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中译本,2002年版,第236、237页。
[56]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纽约1975年版,第27页。
[57]参见戴尔·布朗主编:《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中译本,2002年版,第26页。
[58]J.A.豪斯顿:《爱斯基摩人的雕刻》,载加拿大大使馆编:《加拿大爱斯基摩人的艺术》。
[59]罗伯特·麦吉:《爱斯基摩人文化传统中不同的艺术创造性》(Differential Artistic Productivity in the Eskimo Cultural Tradition),载《现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1976年第17卷,第2期,第203~220页。
[60]盖尔·勒特曼(Gail Luttmann)和里克·勒特曼(Rick Luttmann):《爱斯基摩人的舞蹈美学:一种方法论的比较》(Aesthetics of Eskimo Dance:A Comparison Methodology),载贝蒂·特鲁·琼斯(Betty True Jones)编:《作为文化遗产的舞蹈》(Dance as Cultural Heritage),1985年版,第2卷,第53~61页。
[61]参见纳尔逊H.H.格拉伯恩(Nelson H.H.Graburn):《爱斯基摩人和“机场艺术”》(The Eskimo and‘Airport Art'),载《Trans-Action》,1967年第4卷,第10期,第28~33页。
[62]爱德蒙·卡彭特:《爱斯基摩人的艺术家》(The Eskimo Artist),载夏洛特M.奥滕编:《人类学与艺术》,纽约1971年版,第165页。
[63]爱德蒙·卡彭特:《爱斯基摩人的艺术家》,载夏洛特M.奥滕编:《人类学与艺术》,纽约1971年版,第32页。
[6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中译本,2006年版,第2卷,第832页。
[65]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中译本,2006年版,第1卷,第265、283页。
[66]托尔·海尔达尔:《复活节岛的秘密》中译本,2005年版,第2页。
[67]托尔·海尔达尔:《复活节岛的秘密》中译本,2005年版,第103页。
[68]托尔·海尔达尔:《复活节岛的秘密》中译本,2005年版,第104~105页。
[69]托尔·海尔达尔:《复活节岛的秘密》中译本,2005年版,第140页。
[70]托尔·海尔达尔:《复活节岛的秘密》中译本,2005年版,第147页。
[71]托尔·海尔达尔:《复活节岛的秘密》中译本,2005年版,第160页。
[72]托尔·海尔达尔:《复活节岛的秘密》中译本,2005年版,第171~172页。
[73]托尔·海尔达尔:《复活节岛的秘密》中译本,2005年版,第180页。
[74]埃杰顿·赛克斯:《非古典神话词典》,伦敦1974年版,第6页。
[75]托尔·海尔达尔:《Aku-Aku复活节岛的秘密》(Aku-Aku,The secret of Easter Island),鹈鹕丛书,1965年版,第56页。
[76]托尔·海尔达尔:《Aku-Aku复活节岛的秘密》,鹈鹕丛书,1965年版,第96页。
[77]托尔·海尔达尔:《Aku-Aku复活节岛的秘密》,鹈鹕丛书,1965年版,第97页。
[78]托尔·海尔达尔:《Aku-Aku复活节岛的秘密》,鹈鹕丛书,1965年版,第202页。
[79]保罗G.巴恩编:《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中译本,2002年版,第221~222页。
[80]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中译本,2005年版,第19页。
[81]F.奥托·博尔诺(F.Otto Bollnow):《论敬畏》(Die Ehrfurcht),法兰克福1947年版。
[82]罗素:《宗教与科学》,中译本,1982年版,第11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