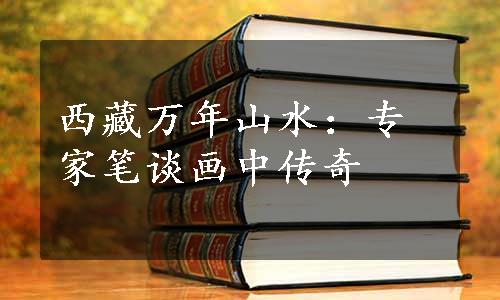
王修功
由阅读《文星》118期,刘国松:《西藏的画中传奇——刘万年》一文,而去“三原色艺术中心”看了刘万年的画展。
这是“三原色”自成立以来,所举办一系列大陆画家展的第五档。在第一档的综合性“大陆水墨画展”中的画,因可能不是参展者的代表作品,看来并无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一般说来,绘画的技巧,多相当稳练,也不乏表达现实题材的作品,可是总不及想象中的那么好。所以以后的几档展览,也再没有兴致去看。
然而刘万年的画,却给予我很深的感动。无论构图、章法、笔墨的表达技巧,不但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截然不同,与我所看到的现代一些海峡两岸的水墨画家作品,也不相类。一向没有余钱买画的我,一时为之心动,而忍不住买下一幅。
不仅如此,在画展已结束的第二天,我的陶作经纪人洪东明先生,突然来访,谈话间,向我问起当前台湾水墨画的情形,无意中便把话题引到刘万年的画展上去。洪君在看过刘画的印刷册子后,便约我立即到“三原色”去看看。
那时,“三原色”正在换档,刘万年的画已撤下放在墙角。洪君与他一同去的一位绘画略有认识的朋友,一看之下,也颇为心动,认为与一般所常见的画,大不相同。遂一时“心血来潮”,居然把还没有售出的25幅(画展中只售出8幅),统统买下。
这件事,对我个人,对不是收藏家、也不怎么懂画的洪东明先生,及画廊本身而言,莫不感到意外。我想乃至画展引介人刘国松,尤其是远在数千里外,西藏高原的画家本人——刘万年,获悉他的画作,在台湾首展,在如此玄妙的情况下售出,当更感到意外中的意外。
刘国松这半年来,在《文星》上所介绍的大陆画家,几乎都不是大陆艺坛赫赫有名之士,而是刘国松心目中认为具有独特风格而画龄相当年轻的一辈。这种不受世俗名声的影响,这种只“认画不认人”的做法,尤其《文星》每期以十多页的宝贵篇幅,为不怎么出道的绘画新锐,刊登彩色图文,大力来支持,都大大地值得喝彩!
一个远处中国大陆边陲的西藏画家,若不是刘国松远去西藏旅游,有机缘看到刘万年的画作,又大力为其著文推介,在台湾不可能知道刘万年这个人。据“三原色”的李锡奇说,大陆知名画家,透过各种中介方式,要求在其画廊展出者,大有人在。若不是刘国松的引介,尤其是刘万年的画果真特殊,他的画,怎么也不会这样快地在台展出。
我的另一种看法是,以刘万年远居西藏,可能参与大陆全国性区域性美展的机会都不大,这也就是他的画尚不为大陆画坛所熟知的原因所在。而以他的杰出绘画成就,假如他人在北京,或大陆其他著名城市,刘万年的画,可以说早就该驰名大陆的大江南北了。但反过来说,若刘万年身属大陆一个很著名的热闹城市,则必然不能画出像西藏那样巍奇的山水来。当然他也可以画别的地方的山水,而未必有现在他画中那种浑厚的气势。再深一层来说,他所处的环境,未必允许他从事绘画创作,都不无可能。真是造化弄人,而人也升沉于造化之中!
由于除了刘国松文中所能看到的一些刘万年画作之外,一时之间难以取得其他可能参阅的资料。所以这里对刘画无法作较高层次的学理分析与批判,而只能依据刘文对刘万年的展出作品,作一概略的探讨。
艺术创作,固需强烈的主观性,艺术欣赏,自也极难客观。写这篇文章,则不免惶恐,但心诚无私。如有冒犯,乞勿介意。
刘万年童年苦难岁月,给他的磨炼,对他日后的奋斗成长,必然产生巨大的力量。
刘万年在幼小时,就喜欢画画,但一直没有人正式教过他。当他从家乡秦安四中毕业之前,在课余,《芥子园画传》是他的启蒙老师,也给他绘画奠下扎实根基,对他以后的水墨创作,最具关键性的老师。
我们不可忽视《芥子园》这部流传已久的传统画册。就是一个研习传统国画的人来说,如能慧心地、有步骤地下点功夫去学习,它真比一些蹩脚的美术教本,一个不怎么高明的绘画老师,要强很多。
我们虽不能从刘万年的画上看到《芥子园》翻版的影子,就以为它对刘的水墨画,未产生明显的作用。我们可以说,《芥子园》这个老师,已消化在他的心中,而不是掌握在他的手上。
刘万年以一个只有中学程度的青年,除了做短工、画画之外,还曾写过两篇小说。可见他平日一定读过不少书,有相当的文学修养。虽然他的画并不是在诉说故事,阐明什么大道理,但人文素养,有助于他绘画格调的提升,则毋庸置疑。
欠缺广阔的人文素养,想把绘画,尤其是中国的水墨画,画好、画出高的品位来,真是难乎其难矣!很多画者所以越画越俗,越画越匠,与其平日不读书,欠缺书卷气,有很大的关系。
就中国绘画而言,传统有其优秀的一面,也有其腐朽的一面。能掌握、能传承、能活学活用其优秀部分——如对前人的绘画理论与技巧,透过相当的主观思维,作创造性的承续和发展,传统即可历久弥新。否则,不假思索、不予取舍地死抱定一个特定的对象不放——亦步亦趋地依照前人的笔情墨趣,其所下的功夫再大,则其迷失的程度也越深,乃至难以自拔。这样的所谓“今之古人”,在此时此地,颇不乏人。中国的水墨画,到了这步田地,怎么也“新”不起来,也“现代”不起来。
反之,对传统一味地排斥,想凭空造个金字塔,也同样地幼稚。
任何人不能自外于传统,尤其是学中国画的人,如何从浩瀚的传统中,分辨其优劣,如何把握“承”与“拒”的分寸,就要依赖很高的智慧了。
刘万年到西藏后,曾学过水彩,也学过油画(其学习环境,一定比这里差),无疑水彩画的水分运作,油画的色、质感,都有助于他水墨画的抒情手段。但他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画。这种中国画,是中国的,而不是陈腐的“古”中国,是“现代”中国,而不是现代的、混杂的“仿冒”品。
有人说,怎么画比画什么,往往来得艰难;也有人以为,画什么比怎么画,更为不易。其实各有所偏,而两者都很重要。(www.zuozong.com)
很多从事中国画的人都知道,“黄山”是个上好的题材,自古至今,画过的人不知几何。而把“黄山”画得好,给我们印象很深的,则并不多见。也许由于太偏远的因素,在中国的山水画里,“西藏”的山,根本没有地位,但刘万年的画,却给予我们很深的感动。西藏的高山固然荒寒而巍奇,假若是让一个画什么都是那一套的庸俗画者去画,其结果可想而知。
现在有些从事艺术的人真是聪明绝顶。只拣现成的,而不肯下真功夫,在过分依赖现代资讯的结果下,既懒得动手,也懒得动脑,相形之下,以致虚弱的,正如一位作家很传神的形容:纽约、巴黎闹感冒,我们这里就跟着打喷嚏。于是拼凑、装置等玩具材料把戏之类的仿冒品,很快便应时而兴。可以说,我们在经济上尚没有迈向所谓“自由化”“国际化”之前,而我们的文化艺术,早就“国际化”了。
可是,从事水墨画者,就没有这种幸运,除了必要的画法,绘画的基本功夫之外,更需要广博的知识、进步的思想等深厚的人文素养,这都不是三年五载可见其功的。
当前中国的水墨画,海峡两岸都有它面临的困境。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又写小说的李渝女士,虽身在美国,而“放眼中国”。她对海峡两岸写意画的现况,有很不保留的指责。
她在《诚意山水,情意山水》(1976年9月《中国时报》——《人间》与《雄狮美术》第200期月刊)——评析余承作品一文里,对中国写意画,有下面一段相当尖锐的评论:“……‘写意’并非乍看之下的那样轻松愉快;在宏观世界挥洒有形的东西,其实暗藏着长时间辛苦而精密的训练,而且若要达到出人头地的层次,更非得陶练出不凡的人格不可,这种种局限和要求都是使‘写意’在当下成为艰难的画法。但是我们的写意画家,似乎并不重视这层层困难,往往提起笔、蘸满了墨水,在训练和修养两者皆缺失的情形下,就即席挥动了起来。大陆的《新人文画》、台湾的一些狂笔人物、花鸟山水,乍看意气风发,水墨淋漓,再看却是没有一笔实质的,没有一笔落实下来,透进了画里。展现出来的那一片空虚架势,简直要我们怀疑,是不是还有画‘写意’的必要来。”
在另一篇《童年和童年的失落》(《当代》第4期)一文里,李渝更沉痛地剖析文学与艺术的病态之后,又说:“……也许画家李可染是例外。”
李渝女士的观点,固很严苛,相信许多水墨画家看了,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但也很值得深思。
李渝所说的“即席挥动”,也常见于我们这里的公众场合。有些美术机构,也许为了促使美术活动产生社会教育的功能,每每在特别的节日邀请一些知名的水墨画家,担任一种助兴的表演角色,而艺术已技术化者,稠人广众之前扬扬得意,摇头晃脑弄一番墨,点几个点,画几条线,于是乎一只雉、一对虾、一棵树便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则拍手叫好,画者、主办者也莫不皆大欢喜。但也有无可奈何的一面,因而发出“还我艺术本来心,莫做擂台竞技人”的浩叹!
刘万年于1979年,在四川美术学院进修的期间,看到了石鲁的作品,而彻底影响了他的画风。因而我不得不在此简单地谈一下石鲁这个人。
石鲁,四川人,早年以一支充满热血的画笔,为中共挎刀效命。其人才高个性强,对书法、金石,极富现实意义的水墨画,都有独特的成就。为大陆所谓“长安画派”中的佼佼者。“文革”时,因歌颂毛的一幅画,所引发的不同解释,受到迫害,以颇为戏剧性的真疯?还是假疯?而幸免一死。但也终因饱经折磨,身心俱碎,1982年死于西安。
石鲁的画,对中国大陆大江南北的画风,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但我却很喜欢那种画风,尤其是那画面所呈现的“火燥”气氛。这个“火燥”味,似与李渝所感觉的那种不“落实”、没有“实质”的“意气风发”的评断相近。
石鲁画里的“火气”,与潘天寿作品中那种磅礴耐看的“一味霸悍”(潘天寿自篆的一颗印章)不同。
石鲁山水画里,偶尔一些强调运用较柔细线的皴法,看来很受黄宾虹的影响。而黄宾虹画里的那种沉郁、浓厚、苍横而优游自如的线条,交织成近乎半抽象意味的气氛,在石鲁的画里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刘万年山水画里有些峰面,多少受到石鲁一些“章法”的影响,但却没有一丝石鲁那样的“火气”。
刘万年“为了使山厚实,故要把画面塞满!让观众有压抑,喘不过气之感。我们站在一座大山下,就像站在一位伟人前面的感觉才对”(引自刘国松的文章中刘万年的话)。这是何等的豪语,又是何等的气势,难怪在他的画里,看不到我们在这里所常见的软绵绵的停云、松塌的瀑布等一类的调调。
他的一幅题名《福地》的连作大画,整个以坚实如木刻般的线条,织成一绵延起伏的山景,传以厚重近乎油画质感的暗朱红色,气势真是壮阔极了。这样的红色调,间而在石鲁的画面出现过,但那也只是局部而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画风虽然深受石鲁的影响,但其笔触,没有石鲁那样放,那样狂——那样的“火”味。平心而论,他比石鲁要“理性”得多,据“三原色”的徐术修称,有位参观者认为,刘万年是以一种近乎宗教的虔敬心情去创作,似与我这里所指陈的“理性”不谋而合。也有人说,那是真正阳光下的作品,自然与我们这里冷气房里的水墨画,大不相同。
刘万年对于景物的取舍,运用不同的笔墨技巧,而塑造成不同的意境。这一切很显然地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实地观察与探索所体验的结果。没有一般画者近乎公式化的“陈腔滥调”。所以他的每一幅画,几乎都给人一种很新的意境,明显而强烈地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画路。
刘万年虽受到大陆“长安画派”,尤其是石鲁——探索再探索的启示,他以水墨而论并不局限于水墨——尝试以水墨外的其它工具材料与技巧,表现出西藏山峦“干裂荒枯”的独特风貌,为现代中国水墨画开创了新的风格与新的发展途径,很值得喝彩。
载1988年4月台湾《文星》第120期
(作者:台湾著名陶艺家)
雪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