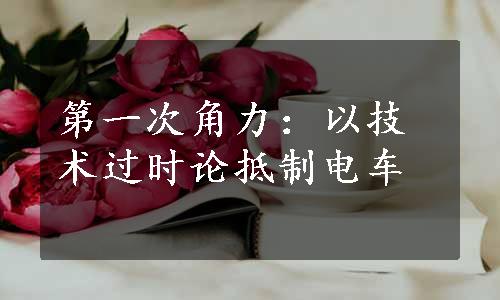
不难发现,“中国若汽车工业不能建立,建国大业就缺少了一环”,即“汽车事业振兴之国家,其市政必先之改善,易而言之,即市政改善之机会,汽车兴之也”。具如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第五计划”第四部“行动工业”中提出建立中国汽车工业的宏图远志:“自动车为近时所发明,乃急速行动所必要,吾济欲行动必要,必先建造大路(公路)……中国人民既决定建造大路,国际发展机关,即可设立制造自动车(汽车)之工场;最初用小规模,后乃逐渐扩张,以供给四万万人之需要。所造之车,当合于各种用途,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此一切车以大规模制造,实可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自动车(汽车)之工场,此一切车以大规模制造,实可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除供给廉价车之外,尚须供给廉价燃料。否则人民不能用之”。再如定都前,时人就提出南京“其注重之点,首在扩充路线,而以汽车道路为发轫之始。此次规划路线自宜大展规模,断不能草率从事。旧有道路,务须亟行修治,以便汽车之通行。歪斜者宜左右展宽,便汽车之旋转,新开汽车路,当分干线支线。干线为各项车辆行驶所必经,务须格外宽阔(宽度在四丈内外);支线则取交通便利之地,其路线之指定当分城内与城外分办”。进一步提出,“电车费用浩繁,事不易举,而长途汽车之创设,乃为南京目下且要之图,此殆无可讳言者”;且“宁垣街道窄而不阔,电车之建筑不宜。汽车左右灵便占地甚少且建设简易,经济已少困难”。
定都后,《首都计划》指出,南京“附近各市,现方积极开辟公路,将来需用汽车至多,宜于开设汽车配制厂”。而自江南汽车公司独营全市公共汽车业后,引起“建设银公司”觊觎,该公司由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主持,因见南京市面逐渐繁荣,想办首都电车。此意传至南京市府后,因有些嫉妒江南,就把此消息传给公司,其对此不便表态,只得忍耐。1936年,江南公司业务趋于稳定,经理吴琢之已为公路运输专家,还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交通人员训练所”教员。是年夏,吴“奉政府命赴欧美考察工业建设,历时半载,对于交通政策及管理,注意尤为周至”,翌年2月回国。考察期间,吴氏途径罗马、柏林、巴黎、伦敦、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及汽车制造集中地底特律城。每至一城市,参观汽车厂时,他都注意工厂的设备和管理制度,并关注自动化的流水作业及控制工人的劳动方法等。之后,其就“考察各国首都时,世界各国大都市之公共交通工具,最近十数年来之趋势所见”做出总结:“譬如现在欧美之都市,不惜牺牲已废弃固有的地面电车,而用公共汽车矣”。即国外五大都市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内之交通工具,“莫不具同一之趋势。即地面的有轨与无轨电车,群众均毅然决然拆除废弃另起炉灶,代之以公共汽车”。而当时南京作为“今日之首都,欲选择合理之交通工具,从国防言、从交通言、从建设言、从经济言,如经济能力足以负担巨额设备费者,则以地道电车为宜;倘使经济力量不充,则以公共汽车为最合理。故应分缓急先后而定步骤,现在则尽量用公共汽车以应需要,同时准备地道电车以利将来。庶几一旦财力充盈,群众需要地道电车时,然后着手构建”。
由是,吴氏在分析其时电车业务日渐衰落和公共汽车的优势后,认为公共汽车是当前最新的交通工具,南京今后市政要发达,只能发展它;或也只能仿照美国纽约的地道电车(地铁),绝不能再开倒车行驶地面电车。其观点论证有力、言之凿凿,在同《朝报》记者的谈话中也提出如此建议。因而,有纽约、伦敦及柏林等都市事实的佐证,加上以当时南京财政状况而言,建设地道电车不符实际和财力,由此就使得许多迷信欧美的建设银公司经理人思想开始动摇,宋子良也觉电车事业落伍,打消此意。
与此同时,一些市政专家亦表支持。如沙公超指出,因开行电车存在资金投入大、技术要求高等特征,至1926年“吾国商埠中之有电车设备者,仅上海、香港、天津、大连、抚顺及北京,合计不过六处”。再如董修甲论及,“在公共汽车未发明以前,电车为都市最敏捷之交通利器,但自其发明后,电车竟成过渡之交通器具矣。故现在欧美各都市,以公共汽车代电车者日见加多。查电车须有电厂,如系有轨电车更须铺设铁轨,即系无轨电车,其电线之设备至不可少,其开办与设备费均极浩大,非资本雄厚者不能创办也。至公共汽车不须极大之经费,况公共汽车既无铁轨与电线之设备,是遇必需更改路线时,尽可出一公告,即可将路线变更之,非如电车既须迁移其路轨,复须更动其电线,其损失之大不可以道里计”。从而,“宜乎各都市,均以公共汽车代电车也”。(www.zuozong.com)
事实上,其时自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公路处专管公路建设和汽车运输后,公路发展较快。除制定规章外,实行国道由中央统一规划、修建和管理,其他路线由各省市负责。到1936年年底共新建京杭、沪杭等公路8 .65万公里,全国通车里程增加到11 .57万公里。民用汽车也发展到6 .89万辆(未含日伪占领区),其中有私营汽车1 .77万辆,官办营运汽车2900多辆,其余均为机关、工厂和私人的自备车辆。再据当时《交通概况》及《统计年鉴》显示,1933年中国关内有公路63406公里、登记汽车32283辆,内公路汽车5214辆、营业收入3479万元。抗战前夕,关内有公路10.95万公里、登记汽车58344辆,分别为1933年的173%和181%;1936年公路汽车营业收入为6158万元。并且,1927—1936年全国石油进口量由1300万加仑增至4600万加仑,客货汽车平均每年进口四五千辆。按车辆登记数字,1927年客车16020辆、卡车1901辆、公共汽车1015辆;1936年客车27465辆、卡车11917辆、公共汽车8060辆(军车除外)。除军车外,公路运输主要是客运,货车只占车辆总数25%,拥有货运汽车100辆以上的省市不到半数。1927—1936年我国公路汽车的客车增长71%、卡车增长527%、公共汽车增长693 %。(见表9-1)彼时美国汽车工业每年可制造小汽车350万辆、运货汽车100万辆,有汽车业技术工人100万名,“这是个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工业”。由此,时人论道,“我们希望人们对于兴筑公路与兴筑铁路一样的积极,并望加快筹备汽车工业之自主,以迎接抗战胜利之来临”。基于上述历史潮流,在南京公共汽车与电车的角力中,前者即以胜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