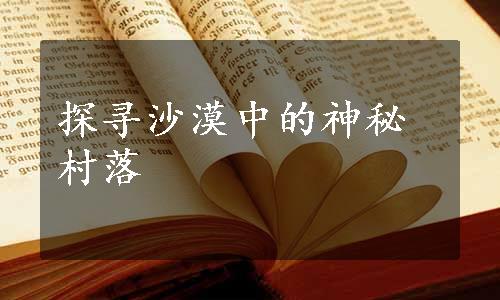
沙漠在我眼前闪闪发光,显得好不真实。这几天来,我造访了亚历山大和开罗的香料市场,现在正与戴夫·丹尼(Dave Denny)神父及两名开罗的驾驶窝在老旧的福斯小巴里,穿越西奈半岛。每年到了这个时节,西奈半岛总是炎热、干燥、荒芜,很难见到一朵云或一辆拖车。我望向窗外,接连几个小时只看到石漠、砾漠与石灰岩山脊边缘的低地,每块石头在沙漠的烈日下都黑得发亮。四周亮晃晃的石头又把太阳的热气反射回来。前方道路突然看起来湿漉漉的,那水潭是海市蜃楼。我们一靠近,便明白潭中根本没有聚积近来的降雨,而是从加萨古老矿脉运来的乌黑沥青。
小巴一路颠簸,我设法将一本没有封面、早已绝版的英国旅游书念给老友戴夫听。上面写着考古学家如何从埃及发现的石棺,解读2300年前关于香料交易的铭文。这份铭文详细描述了迈因商人诉说的一条商路,而这条路和我们走得差不多,只是方向相反。商人从阿拉伯半岛南边带了香水与香料,供知名的埃及神庙使用。
后来,希腊罗得岛历史学家凯利克森努斯[1]曾写道,他见过商队前往半岛以外,为货物寻找更好的价格:“300头阿拉伯绵羊与骆驼大步往前,有些扛着300磅乳香、300磅没药,尚有200磅番红花、肉桂、鸢尾根(orris)与其他香料。”
我的视线从书上移到窗外,恰好看见几个贝都因人骑骆驼前往红海海岸。不久,我眺望到海岸边的沙滩与珊瑚礁,望向阿卡巴湾(Gulf of Aqaba),以及更远的阿拉伯半岛的西北边缘。彼岸低矮的山丘似乎在热气中摇晃扭动。我所在的这条公路与海岸平行,有时离海域近一点,有时比较远,就这样又走了一个小时。我搭没空调的小巴已觉得路途艰辛,那些骑骆驼、直接曝晒于沙漠烈日下的人又作何感想?
不过,公元前1000年后的几个世纪以来,迈因商队就带着乳香、没药与香料沿着这条路,从阿拉伯福地的哈德拉毛往北前进,穿过阿拉伯沙漠到阿卡巴湾,再往北到佩特拉与加萨,或穿过西奈半岛,抵达尼罗河。有些商队有幸躲过掠劫(ghazw)──贫穷的游牧民族掠夺较富有部落的食物与其他资源,使财富重新分配。若迈因人远征顺利,货物大概可送到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甚至尼罗河另一边的亚历山大与吉萨(今天的开罗附近)。不过,如果当地游牧民族碰上干旱或瘟疫,无法饲养牲口或在野外取得食物时,就会偷偷接近香料商人。迈因人为了避免商队完全失去财物,经常宁愿贿赂或支付保护费给贫穷的游牧民族,以求平安通过他们的地盘。
我向来佩服史前商人的毅力与睿智,更佩服他们的勇气。光想到穿越辽阔沙漠的过程多么艰险,就让我裹足不前。要能承受这趟旅程,必然要秉持某种态度──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探险家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 1805—1852)便如实反映出这种心态。他在贝都因人的陪伴之下从红海前往佩特拉,之后他写道:“这天我们顺利度过,周围的景色一成不变:前面是黄沙滚滚的荒凉谷地,两边则是更荒凉的山。到了傍晚扎营时,我和同伴们在营火边坐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回到帐篷(睡觉)。”
小巴开到西奈高速公路的荒凉之处时,轮胎没气了,于是我们到休息站停留半小时。我无事可做,便开始思考坚毅不拔的迈因商人产生的广大影响──他们比斯蒂芬斯的年代还早了两三千年。在那段时间,迈因人的贸易文化蓬勃发展,使者曾前往希腊提洛岛(Delos)、亚历山大、帕迈拉(Palmyra)绿洲及迦勒底(Chaldea)聚落,甚至远达今天印度海岸的古老港口克拉拉普特拉(Keralaputra)。他们在阿拉伯沙漠维持了一连串的绿洲商栈,包括奈季兰(Najran)与提姆纳(Timna)。但是在称霸香料交易数个世纪之后,迈因人在掌控进出阿拉伯福地的香料、熏香、染料与矿物时出现颓势。势力衰微的原因,可能是贿赂金与保护费太重。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也很可能导致迈因人荣景不再:竞争者已学会如何从西边的红海与东边的阿拉伯海乘船到南方的亚丁港,如此即可避开沙漠的掠夺者。最后,迈因人失去了竞争优势与利益基础。到了100年,闪语系中迈因人独有的迈达比克语(Madhabic tongue)已不再是全球贸易的通用语言,如今更是已经失传。
司机发动福斯小巴的引擎声将我从思绪中拉回现实。虽然轮胎胎纹几乎磨光,但已充足气,老爷车继续一拐一拐,往埃及最东边的红海度假小镇塔巴(Taba)前进。车停下来之后,我给了两名埃及司机几镑,他们马上驾车往西返,连新轮胎或食物都没买,只急忙往开罗与舒适的尼罗河前进。
戴夫神父与我分别住在一个简朴旅馆的两个房间里。旅馆濒临海岸线,我偷闲泡泡阿卡巴湾超咸的海水。日落前一个小时,暑气逐渐消退。我们离开海滩,从公路回到侧边峡谷的阴影时,遇见了四五十个塔拉宾部落(Tarabin)的贝都因人扎营,他们从附近的努威巴镇(Nuweiba)来到这儿。
这群贝都因人在帐篷与围栏旁搭盖了临时遮蔽处与储藏小屋,建材看起来相当残破,是靠着打劫、回收,或是在这个度假小镇大道旁的旅馆工地捡来的。两个贝都因男孩与一个女孩刚把努比亚山羊与尾巴蓬松的绵羊赶进围栏过夜,看见我便打招呼。
孩子们安顿好绵羊与山羊之后,便领我到父母扎营处。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位老先生热情迎接,他们在石头地面铺上地毯,请我们坐下。一旁有个小柴炉在煮水。他们煮了些薄荷茶(shai nana'a),给我们一杯,也帮自己倒了些。我们啜饮时,孩子们在身边游戏。离开营地时,老人家送给我一个砂岩,上头刻着有斑纹的猎狗吃掉一个不幸旅人的头。我默默接受礼物,给他几块钱与几条变形虫大方巾当作回礼。
我们在天黑之前回到旅馆,发现此处能看见海湾对面的灯光──那是以色列埃拉特(Eilat),紧邻其右的是约旦阿卡巴。今天度假胜地塔巴的灯光照亮了北边的地平线,但在以前,海岸边是许多古老港口。来自印度的货物在此上岸,改由骆驼商队转运到沙漠。
我也看得见对岸属于沙特阿拉伯的海岸。我所在的位置不错,能看到如今分属于4个国家的红海北岸。2000年前,这里都属于某群香料商人的传奇国度,这些沙漠国家没有固定边界,犹太历史学家提图斯·弗拉维奥·约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 37—100)称之为纳巴泰(Nabatene)王国。这里的纳巴图(Nabatu)商人定期从马格里布前往罗马,而我们称之为纳巴泰人。
西奈半岛零星出没的塔拉宾贝都因人,恰好呼应着我对古纳巴泰人的少许认知。虽然在公元前4世纪的考古学记录中,即证实了纳巴泰人的存在,但这群游牧民族的宗族很小,至少要等几百年后,才较常出现在书面记录中。公元前312年,历史学家卡迪亚的希洛尼摩斯(Hieronymus of Cardia)记录了他观察到的纳巴泰人。他看见这群人在寸草不生的死海边缘附近做沥青挖掘的苦工。接着,他们尽量让骆驼多扛点沥青,然后跨越沙漠前往埃及城市,想用沥青换取在尼罗河冲积平原的沃土上种植的食物。
那个年代的纳巴泰人禁止自家人种植作物,据说他们痛恨投入畜牧以外的任何农业形态。不过,他们还是得吃,因此会多采用交换的方式,例如以羊皮或野生药用植物换取粮食。到了公元前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阿伽撒尔基德斯(Agatharchides,约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指出,纳巴泰人口增加,僧多粥少的情况愈发严重,进而陷入贫困,于是他们开始抢劫,对象从跨越沙漠的商队,转变成另一种商队──海上船队。基本上,纳巴泰人离开沙漠,成为在整个阿卡巴湾抢夺帆船的海盗,尤其喜欢突袭不幸的埃及水手。
早期过着游牧生活的纳巴泰突击者,人数超过万名。他们掠夺海湾上的船只或沿岸的商队,却不自行发展农业或建造固定的住所,因此在红海恶名昭彰。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时候的纳巴泰人多数是纳巴图家族的后代,是阿拉伯福地最早成名的闪族部落。这支部族在资源稀少的情况下撑过好几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变得越来越精实。
不过,他们赚了点钱之后,开始致力于发展能通行沙漠的新沟通方式。今天用来抄写《古兰经》的阿拉伯字母与古阿拉伯书法(Kufic),显然就是从他们装饰性强、曲线美观的书法演变而来。
有学者指出,纳巴泰维持单一种族实体的时间并不长。他们吸收了其他部落,成为有异质性的社群。他们逐渐与其他许多种族紧密交织,包括罗马、希腊、埃及与希伯来,并受其影响,具备了更广的文化与经济内涵。各种族共同创造出独特的“跨界料理”,例如哈利拉与巧巴(chorba)是很丰盛的炖菜,还有牧里酱(murrī,一种咸的发酵大麦酱)与卡麦克里加酱(kāmakh rījāl,有点酸,是味道很浓的奶酪酱,制作时要把酸奶放在开放的容器里几个星期)。
这些以阿拉米语记录的古纳巴泰食物名称,传到附近的阿拉伯与希伯来方言中,之后波斯、希腊与罗马方言也借用。久了之后,纳巴泰这个群体由包罗万象的人组成,包括说亚拉姆、希伯来与阿拉伯语的人,大伙儿成群结党,“重新分配”在亚历山大与耶路撒冷之间洗劫而来的一切。在西西里出生的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活跃于公元前60年到公元前30年)认为,纳巴泰人主要是在海上投机冒险的阿拉伯畜牧者,想抢劫战利品。
许多纳巴泰人带来在海上得到的熏香、没药与珍贵的香水,那些东西来自阿拉伯福地……这个部落占据海岸的绝大部分,占领的内陆面积也不小。他们人数众多,豢养的牲畜多得令人难以置信。过去这些阿拉伯人奉公守法,满足于豢养的动物所提供的食物。但后来,亚历山大的国王设法为商人开辟海上道路之后,这些阿拉伯人不仅攻击船只,还装备海盗船、打劫航海者……但过了几年,他们在海上遭到更大的船只袭击,终究自食恶果。
无论纳巴泰人从哪里来,总之他们渐渐从打劫转变成以贸易为生。不过,他们的贸易方式和邻人不同。他们想更系统甚至全面掌握多数从熏香生产国延伸而出的海陆贸易。他们运用长长的骆驼商队,沿着难以追踪的路线,辅以配有船桨与船帆的成熟船只进行补给,于是侵蚀了迈因人的势力,主宰了许多乳香之路。正如当代学者沃特·魏斯(Walter Weiss)观察到的,纳巴泰国度“是出奇和平的国度,只靠着贸易获利来运作,没有真正的疆界、赋税或社会动乱,也没有多少奴隶。纳巴泰人的优势在于,能持续让货物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保持距离”。
简言之,纳巴泰人成为第一个主要由中介商构成的文化族群。他们转手香料、熏香与香水,发展、维持并掌控跨大陆的交易网络。事实上,他们在乳香之路上运送的货物,几乎都来自自己的土地。他们在熏香、没药、印度香料与其他芳香物质的跨海与跨洲交易上,担任不可或缺的中间商,从而建立了生态栖位[2]。
图6:哈利拉炖菜是美味的饮食“使者”,将香料引介给波斯人、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这顿午餐是埃及锡瓦(Siwa)绿洲的柏柏尔人提供的。(图片来源:作者)
为了建立生态栖位,纳巴泰人多居住在芳香植物的采集地及目标都会市场之间的“空旷”空间。他们不必再直接依赖当地资源来辛苦过活,只要穿越沙漠或海洋的空间即可。重要的是,他们能掌握商队旅馆与其他安全港口,这样在横渡漫漫长路之时,即可把这些地方当成休息站。
魏斯说,纳巴泰人的“优势”在于能坚持让消费者与生产者无法直接接触。只要采收者不知道谁想买他们的货物,也不告诉最终使用者货物究竟从何而来,纳巴泰人就能掌握乳香价值链。纳巴泰人通过这条法则,靠香料交易大发利市,因为其他人无法得知供应链上其他环节蕴含的价值。
老普林尼提到,无论纳巴泰人是靠着骆驼商队搬运,或是由椰子树打造、搭配三角帆的独桅帆船运送,总之,熏香、香料与其他产品从阿拉伯福地到加萨的途中,价值比当初入手时上涨了百倍。
不过纳巴泰人真正的天分,在于能让熏香、香料与丝绸在抵达欧洲、非洲与小亚细亚时散发出神秘感。他们不只看重这些东西的实用价值,还为它们赋予神秘的色彩。这项策略或许是从之前的迈因人那儿学来的。纳巴泰人在推销孜然、肉桂、乳香、劳丹脂(labdanum)或没药时,并非强调这些种子、树胶、叶子与树皮的热量或杀菌价值。相反地,这些东西能卖出去,完全是靠他们的营销手法,阐述这些异国商品的神秘特色。这与今天的谷粒苋(amaranth)、初榨橄榄油、人参与神奇蘑菇的推销手法如出一辙。除了这些植物或菇菌的实用价值,他们兜售的是“安慰剂效果”,从而取得经济优势。
比方说,纳巴泰人让欧洲人相信,乳香必然昂贵,因为在采收时必须偷偷摸摸,从阿拉伯南边备受保护的树园才能采收到。希罗多德向欧洲读者解释:“乳香树周围有许多小飞蛇守护,只能用苏合香(storax,一种甜的胶状树脂)摆脱它们。因此在收集乳香时要烧苏合香……苏合香产生的烟能赶走小飞蛇。”
想想看他们说的故事多么诡异:为了享受神圣的熏香,必须先用另一种熏香驱赶邪恶之蛇,再悄悄窃取,然而那蛇原本是要保护这神圣之物!或许这传说是迈因香料商人在公元前5世纪告诉希罗多德的,而纳巴泰人确保这样的故事能在距离阿拉伯福地香料产地相当遥远的国度继续流传几个世纪。难怪纳巴泰人提到乳香产地与采收者时,也能编出同样精彩的故事。
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外来者能靠近乳香或没药产地,甚至不能靠近暂时储藏这些东西的商队旅馆。在1世纪晚期,佩特拉中心拥有世界上规模数一数二的神庙与贸易中心,但这里就实体环境而言,都隐藏在岩石中。
佩特拉贴切且具体地呈现出纳巴泰人如何运作:这座城的力量与美感,蒙着层层神秘色彩。只有抵达这座城市之后,才能一睹庐山真面目,届时心中的敬畏感油然而生。怪的是,从岩壁上开凿出的神庙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乳香或其他芳香植物的考古遗迹。或许这些东西已被悄悄送到其他地方,藏在附近狭窄的山谷中,外来军队或掠夺者根本无从找起。
几个世纪以来,纳巴泰商人把香料、染料、树胶、香膏与异国香草,卖到亚历山大、阿里什(Al'Arīsh,位于埃及西奈半岛)、加萨、耶路撒冷、巴士拉与大马士革。他们很懂与其他中间商的合作诀窍,以获得骆驼从中国载来的丝绸与姜、锡兰与印度的肉桂与胡椒、索科特拉岛的芦荟与龙血树,以及香料群岛的肉豆蔻。虽然他们未必亲自造访过所有产地,却与许多芳香植物的采收者直接交易。6个世纪以来,纳巴泰人穿越阿拉伯沙漠与海洋,将数千吨货物送到也门与阿曼以外,抵达鲁斯康(Leuce Come)与埃拉[ Aila,后来称为埃拉特(Elath、Eilat)]这两处港口。之后,珍贵的货物越过大地,送到叙利亚、迦南、埃及与更远的国度。
我原本想沿着纳巴泰人的商路,往北跨越内盖夫[3],先到耶路撒冷,之后再去大马士革。然而那时政治局势紧张,我无法轻易在这些国家进出。由于我是黎巴嫩裔美国人,而我当时使用的那本护照上,显示我曾去黎巴嫩与叙利亚探亲,导致我在以色列埃拉港入境时被海关盘问了3个小时。我的姓氏不巧和索马里的盖达组织领袖相同,这更使情况雪上加霜。海关人员说,若我之后打算前往叙利亚就不让我入境,即使我只是要去见一位刚当上修女院院长的同辈亲戚!海关说,我得先从进入以色列的同一个港口离境,然后回到埃及,之后才能前往约旦(朝佩特拉前进)。此外,如果我护照上盖有以色列的章,叙利亚就不会让我入境。听起来很可怕,于是戴夫神父与我选择最简单的方案:把重点只放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这条路,约旦与叙利亚只好留待来日再访。
但是来到以色列之后,戴夫神父与我大失所望,因为今天的埃拉特已看不到多少古代纳巴泰与罗马时代的埃拉港的痕迹。我后来请教考古植物学家彼德·沃纳克(Peter Warnock),他证实无论是纳巴泰的埃拉港,或是佩特拉这座隐秘的贸易中心,几乎都找不到商品行经此地的证据。部分原因在于,这边发现的研磨香草、香料与染料等考古资料保存得并不好,不像谷类与豆类那样相对丰富。或许很久以前,数以万吨计的熏香与香料曾通过内盖夫沙漠,但如今却没留下任何痕迹。
还有一个原因则可能是,香料货物一送到纳巴泰人的港口与商队旅馆,就得尽快转手出去。香料商人把货品留在身边太久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因为精油的芬芳程度会随着时间而递减,他们反而学到如何让货物的周转率提到最高。我在我的农场附近就看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农场邻近美国农产品最大的进口港,货物多数来自墨西哥。大批芫荽、小黄瓜、青椒与西红柿送到边界附近的中介公司,但停留不到2个小时又被送上运送货物的拖车上,继续五百到上千里的北上旅程。
我在以色列时,便不断思索这种奇怪的情况:我在沙漠中,位于史前最大的香料交易中心佩特拉与埃拉之间,却没有任何考古学或旅游指南能指出这两处有任何闻名于世的香料遗迹。古人的香料芬芳早已逸散,熏香也已化为烟雾。
既然埃拉特无可观之处,神父戴夫和我只好登上巴士前往耶路撒冷,期盼途中能一瞥古代纳巴泰人的沙漠故乡,之后到耶路撒冷旧城的市集,探究如今依然存在的香料与熏香交易。我知道纳巴泰人曾在内盖夫沙漠设置星罗棋布的水洞与驻站,就像汪洋中许多浮沉的浮标。
我从埃拉特上高速公路前往耶路撒冷,以为途中能见到纳巴泰人的遗迹,而车上会是衣着保守的哈西德犹太人(Hasidic Jew)与贝都因人。不过,车速太快,我根本没看清楚多少东西,车上还挤满被阳光晒得黝黑的青少年。他们是年轻的以色列犹太人及欧美来的“自由”犹太人,身上都是最新的海滩装扮:名牌比基尼、Speedo泳装、T恤、坦克背心,脚踩人字拖。但令我不安的并非他们的穿着,而是他们的社交行为──或是说缺乏社交行为。他们多半坐在座位上,用手机发信息给朋友,或戴耳机听音乐。
他们和世界各地诸多年轻人一样,不管到了哪里都做相同的事情,好像哪里都没去。在两小时中,我发现只有一个青少年曾瞄了一眼窗外,仿佛发现沙漠很值得一看。
我来到内盖夫沙漠,最初几个小时的经历很奇怪。眼前虽是传说中的纳巴泰王国核心,看上去却只是一望无际、从红海延伸到死海的荒凉大地。同车旅客聆听雷鬼、摇滚与嘻哈,我则凝视内盖夫沙漠,这里或许和阿曼南部的尼亚德一样干燥险恶。
除了靠着处理过的水灌溉的吉布茨(kibbutzim,以色列集体农场)与枣椰林看得见绿意,这块土地或许比后期纳巴泰人知道的还要荒凉。为了解这块沙漠在以色列度假村兴建之前的样貌,我回去翻阅斯蒂芬斯写下的日记,他是第一个从阿卡巴湾北端抵达佩特拉的美国探险家:
我站在靠近红海最北端的海岸,眼前是广袤的沙之谷。一般人若缺乏地质学的知识,看到这景象后会推测,这里以前曾是海底或河床吧!……谷地宽度从4英里到8英里不等,四面八方阴暗荒凉的高山,宛如墙包围山谷。左边是犹地亚山(Judea),右边则为西珥山(Seir)……在山的中间,外来者看不出来这里埋着王国古都,唯有四处游荡的贝都因人才知道如何前往──这就是部分已开挖出来的城市佩特拉……我眼前的大地苍凉贫瘠,山顶不见一丝绿意。目之所及了无生气,渺无人迹。
无论是骑在马背上的斯蒂芬斯,或是搭乘疾驰巴士的我,都看不出在埃拉特北边的内盖夫沙漠土地上散布着许多刻着壁画的巨岩,上头密密麻麻的疤痕写着隐藏的水乡与“水井之链”在哪里。从也门南方到黎凡特(Levant)这条长路上,纳巴泰人完全掌握稀少的水资源隐藏之处,遂能控制乳香之路。
纳巴泰人及与之比邻的以东人(Idumean)是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沙漠水利学家与地形学家,藏在沙漠中的水源,鲜少能逃过他们的法眼。即使在如月球表面般环境严苛的拉蒙峡谷(Machtesh Ramon),也就是纳巴泰国度中最大的天然谷,他们也找得到札哈兰泉(Ayn Zaharan)的自流含水层──如今犹太人称这一水源为萨哈隆尼姆泉(Ein Saharonim)。纳巴泰人能控制淡水的取用来源,等于掌握了阿拉伯半岛最珍稀的资源,进而控制香料交易。他们十分懂得如何用微乎其微的东西发大财,在今天应该会是很好的纳米科学家。
图7:在内盖夫如此干燥的大地上,水井是纳巴泰商人活命的关键。(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
唯有通过航拍,考古学家才明白纳巴泰人如何彻底改造内盖夫沙漠——他们用大量路标标示商路与有丰富淡水资源的商栈,以形成巨大的网络。这些路标是一个个石头与岩壁,数千年来纳巴泰人会将白色的信息刻画在黑得发亮的石头表面。这些信息多半以类似古阿拉伯文的文字书写,但也有以赛法语(Safaitic)、萨穆德文(Thamudic)、亚拉姆文甚至希腊字母写成的,因为这可能是能说多种语言的纳巴泰人所留下的“密语”。有些标志是指示方向的,例如“往西边走,过了山、到谷地去,就能找到水”。有些则是记录原本约好见面的朋友彼此错过,例如“Sa'id ma shaf Sud”便是记录了费尽千辛万苦之后,却见不到朋友的懊恼心情:“赛伊德没能见到朋友苏德。”
到了公元50年,这些标志也指出内盖夫沙漠另一项史无前例的发展:这里出现如岛屿般的葡萄园、果园,以及种植粮秣与日常粮食农作物的冲积平原。
没错,农作物。先前提过,纳巴泰人原本遵守不耕种的禁忌,是靠着贸易、打劫与畜牧维生,或是采集沙漠中的野生植物。虽然他们顽强地掌控了部分贸易路线,得以繁荣发展,但罗马人与其他民族难免会设法掌握或回避这些道路。在1世纪,纳巴泰人预料罗马人可能带着更强大的军队与军火击溃他们的贸易中心,于是决定解除自我加诸的农业禁忌。之后,他们以广泛的灌溉农作知识打造出世界上最干旱的农作区。为避免被罗马竞争者宰割,纳巴泰人开始把农业耕作的目标定为种植罗马帝国最稀少的供给。考古学家道格拉斯·康莫(Douglas Comer)解释:
对纳巴泰人来说,靠农业取得财富越来越重要,因为像过去那样,依赖贸易发大财的荣景已不复见。在基督诞生之前的数百年,纳巴泰人垄断来自东南亚与非洲的香料、熏香与珍贵货物贸易,将这些商品从阿拉伯半岛南端送到地中海,之后送至罗马。只有纳巴泰人知道跨越鲁卜哈利的道路。但是在公元前66年,庞培(Pompey, 公元前106—前48,古罗马军事家)与海盗开战之后,海路更加安全,终于打破了纳巴泰人掌握阿拉伯半岛运输系统的局面……因此,他们转而出口可运送的谷类。农业生产者可在罗马帝国找到现成的市场,因为罗马帝国有谷类供不应求的情况,就像许多已开发国家缺乏石油。
纳巴泰人突然从野生香料与熏香的交易者,变成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与交易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谷类商品中间商,把持甚至倾销谷类到市场上,还趁着帝国某部分遭逢干旱、瘟疫、饥荒或通货膨胀时获利。他们不仅提供谷类给罗马人、希腊人与波斯人,更引介某些谷类调味品,例如发酵的大麦丸子,后来演变为众所周知的大麦咸酱(bunn)。
从某些方面来看,纳巴泰谷类商人在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今天的嘉能可公司(Glencore International)──这个跨国中介公司掌控了全球1/4的大麦、油菜、葵花籽的供应量,以及1/10的小麦供应量。虽然嘉能可公司并非家喻户晓,但这个跨国公司与子公司的价值超过600亿美元,掌握的资产价值超过790亿美元,包括全球可得铜矿的一半、铝供应量的1/3,以及1/4的燃料用煤。2011年夏天,嘉能可公司在伦敦证交所公开上市时,有人估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几周之内就大赚90亿美元。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指出,嘉能可从不真正长久持有大量的大宗商品“大赚饥荒与混乱的灾难财”。矿业分析师克里斯·席德(Chris Hinde)告诉半岛电视台的克利斯·阿森诺(Chris Arsenault)说:“他们是大宗商品的股票中间商,在相当隐秘的世界中运作,几乎为每一种重要商品制定价格。”
纳巴泰人的角色从沙漠商人、畜牧者、掠夺者,演变成灌溉农田的农夫,最后纳巴泰人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沙漠,但一直要到几个世纪之后,人们才明白这个变动。大约在1870年,考古学家爱德华·亨利·帕莫(E.H.Palmer)开始画出地图,说明成千上万刻意摆放的石堆是曾经种植葡萄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神秘的“葡萄石堆”(tuleilat el-anab)。这些石堆为农业水利设施,能留住水分,收集、集中与传送雾气与露水,帮助藤蔓、小麦与果树生长。在帕莫之后不久,其他人也发现了很长的卵石排列,让鲜少出现的暴雨径流从沙漠流入冲积平原的肥沃谷类梯田。
埃拉特北边25英里的地方,考古学家曾发现嘉蒂安泉(Ain Ghadian)附近的地面上有一系列圆形,乍看像炸弹弹坑,仔细看又像串在项链上的念珠。一位曾与水利工程师合作的沙漠土壤学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辨识出这些图案,并确定其功能。
这些设施是后来的纳巴泰人发明的,功用为集水暗渠。这些暗渠通过像水井一样的竖井,连接到水平水道,而这些水道又能接触到地下水、收集雨水,储藏在地下水塘。这位科学家贝瑞尔·艾森斯坦(Berel Aisenstein)发现了这套系统的效用与范围,说聪明的纳巴泰人发明了“人造泉”。一连串的井能有效供应稳定的新鲜饮用水,这么一来,纳巴泰人即使在一年仅有1寸(25毫米)降雨的干旱之地仍可以生存。在许多闪族语言中,这一供水系统称为坎儿井(qanat),这个词可能衍生出如今在水资源管理上广泛使用的字,相关用词包括运河(canal)、渠道(channel)、长茎植物(cane)与排水道(alcantarilla),而且在全球都有使用。
我知道在距离埃拉港100英里之处,纳巴泰人也在峡谷中使用这种集水技巧。纳巴泰人的首都佩特拉就藏在这一带的峡谷中,只能通过狭缝进入。不过,一座史前城市究竟如何在如此干旱的环境下支持两三万居民生活?显然光靠香料并不够。人不可能光靠着肉桂、番红花或鼠尾草过活。内盖夫的年平均雨量各处都不太相同,介于3到9寸(80到228毫米)之间,少则仅仅1寸,多则13寸(330毫米)。我身为农夫,不免纳闷这里的人如何自给自足?我深知要支持一个家庭已不容易,更何况是整个文明。
当然,答案和什么叫作“支持”有关。纳巴泰人很懂变通,能以令人大开眼界的方式,从一年只泛滥几次的谷地取得水和食物。他们运用香料交易的获利建设水利公共工程,这一重商文化找来外地劳工,搬运移动成千上万吨的石头,建立集水设施,并隐藏饮用水储藏处。旅人在无意间遇见这些储水处时,莫不啧啧称奇。
经过几个世纪靠着贸易积累起财富之后,纳巴泰人已能雇用无数工人排列岩石,建构拦水坝,从岩石密布的山岭斜坡收集雨水,导入肥沃的冲积平原。这么一来,干燥大地的农田上就有“加倍”的雨水可用,从而种植出足够的椰枣、核果、无花果、谷类与豆类,让骆驼夫与战士获得充足的营养。
纳巴泰人和多数有富商阶级的国家一样,发展出高度阶级化的社会。不幸的是,他们已实行定居的生活形态,且投入大量的基础建设在某些商队旅馆,这让他们更难以抵抗想争夺香料与熏香贸易的势力。
正如迈因人,支撑纳巴泰文化成熟发展的力量并非来自地方食物生产。他们靠的是在那个年代,身为全中东最优秀的商人所积累的财富与议价能力。他们严谨地管理几条商路上所有的香料交易,每条商路都有一连串隐秘的商栈。他们设有防御的商队旅馆从也门绿洲经过雅什里布,延伸到加萨、佩特拉与霍兰山(Mount Houran)。纳巴泰人曾一度通过这些方式,掌握罗马与雅典的乳香、劳丹脂、孜然、肉桂与其他芳香植物的价格,即使罗马与雅典人最初想逆转局势,依然徒劳无功。
后来,装备精良的罗马军队拥向红海海岸的埃格拉绿洲(Egra),纳巴泰军队在抵抗入侵者时竟然全军覆没,于是商业垄断的荣景不再。到了公元80年,纳巴泰人已永远失去独占取得也门丰饶资源的能力,因为他们太依赖单一的财富资源。罗马人明白,他们能轻松绕过纳巴泰国度,建立起替代的通商之路。不出几十年,罗马人已吞并纳巴泰和以东,纳巴泰的身份逐渐衰微甚至消失。正因如此,6个世纪之后,波斯食谱作家沃拉克把一道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制作的丰盛炖菜归功于古老的纳巴泰祖先时,反倒引人瞩目。这道菜称为“纳巴泰综合炖煮”(nabātiyyāt)。
但那时,纳巴泰人已从欧洲地中海的城邦国家积累了大笔财富,正如今天拉丁美洲的贩毒集团,最后靠着吸食毒品者,取得北方国家的财富。罗马精英爱上了芬芳的乳香与其他珍贵的芳香植物,遂挥霍大量的城市物产来购买。经济史学家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Bernstein)指出,罗马人会花费大笔财富购买芳香植物,当作炫耀性消费:“罗马有一大笔战利品被用来购买熏香……他们会把乳香放在三脚架(acera)上,供奉在圣坛旁。罗马人的宗教仪式很重视焚烧乳香,因此乳香可以免税进入帝国,不像其他进口物品需要缴25%的税。”
虽然许多历史书认为希腊罗马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推手,但当时掌控世界贸易的其实是纳巴泰人。他们也影响了烹饪传统,还展现出取得世界其他宝藏的卓越能力。然而,除了他们随意在内盖夫砾漠的巨石上留下的涂鸦之外,我们不太清楚这些闪族香料商人的私人与宗教世界。我们只能推测,最早的纳巴泰人崇拜多神,包括太阳神达萨拉(Dushara)与生殖女神拉特(al-Lāt)。这两种神祇最早的记录,都出现在阿拉伯部落的萨吉夫家族(Banu Thaqif)。不过,纳巴泰人越来越频繁地以阿拉米语对话,也具备阿拉米语的思维认知,之后宗教逐渐偏向一神信仰。
纳巴泰人很快明白,任何宗教都可能让他们与潜在客户的社群产生社会与政治的结盟。纳巴泰人的疆域拓展到以东时,与犹太人建立了贸易合作关系,于是纳巴泰人也改信犹太教。在70年以后,随着耶路撒冷圣殿陷落,有些纳巴泰人又变成基督教徒,想借此促成与罗马天主教精英的生意。然而随着时间逝去,他们的语言渐渐回归阿拉伯根源,不再以阿拉米语写作与做买卖,后代改信伊斯兰教。
纳巴泰人有如变形虫,原本是过着游牧生活的畜牧与采集者,后来变成海盗,之后当起船长与商人,最后成为大宗商品的投机者与公共工程的管理者。几个世纪中,他们的信仰从泛神、多神变成一神,目的或许是拉拢商路及目的地的权力掮客,巩固社会关系。之后,他们学习与吸收其他语言,陆续信仰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他们每回表面上改信其他宗教时,都会趁机强化他们在各大陆的贸易结盟关系。
纳巴泰人已学会在推销香料时通过编造故事来加油添醋,也学会在必要时掩饰自己的生活与信仰。事实上,他们或许是世界上为了经济效益,最早懂得操控心灵的文化,早早就懂得“带风向”。熏香与其他有迷幻效果的植物,是他们用来安抚大众的药品。
那群大众居住的地方,多半是地中海沿岸港口与美索不达米亚沼泽地。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罗马与雅典有大量的文献记录证实,乳香、胡椒与肉桂并非是仅属于上流阶级的新奇玩意。这些城邦国家几乎家家户户焚香,目的或许是驱散鲜少沐浴导致的体臭及肉铺与下水道飘出的腐臭。仿佛天堂的香气可以消除百姓日常劳动时的汗臭,避免他们精神不济。今天住在都市的穷人可能会将买手机或名牌牛仔裤当作地位象征(无论能否负担),古代地中海的穷人也会运用芳香的物质、香料与浸泡物来满足自己的物欲,即使这些奢侈品可能榨干他们微薄的财产。
不过有些人渐渐明白,贸易固然可以改善生活与致富,却也会使有些人一贫如洗。恺撒大帝曾设法控制罗马的奢华文化,避免帝国财富过度耗损。他甚至派出食物与熏香“特警小组”到市场与私人住家,搜查谁沉溺于炫富,因为那些人不仅会害得自己破产,也会使帝国财富耗竭。
我来到这片干涸大地时,当然为时已晚,没机会与纳巴泰商人谈谈他们的全球化观念,或聆听他们诉说香料营销技巧。但我至少可以雾里看花,瞧瞧现代人如何在耶路撒冷的市集上运用纳巴泰人留下的资产。
巴士爬上山坡,离开内盖夫,经过死海,来到水源较丰沛的耶路撒冷与伯利恒山丘。巴士终于抵达所谓最神圣的城市时,戴夫神父与我找地方落脚,之后我徒步前往最古老的城区,那里曾是纳巴泰商人经常光顾之处。如今至少有800个商人仍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叫卖商品。
旧城周围的城墙是在1538年完成建设,但部分琢石在2000年前就已安放。我穿过位于北侧、通往基督教与穆斯林区的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走下阶梯,沿着堪艾赛市集街(Souk Khan Ez-Zeit Street)来到阿塔林市集。这里正是耶路撒冷的香料交易延续得最久之处。
但是,我找不到太多香料的踪影,周围尽是摆满运动鞋、凉鞋、背包与帆布袋的服饰店。
我远离这些工厂生产的东西,在基督教区拥挤的步道上蜿蜒前行,直到瞥见圣墓教堂。我恢复方向感之后,朝着艾夫提莫斯市集(Souk Aftimos)的三联拱入口前进,过去这里曾是耶路撒冷最大的香料市集。
我访问一处处的亚美尼亚与犹太商人的摊位,看到他们的面前摆着斑驳的棕色扎塔综合香料、黄色的姜黄、米色孜然与红色的盐肤木粉,香料堆成了尖尖的小山。有些摊位贩卖大块熏香,不光有乳香和没药,还有茉莉、玫瑰与现场混合的独特秘方,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
不过,当场调配香料的商人不多,大部分的摊贩是贩卖三四种包装好的熏香“纪念品”。商人用玻璃纸或塑料袋将其密封起来放在登机箱里,箱子上标示“耶路撒冷熏香”或“贤士的礼物”。不必说,在层层包装的保护下,我根本什么也闻不到。我发现多数观光客会帮香料商人拍数码照,并给他们一点点小费,但鲜少有人购买任何香料或熏香。他们朝犹太区前进,那里有“真正”的纪念品:死海护肤产品与橄榄油香皂、耶稣的凉鞋与珠饰手提包、圣膏油、明信片与T恤。大部分商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但购物者不以为意。每年拥入旧城的“宗教旅客”约有百万人,他们最爱买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天我在旧城找到唯一的新鲜“香料”,是生长在古老的城墙上的。一株续随子在观光客上方蔓延,鲜少人会发现它如此坚毅。(www.zuozong.com)
只不过隔天早上,我高高兴兴地和摩许·贝松(Moshe Basson)主厨准备去本-古瑞安都会森林(Ben-Gurion Urban Forest)找续随子、鼠尾草、盐肤木、芥菜种子、松子与野生开心果时,却感觉在耶路撒冷无论走到哪儿,总令我神经紧绷。于是,我改而前往西岸的伯利恒。我不是为了看不同景色,只是想从旧城的压迫感中喘口气。虽然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中心仅仅6英里路(约10公里),我却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穿过交通打结的大街小巷、路障与检查点,抵达这一带的另一座圣城。
我就是在那边遇见的马尔文(Marwan),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种子商人与育种管理者。他拥有全中东目前最适应沙漠的传统香料与蔬菜种子。他把这些东西称为“本地特有”(biladi)的种子,意思是“属于这个国家与这里的农民”。这些种子是真正的沙漠复古品种,代代相传留了下来。马尔文话不多,乐于谈谈植物繁殖,却不爱谈地缘政治。但是聊着聊着,话题总不免触碰这一带的政治局势。
“这些本地特有的种子,能在降雨稀少的环境中生长。我当然是看重这些种子的质量优良,何况这些种子早已伴随我们数百年。它们必须在缺乏灌溉的情况下生长,毕竟我们的水源时不时就被以色列军人切断。我们脚下的地下水被抽走,顶多能用废水供果树与农作物生长。不过,就算这些植物只要很少的水就能生长,现在还是没什么人要买。”
“没人要买?”我看着他这些品质上佳的种子问,“这些沙漠的香草与香料这么好!难道巴勒斯坦没有农夫、没有人种植物了吗?”
马尔文看起来很疲惫,沉默半晌之后才轻声说:“你恐怕不了解这边的情况。农夫还是设法耕种,却赚不了钱。就算农夫靠着一点点降雨把植物照料到采收……他们在大清早装满卡车,想载去耶路撒冷的市场卖,却在检查站停下来……之后,他们就卡在车阵中动弹不得,等着排队检查。他们坐在那边等呀等,车慢吞吞前进,于是这些沙拉菜呀香草啊全都枯了……”
他叹口气,很无奈地说:“有时候农夫被迫等很久,排队时整车农产品都烂了。他们泄气地回来,放弃务农,不再跟我买种子了。”
我和马尔文道别。离开他的种子与苗圃商店时,我黯然神伤,又无能为力。我决定走一趟伯利恒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屹立之处,这个教堂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教堂中最古老的一座。不过,这里有太多礼品商店与巴士停车场,我很难想象这个地方两千年前,也就是大约公元前4年的景象──当年某些外国人(或许是带着熏香的魔法师或占星者)通过星星的引导,从遥远的国度骑着骆驼前来寻找一名新生儿。
近年有一份古叙利亚语的文件被翻译出来,显示东方三贤士未必是三名来自波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也称为“祆教”)的“智者”,而是一整批来自远东靠海的丝国(Shir)的魔法师或萨满巫师商队。他们在大希律王时代往西方前进,而大希律王是一位以东犹太人,母亲是纳巴泰人。这些来到希律王国度的人究竟是谁,线索并不多,不过倒是有些名字用叙利亚语记录了下来。其中一人叫作古达波(Gudaphar或Gandapor),这个姓氏很可能来自阿拉伯海东北的印巴国度。这个国度中,阿拉米语、希腊语、梵语、巴利语(Pali)都已通行了几个世纪,而琐罗亚斯德教与佛教的影响都沿着丝路靠南边的路径扩张。
这份叙利亚文本近年被译为“贤士启示”(Revelation of the Magi),里面没有提到将乳香和没药当成东方的礼物。然而,这些芳香植物显然在阿拉伯海的北方一带流通,在那个年代甚至可能远达黄海。这些香料在当时可能被当成是相当贵重的礼物,无论是通过陆路还是海路而来。
若他们果真在公元前4年抵达伯利恒,那时正是芳香商品交易在世界大幅扩张的时代:从中国、摩洛哥、印度与索科特拉岛,扩张到今天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以及肯尼亚外海的拉穆群岛。这时陆上与海上的香料贸易,为真正前所未见的全球化拉开序幕。大陆间的贸易已是常态,不再是例外。它依赖多数人对于“异国”的向往,人们借以逃遁日渐辛苦烦闷的日常生活。香料贸易善用人们心中的渴望,并从中牟利,这种做法从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中发展出来。这股渴望并非来自于空空的胃,而是源于难以满足的心灵。
纳巴泰综合炖煮
打开扎亚利的《中世纪伊斯兰世界饮食》(Medieval Cuisine of the Islamic World),会读到查尔斯·佩瑞(Charles Perry)在前言中提到的,“纳巴泰综合炖煮”(nabātiyyāt)的字面意思就是古代纳巴泰人做的汤、炖菜等菜肴,后来流传到阿拉伯与波斯的厨子中,变得更加精致。扎亚利继续说明,这道特殊的菜肴是10世纪后半叶的沃拉克记录的,但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到2世纪之间。许多人认为,面是马可·波罗从中国传入中东的,但这种说法实为讹误。伊朗出生的食谱作家纳米亚·巴曼利(Najmieh Batmanglij)认为,早在马可·波罗之前,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已有多种不同面食的记载,之后面食往东传入中亚与中国。
这里提到的伊特利亚面(itriya)可能是由杜兰小麦制成的(可能也用2粒小麦),这些小麦压碎之后与水混合,加入大茴香与盐,做成厚面糊。面糊再挤压成细条,就像“天使发意大利面”,然后卷成巢状,之后干燥。泰伊(Al Taie)写道,阿曼人如今仍会制作这种面。在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与西西里,也看得到类似的意大利面,称为“tria”,埃及尼罗河附近的聚落也有“treyya”这种面。运用豆类和面使汤变浓稠的做法,让我想起摩洛哥的哈利亚与巧巴炖菜。不过,这道菜肴的特殊之处是在最后阶段加入玫瑰水,味道会大大加分。
匙叶甘松(Spikenard)是来自喜马拉雅山的芳香药草,罗马人常用来调味。源自印度的荜拨(long pepper)也是罗马人厨房中很常见的食材,市场会贩卖晒干的完整果实。荜拨与常见的黑胡椒是亲属,果实研磨之后会释放出胡椒碱(piperine),也就是胡椒中有刺激性的生物碱。在这个食谱出现的年代,人们通常以炭烤的方式来烹饪鸡肉。为重现传统做法的烟熏味,不妨用后院的烤炉取代瓦斯炉,把鸡肉烤至棕色。鸡肉去骨之后,为了增加菜色滋味,可用鸡骨头熬高汤来取代水,之后加入压碎的豆子和鸡肉。
可用橄榄油炒一盘菠菜或芥菜,并加入迷你洋葱与牛肝菌。6人到8人份。
材料
干鹰嘴豆/一杯
新鲜柠檬汁/两大匙
水/六杯
橄榄油/1/4杯
全鸡/两只(每只重约3000~3600克,去骨、切大块,或用等重的鸡腿)
白洋葱/一个,切丁
锡兰肉桂/一根(不是中国肉桂)
黑胡椒/半小匙
白胡椒/半小匙
荜拨/半小匙
芫荽籽/一小匙
完整丁香/一小匙
海盐/一小匙
新鲜肉豆蔻(磨碎)或肉豆蔻粉/一小匙
南姜粉/一小匙,或是半寸的新鲜南姜,去皮切末
鲜姜/一小匙,去皮切末
烹饪用匙叶甘松油/1/4小匙,或一小匙新鲜匙叶甘松的根,去皮切成碎末
玫瑰水/两杯
干面条/85~110克(可用大茴香风味的伊特利亚面、天使发细面,或其他含有香草的细面条)
水煮蛋/五个,煮熟,剥皮切片
意大利绵羊奶酪/110克(其他陈年绵羊奶酪亦可),切片
做法
鹰嘴豆放入碗中,加水淹过,并加入柠檬汁搅拌。在室温中静置8到24小时,也可放进冰箱。沥干、洗净,放入锅中。加水,以中大火烧开,之后转成中小火,不要加盖,把豆子慢煮至软,共需2.5到3个小时。之后将豆子沥干,用金属或木汤匙压成糊状。
在汤锅或铸铁锅中倒入橄榄油,以中火热油。油热了之后,将鸡肉分批加入。每一面煎至金棕色,再用有漏槽的锅铲把鸡肉捞到盘中。之后将洋葱放入油锅,以中火炒至透明,大约5分钟。加入豆泥与肉桂,把鸡肉放回锅中。加入水,刚好能淹过鸡肉和豆子,以文火炖煮鸡肉,把鸡肉煮软,约30到45分钟。
同时把黑胡椒、白胡椒、荜拨、芫荽籽、丁香放入研磨钵,用杵捣成粉(或香料研磨器亦可),之后加入盐搅拌。
等鸡肉变软,加入香料粉、肉豆蔻、南姜、姜、匙叶甘松与玫瑰水拌匀。之后调成大火,煮滚之后加入面条搅拌,煮到面条弹牙。
用大汤匙把鸡肉和面放进深盘中,锅内剩下的高汤也倒入。盘子边缘摆蛋与奶酪切片,即可食用。
番红花
听起来或许难以置信,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料是一种淡紫色小花的性器官。这种花的叶子像草,只有尖锐、类似稻草的苦涩香气。就算作为金黄色染料,也有更便宜的东西可替代。然而真正的番红花(Crocus sativus)仍是香料界的黄金,丝状的红色柱头每公斤批发价超过1000美元,零售价更是上万。采收番红花柱头很费工夫:1公斤番红花丝得靠着手工采集15000朵花朵的柱头,生产成本相当惊人,毕竟整整一亩的花田只能生产一磅的干燥花丝。不过,番红花身价如此昂贵,原因应是没有其他香料能像它一样:番红花总能唤醒爱用者心中不可取代的想象与嗅觉记忆。
番红花含有神奇的化学物质组合,也是不可取代的:藏花素(crocin)、番红花醛(safranal)与苦番红花素(picrocrocin),赋予番红花美丽的颜色与刺激的滋味。番红花的金黄色源自于藏花素,藏花素是一种富含色素的化合物。强烈的香气则源自番红花醛精油,滋味则来自苦番红花素(一种葡萄糖苷),能产生微苦的尾韵。番红花是少数水溶性香料之一,如果把花丝泡水一晚,隔天清晨就能得到金色阳光般的液体。番红花若加上定染剂,就能将衣服染成金黄色。千年来,许多政教界的达官贵人都用番红花来染衣服,连佛教僧侣也使用。
番红花有许多治病方面的相关记载,药用功能包括抗痉挛、镇定与堕胎。
若浓度很高可能产生毒性,但如果要致命,代价恐怕相当高昂。
在历史上,用来当香料、染剂与药物的番红花品种不只一种,因此很难认定古代绘画与著作中提及番红花时,是否都指真正的番红花(C.sativus),即使它是今天最广为利用、价格最高昂的一种。长久以来,植物学家不断讨论着驯化的真番红花起源,因为类似的野生品种在真番红花天然产地的地理范围是找不到的。近年的研究或许稍微解决了一些疑点,确认真番红花是其他两种番红花属植物杂交而来的。其中一种是卡莱番红花(C.cartwrightianus),这种植物生长在希腊大陆与部分岛屿,包括圣托里尼(Santorini)。如今圣托里尼仍大量采收番红花。
番红花的另一亲本可能是“托玛士番红花”(C.thomasii),同样是在地中海一带生长,如今在意大利与爱琴海岛屿仍找得到。虽然真番红花的各种“分身”可能最先在爱琴海附近驯化,也可能是从土耳其,经伊拉克与伊朗,再延伸到印度西北部的这条弧线。考古学家在研究伊朗岩石壁画时,曾发现5000年前番红花属的花色素,虽然几乎可以确定那是来自野生品种。伊朗仍是番红花的最大出口国,但是作家法比安·甘布瑞儿(Fabienne Gambrelle)认为,最好的番红花品种来自克什米尔。
部分历史学家推测,类似番红花的植物最初是在克里特岛栽种,但如此推论的原因,只是3000年前克诺索斯(Knossos)的米诺斯宫(Palace of Minos)有类似番红花的绘图。不过,光靠着这些图或宫殿知名的番红花采集者壁画,未必能确认早期番红花在此驯化。番红花起源之谜仍差那么临门一脚。更进一步的信息,仍有待考古学家与其他历史侦探探究。
无论我旅行到何处,都会发现番红花做成的菜肴往往与种族认同有很强的联系。每当移民到欧美的朋友邀请我到家中共享晚餐时,他们总会得意洋洋地端出加了番红花的米饭。我的西班牙主厨朋友弗朗西斯科·佩雷兹(Francisco Pèrez)得知我喜欢海鲜炖饭,还特地放弃了3个小时的“周日休假”时间,让我瞧瞧该怎么正确制作他的招牌菜,分量之大,足以让40个朋友饱餐一顿。不过,我最喜欢的番红花种族菜肴,是来自北美西部大盆地的巴斯克移民。我前往爱达荷、内华达或犹他州的巴斯克小区时,常碰到晚宴聚会,宴会上会端出分量超大的海鲜炖饭,并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进口的上好番红花着色与调味。我享受可口的炖饭时总会悄悄思考,番红花、淡菜、蛤蜊与虾从伊比利亚半岛海岸被送到几千里外的干燥北美内陆盆地,代表着什么。
15世纪晚期,犹太人与穆斯林家族开始被逐出西班牙,他们带着祖母的食谱与香料,逃往欧洲其他地区及北非、中东与美洲。塞法迪犹太人的家庭中,受洁食(kosher)饮食与阿拉伯的影响,融合出新的传统,强化了他们独特的身份认同。肉丸(albóndigas)佐番红花夕阳酱,只是移居威尼斯的塞法迪犹太人把阿拉伯食谱加以变化的一个例子。这道菜的阿拉伯名称为“chems el aachi”,意思是“夕阳”。那金色酱汁,令人怀念马格里布与安达卢西亚的灿烂夕阳。
肉桂
从香料交易的历史记录看,“肉桂”的科学身份与文化起源众说纷纭。不过,肉桂(Cinnamomum cassia,过去为C.aromaticum)的滋味与历史和许多俗称类似的植物并不一样。通常肉桂(cassia)是指中国肉桂,英文过去称呼其为“杂种肉桂”(bastard cinnamon)实在不恰当,毕竟它绝不逊于其他肉桂。许多人会认为,中国肉桂的滋味虽不如真肉桂丰富,却比较直接强烈,因为中国肉桂红棕色的树皮精油含量比较高。肉桂和樟属(Cinnamomum)一样,这类树为高大常青树,树冠往上收拢,萃取物温润美味的滋味并非来自木头本身,而是树木的内层树皮,这里强烈的芳香油脂含量最高。
中国肉桂与多数其他种类肉桂的辛辣甜味,是因为精油中有浓度很高的桂皮醛(cinnamaldehyde),但和来自斯里兰卡的真肉桂不同,中国肉桂也有不少香豆素(coumarin),这是一种抗凝血剂。有些亚洲人的基因已适应饮食中的香豆素,但有些使用抗凝血药物的人若摄取肉桂,可能会危害健康。多数人仅偶尔摄取香豆素,会觉得滋味细致而不腻、甜美,并有宜人的木质尾韵。
中国肉桂原本是在中国南部省份(例如广东与广西)野生的,今天则主要来自栽培区,而非真正的天然生长地。此外,阿萨姆与缅甸也出产肉桂,越南亦有栽种。树木到了采收树龄,采收者会掀动一块方形的内层皮,之后才从树干切开。这一条如卷轴的树皮会卷得类似软木塞,之后予以干燥与陈年。中国肉桂的内层树皮比其他肉桂厚而粗糙,而粗糙的深棕色表皮会散发出微苦的樟木香气。不过和斯里兰卡或锡兰肉桂不同,中国肉桂不含丁香酚(eugenol)。在产区之外,肉桂树类似续随子般的花苞就比较少见,它除了肉桂香味之外,还有多香果与胡椒味,而叶子也可以提炼肉桂油。
在许多中国方言中,中国肉桂的原始名称可能是桂枝。公元前216年,秦始皇重新为刚纳入版图的地点命名。那个地方因栽培许多肉桂而深受青睐,遂称为“桂林”,即现在广西桂林。
中国肉桂外销的时间得追溯到古典时期,当时的商路上尚未出现其他肉桂品种。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肉桂被视为药草,《圣经》中的肉桂最有可能是中国肉桂,而非真肉桂。1世纪中期,以希腊文写成的《厄立特利亚海航行记》(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就提到,中国肉桂运到了印度港口,再送到亚丁湾与索马里,但这些海上商人未必知道肉桂是在何处采收。
后来,丝路上的粟特人(Sogdian)与波斯商人确实知道这种香料的来源,并称之为“达秦”(dar-chin),其中“秦”是指中国,“达”可能是指芬芳或辛辣的木材。中国西部的维吾尔族如今仍以“达”这个字来泛称香料。中国肉桂在孟加拉国语中称为“darchibi”、印度语中称为“dal chini”、东突厥语中称为“tarçin”、格鲁吉亚语中称为“darichini”,阿拉伯语中称为“ad-darsin”。
将肉桂引进欧洲的,显然是犹太商人或其他闪族商人。希伯来文的肉桂称为“ketsiah”(也是乔布女儿“基洗亚”的名字),呼应了希腊文的“kasia”,罗曼语族的多数语言中也找得到这个词。等到中国肉桂与其他肉桂通过中亚与印度辗转来到西方之时,商人已经运用神话美化其来源。希罗多德道听途说,在《历史》中写道,阿拉伯的巨禽会用肉桂卷来做鸟巢,而阿拉伯人为取得肉桂,就会在鸟巢下放大块的肉。鸟受到诱惑,会把肉叼回巢,却使鸟巢太重而坍塌。等到鸟巢掉到地上,在下方耐心等待的阿拉伯人即可开心拾起。不仅如此,希罗多德还相信,肉桂是种在阿拉伯浅浅的湖水中,由吵闹讨厌的蝙蝠看守。阿拉伯人冒着眼睛被蝙蝠啄出来的风险,全身裹着防护皮衣避免蝙蝠攻击,以收集足够的肉桂卖到欧洲。
世界上许多美味的综合香料中,都不乏肉桂的踪影,例如中国五香粉、中东的巴哈拉特与卡拉达卡(qalat daqqa),以及墨西哥的莫雷酱(mole)与雷卡多酱(recaudo)。我的许多黎巴嫩亲戚在制作吉布(kibbe)、肉饼(kefta)与羊肉串(lahem meshwi)时,都会先用肉桂来帮羊肉调味。不过我最常见到肉桂的地方并非其原产地,也不是我的家乡,而是在拉丁美洲。从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原到危地马拉,许多社群喝热咖啡时都少不了肉桂。他们心中的肉桂,就是中国肉桂。
续随子
续随子(Capparis spinosa var.spinosa)是一种有刺、已适应干燥气候的植物,主要的产物是尚未开花的花蕾,味道有点刺激、苦涩、不太顺口。为了去除花苞的苦味,人们会以盐腌制,或是以盐与醋腌制。腌好之后,花苞中的癸酸(capric acid)、檞皮素(quercetin)与山柰酚(kaempferol,与檞皮素皆属多酚类)会让这永不盛开的花朵产生强烈香味。
续随子成熟后,会结出橄榄绿的泪滴状浆果,上头有细纹。处理浆果的方式和花苞一样,腌制后即可降低刺激的口味,食用方式也和花差不多。在地中海岛屿和沿岸,续随子花朵和浆果可采收,不过浆果的需求量远不及花蕾,花蕾在生长地之外也很受欢迎。小小的花蕾虽然稍纵即逝,但在世界各地依然可以卖出高价。意大利、摩洛哥、西班牙和土耳其是最大的生产国。
从地中海到俄罗斯南部都有续随子的考古记录,但是在史前,续随子并未在土耳其与黎凡特以东的地区使用。其他语言中的续随子花苞与浆果,多半是借用阿拉伯语中的“al-kabar”,或其他更古老的闪族语言(例如腓尼基或纳巴泰语)。土耳其语是“kapari”,印度语称为“kobra”与“kabra”,日文是“ケッパー”(keipa),意大利文称为“cappero”,葡萄牙语是“alcaparra”等。最早把这种半栽培的植物及其腌制技巧与食用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就是闪族商人。
续随子常在废墟中生长。我曾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城(Baalbek)遗址中,看见续随子毛茸茸的花朵;在耶路撒冷旧城,续随子在阿拉伯区外攀着灯柱缠绕而上;在雅典,续随子爬上帕特农神庙的墙面;在安达卢西亚,续随子在阿尔罕布拉宫沿着花园步道而生。我也在中国西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交河故城惊喜地发现续随子的踪迹。在这处已遭到遗忘的、2000年前的大都会中,续随子是最常见的植物。
事实上,植物学家认为亚洲续随子(C.spinosa var mariana)是不同的变种,原生地是印度、巴基斯坦与东南亚,但我不够熟悉,无法得知我在中国西部看到的究竟是变种,还是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当年带着到东方,定居于丝路东边时所留下的品种。
我初次看见续随子的藤蔓,是在食物历史学家玛丽·西麦提(Mary Simeti)的位于西西里岛中部的农场上。这些藤蔓在果树下被栽培成攀缘植物,也就是底部类似灌木,却会像真正的藤蔓一样,沿着树干往上蜿蜒生长。玛丽的西西里农艺学家朋友吉乌斯佩·巴贝拉(Giuseppe Barbera)告诉我,续随子曾是西西里岛最昂贵的出口商品。每个来西西里岛的美国人在返乡时,行李中必定要藏一包这种高价的珍馐。因此我和西西里朋友开玩笑,早在他们的黑手党邻居走私毒品之前,他们就已经懂得走私续随子了!玛丽以生物动力学农法栽种的续随子树丛,令我好生羡慕,因为我每回尝试移植续随子苗到我果园的石灰土上时,总不出几个星期幼苗就枯萎死亡。或许我家欠缺地中海的微风与水气吧!
续随子常做成各种酱汁,搭配肉类、鱼类与禽类食用,包括墨西哥蔬菜炖鱼(pescado a la veracruzana)──这道菜肴说明墨西哥在殖民时代受到安达卢西亚人、摩尔人与黎巴嫩人影响。此外,整个拉丁美洲都找得到的蔬菜丁炖肉(picadillo)、意大利的烟花女面(salsa puttanesca),还有阿卡迪亚(Acadian)、卡郡(Cajun)与克里奥(Creole)的香料蛋黄酱(rèmoulade),皆会加入续随子。在法国,续随子用来增加南法香料奶油(montpellier butter)的滋味,而在斯洛伐克、匈牙利与奥地利,续随子则和洋葱、香草与其他调味品一起用来制作利普陶软质干酪(liptauer cheese)。在希腊、克里特与塞浦路斯,续随子可搭配所有的沙拉,也可加入各种酱料中。在黎巴嫩与巴勒斯坦,许多开胃菜都会用续随子。如果厨师手边一时没有续随子,只要到附近的石墙找找看,就能采集到一些回来做菜。
【注释】
[1] 凯利克森努斯(Callixenus of Rhodes),与公元前2世纪的托勒密二世同年代。
[2] 也称为“小生境”或“生态位”,指某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占有的特定地位,包括空间位置以及在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地位。
[3] 内盖夫(Negev),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广大沙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