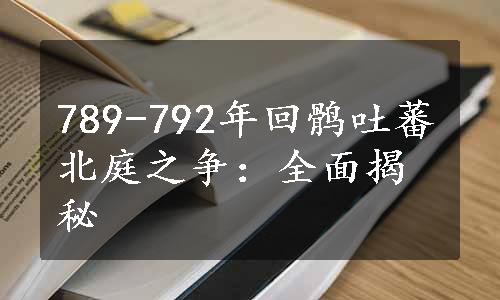
森安孝夫
一、回鹘人与吐蕃人在789—792年为争夺别失八里(北庭)地区的冲突,是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在阐述由这次冲突的结果所提出的问题之前,我必须首先回顾一下在此之前,这两个民族的形势。
在740年间,回鹘人灭了东突厥第二汗国,一举崛起而成为大漠以北地区的主宰者①。回鹘人在震撼唐帝国的安禄山叛乱期间,曾向唐朝派出了一支强大援军,为平息这次叛乱起了重要作用。在此事之后,回鹘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逐渐扩张到天山东部地区②。至于吐蕃人③,他们也利用安禄山叛乱后唐朝的混乱局面,而由东至西逐渐占领了河西走廊诸绿洲城市。他们于784年成功地夺取了敦煌④,与此同时还派遣一支重兵入侵从罗布淖尔到于阗之间的广大地区,而且还作好了进攻天山东部地区的准备⑤。所以,这两大新强正处于夺取东西贸易大道的有利地位,衰弱的唐朝已丧失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二、对于这次冲突的结局,史学家们的看法并不相吻合。有些人认为吐蕃人是胜利者,其他人则认为取胜者是回鹘人。一直到今天,专家们都普遍接受第一种观点,尤其是斯坦因⑥、田阪光道⑦、霍夫曼(Hoffmann)⑧、托玛斯⑨、佐藤长⑩、萨莫林(Samolin) 、埃塞迪(Ecsedy)
、埃塞迪(Ecsedy) 、伊濑
、伊濑 、葛玛丽(von Gabain)
、葛玛丽(von Gabain) 。例如,埃塞迪小姐曾对此问题作出结论认为
。例如,埃塞迪小姐曾对此问题作出结论认为 :“这些地区陷入吐蕃和回鹘的年代……只能是暂时的成功,吐蕃人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在几十年之后,他们终于在黠戛斯军队的压力下逃走了。”
:“这些地区陷入吐蕃和回鹘的年代……只能是暂时的成功,吐蕃人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在几十年之后,他们终于在黠戛斯军队的压力下逃走了。”
然而,安部健夫先生在其《西回鹘国史之研究》一书中,首次对这种论点提出了挑战。在回鹘人于840年遭到黠戛斯人的袭击之后,其中一部被迫逃迁至北庭地区。当时北庭是否真正处于吐蕃人的控制之下呢?如果事实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又该如何解释被戛斯部击败的回鹘人要选择北庭,作为自己的逃难地点呢?因为那里正由他们的宿敌吐蕃人所控制。从这一疑问出发,安部健夫在其书末尾提出了结论,认为事情的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自从789—792年的冲突之后,天山东部地区仍处于回鹘人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有时是严密的,有时又是松散的 。斯普勒(Spuler)
。斯普勒(Spuler) 和哈密顿
和哈密顿 在相当长的时间以来就接受了安部健夫的解释。笔者本人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在相当长的时间以来就接受了安部健夫的解释。笔者本人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进一步发挥了由安部健夫所提出的假设,而在目前正写着的一篇文章中又深入地阐述了我的论点
,进一步发挥了由安部健夫所提出的假设,而在目前正写着的一篇文章中又深入地阐述了我的论点 。在本篇报告中,我仅想概述一下这篇论著,特别是介绍作为本文基础的某些史料。
。在本篇报告中,我仅想概述一下这篇论著,特别是介绍作为本文基础的某些史料。
三、喀喇巴勒哈逊 的碑铭中追念了回鹘保义可汗的功德。我们会从中读到,回鹘人战胜了吐蕃和葛罗禄联军,夺取了北庭地区
的碑铭中追念了回鹘保义可汗的功德。我们会从中读到,回鹘人战胜了吐蕃和葛罗禄联军,夺取了北庭地区 ,击溃了围攻龟兹的吐蕃大军而使该城解围
,击溃了围攻龟兹的吐蕃大军而使该城解围 。回鹘军队一直挺进到遥远的费尔干纳地区和锡尔河盆地,以追歼吐蕃人和葛罗禄人
。回鹘军队一直挺进到遥远的费尔干纳地区和锡尔河盆地,以追歼吐蕃人和葛罗禄人 。
。
回鹘汗国第3位可汗——牟羽可汗(959—779年执政)皈依了摩尼教,并且特许给予粟特摩尼教徒一种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在这一事件之后,牟羽可汗被一支反对摩尼教的势力所推翻,摩尼教在回鹘汗国中有所衰落 。可是,回鹘人为了控制横穿西域的丝绸之路,争取粟特商人们的合作则是必不可缺的。所以回鹘人又重新皈依了摩尼教
。可是,回鹘人为了控制横穿西域的丝绸之路,争取粟特商人们的合作则是必不可缺的。所以回鹘人又重新皈依了摩尼教 。
。
由柏林所收藏的一卷古突厥文写本(T.Ⅱ、D.173.a2号)证实 ,到759年,在蒙古乌德健山地区还存在有摩尼教的“教理大师”
,到759年,在蒙古乌德健山地区还存在有摩尼教的“教理大师” ,即教阶很高的摩尼教僧侣,很可能是一位摩尼师。然而,对于本论文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这卷写本是在吐鲁番盆地发现的
,即教阶很高的摩尼教僧侣,很可能是一位摩尼师。然而,对于本论文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这卷写本是在吐鲁番盆地发现的 。
。
保存在柏林的另一卷古突厥文写本 (T.Ⅱ,D.173号)告诉我们,怀信可汗于803年(羊年)
(T.Ⅱ,D.173号)告诉我们,怀信可汗于803年(羊年) 来到高昌后,向蒙古地区派遣了3位Maxistak,并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一时,向一位Mozka(“大师”)请教
来到高昌后,向蒙古地区派遣了3位Maxistak,并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一时,向一位Mozka(“大师”)请教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mozka是摩尼教等级中最高的级别,依次下降分别为Ispasag、maxistak、dindar和nivosak(声闻者,即世俗者)。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mozka是摩尼教等级中最高的级别,依次下降分别为Ispasag、maxistak、dindar和nivosak(声闻者,即世俗者)。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另一卷文献。这就是由米勒(F.W.K.Muller)所研究过的《摩尼教赞美诗》(Mehr Namag),它是用中期波斯文 所写的摩尼教赞美诗集,其跋文是在保义可汗(808—821年)执政年间所作
所写的摩尼教赞美诗集,其跋文是在保义可汗(808—821年)执政年间所作 。它向我们提供了某些重要史料。该文献一方面提到,在可汗的家族成员中有许多摩尼教信徒,居住在回鹘汗国的许多高级官员中,也有崇仰摩尼教的信徒;另一方面,它也提到在北庭、高昌、焉耆、龟兹等地也有任高级职务的摩尼教徒,而且还点名提到了3位:高昌的药罗葛伊湼(Yaglaqar inal),另外两位焉耆的同名者Uyrur。众所周知,药罗葛为回鹘王家部落的名称
。它向我们提供了某些重要史料。该文献一方面提到,在可汗的家族成员中有许多摩尼教信徒,居住在回鹘汗国的许多高级官员中,也有崇仰摩尼教的信徒;另一方面,它也提到在北庭、高昌、焉耆、龟兹等地也有任高级职务的摩尼教徒,而且还点名提到了3位:高昌的药罗葛伊湼(Yaglaqar inal),另外两位焉耆的同名者Uyrur。众所周知,药罗葛为回鹘王家部落的名称 。
。
我刚才所研究过的各种文书,都是在与本文直接有关的地区发掘而来的。它们都一致证明,在8世纪末到9世纪上半叶期间,天山东部地区占优势的是回鹘人,而不是吐蕃人。我们研究过的汉文和阿拉伯文文书,同样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四、根据米诺尔斯基(Minorsky)的研究 ,塔明·伊本·巴赫尔是一位伊斯兰教徒,他在820年左右曾被派遣出使回鹘。
,塔明·伊本·巴赫尔是一位伊斯兰教徒,他在820年左右曾被派遣出使回鹘。
据他的游记记载,他从下巴尔尚(Bas-Barsxan)出发,经过伊塞克湖附近,随后又转向九姓乌古斯可汗的地区,并且骑着由可汗为他准备好的驿站马前行。我们不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北庭,还是喀喇巴勒哈逊。然而,我们从他的游记中可以看到,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是沿着天山山脉以北的大草原行进的。该地区当时正处于九姓乌古斯可汗控制之下,而九姓乌古斯明显是指回鹘人 。
。
五、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汉文史料。《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后唐懿祖纪年录》记载说,北庭地区的沙陀部开始时是站在回鹘人一边的,最后归降了吐蕃人,被吐蕃人强迁至甘州地区。在紧接着这一段文献之后,我们便会读到:
贞元十三年(797年),回鹘奉诚(怀信)可汗重新占领了凉州并大败吐蕃人。当时为了挑拨沙陀部首领烈考与吐蕃赞普之间的不和。吐蕃有人提出,沙陀人开始时臣服于回鹘人,现在回鹘人又重新变强大,沙陀人一定会复叛。赞普听从了这一意见,将烈考的牙帐迁至黄河彼岸 。
。
如果阅读一下这段文献,那就会清楚地看到,在797年前后,回鹘人的势力非常强大,以至于使他们可以夺取了凉州(即使是短时间的也罢)。因为凉州是河西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当时正处于吐蕃人的控制之下。由于害怕沙陀部倒戈回鹘人一边,所以吐蕃赞普才决定,要把沙陀部从甘州迁至另一地区。
我们再来看一下《资治通鉴》、《新唐书》和《旧唐书》中的某些段落,这些汉籍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回鹘人于9世纪初的对外关系 。
。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万余骑至拂梯泉。辛未,丰州奏吐蕃万余骑至大石谷,掠回鹘入贡还国者”(《资治通鉴》卷238)。
元和五年(810年)6月,“奚、回纥、室韦寇振武”(《旧唐书》卷14)。
“冬,十月,回鹘发兵度碛南,自柳谷西击吐蕃。壬寅,振武、天德军奏,回鹘数千骑至鹈泉,边军戒严”[《资治通鉴》卷233。(误,应为239。——译者)]。
“李吉甫奏请皇帝要求复置宥州,以备回鹘,复党项”(《资治通鉴》卷239) 。
。
“尚绮心儿以兵击回鹘、党项”(《新唐书》卷216)。
所以,我刚才所引证的各段汉籍文献都证明,回鹘人肯定是已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张到了沙漠大碛以南。相反,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吐蕃人居住于戈壁沙漠以北之回鹘领土上的资料。另外,据《资治通鉴》卷241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当与回鹘和亲的唐朝太和公主到达时,回鹘人向北庭和安西地区各派遣了一万名兵卒,以阻止吐蕃人前来制造障碍。此外,在《新唐书》卷215的黠戛斯传中,我们可以读到:黠戛斯人、大食人、吐蕃人和葛罗禄人始终互相援助。由于害怕回鹘人的抢劫,吐蕃前往黠戛斯人中去的行人首先前往葛罗禄人中,并在那里等待黠戛斯人的护送。时至今日,人们还普遍认为这一段文字记载是有关吐蕃人的活动的。他们在占领了北庭之后,可能代替了回鹘人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段文献中所提到的各民族的地理分布,那么这样一种解释则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葛罗禄人当时居住于伊塞克湖地区,那里位于北庭以西很远的地方。当时黠戛斯人却居住在北庭的东北。如果吐蕃人占领了北庭地区,那么他们在前往东北部黠戛斯人中时,为什么要大迂回地向西绕弯到葛罗禄人中呢?事实上,天山东部地区,当时正处于吐蕃人的不共戴天之敌回鹘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吐蕃人要采取大迂回的方法,以等待黠戛斯人的护送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段文献中所提到的各民族的地理分布,那么这样一种解释则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葛罗禄人当时居住于伊塞克湖地区,那里位于北庭以西很远的地方。当时黠戛斯人却居住在北庭的东北。如果吐蕃人占领了北庭地区,那么他们在前往东北部黠戛斯人中时,为什么要大迂回地向西绕弯到葛罗禄人中呢?事实上,天山东部地区,当时正处于吐蕃人的不共戴天之敌回鹘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吐蕃人要采取大迂回的方法,以等待黠戛斯人的护送 。
。
六、最后,我刚才所研究过的一切都倾向证明,在8世纪末,回鹘与吐蕃人的北庭之争中,尽管回鹘人在开始时遭到了失败,但最终却取得了胜利。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的整个天山东麓地区,从此始终处于回鹘人的影响或控制之下,一直到被黠戛斯人从蒙古大量驱逐出来的回鹘人潮流涌来为止。
七、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应指出与本文主旨有关的某些补充资料。
初看起来,汉文史料中的某些段落似乎与我的论点是相矛盾的。例如,我们在《新唐书》卷216卷中读到,到了9世纪中叶,一位吐蕃将领论(尚)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 ,“七年,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诸部。……仆固俊与吐蕃大战,斩恐热首,传京师”
,“七年,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诸部。……仆固俊与吐蕃大战,斩恐热首,传京师” 。根据这几段史料,从前人们一直认为吐鲁番地区直到9世纪中叶,尚置于吐蕃人的控制之下。但是,论恐热的活动仅局限于鄯、廓两州附近。另外,正如藤枝晃在30多年之前所指出的那样
。根据这几段史料,从前人们一直认为吐鲁番地区直到9世纪中叶,尚置于吐蕃人的控制之下。但是,论恐热的活动仅局限于鄯、廓两州附近。另外,正如藤枝晃在30多年之前所指出的那样 ,一方面说仆固俊夺取了西州,另一方面又说论恐热被斩首,这两篇报告均是由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发出的,但书中误将二者合为一体了。所以,我们再没有理由认为吐蕃军队于9世纪中叶,尚驻扎在吐鲁番
,一方面说仆固俊夺取了西州,另一方面又说论恐热被斩首,这两篇报告均是由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发出的,但书中误将二者合为一体了。所以,我们再没有理由认为吐蕃军队于9世纪中叶,尚驻扎在吐鲁番 。
。
P.3918的跋文中提到了赵彦宾其人,他自称“西州没落官” 。当吐蕃人暂时占领高昌时,他身为唐朝的一重要官员。在对该文书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可以认为吐蕃人是792年被回鹘人从吐鲁番盆地驱逐出去的,赵彦宾也被吐蕃人解到了甘州
。当吐蕃人暂时占领高昌时,他身为唐朝的一重要官员。在对该文书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可以认为吐蕃人是792年被回鹘人从吐鲁番盆地驱逐出去的,赵彦宾也被吐蕃人解到了甘州 。同样,P.2732背面末尾的跋文,是用硃笔书写
。同样,P.2732背面末尾的跋文,是用硃笔书写 ,其时代为贞元十年,即公元794年,其中也提到了一位“西州没落僧”。这个和尚也可能同样也是被强行押解到甘州的。
,其时代为贞元十年,即公元794年,其中也提到了一位“西州没落僧”。这个和尚也可能同样也是被强行押解到甘州的。
傅海波(A.H.Francke)研究了某些保存在柏林的吐鲁番藏文写本。据他认为,这批藏卷中有许多封书信,其中有一封是自于阗寄往吐鲁番的,此外还有一些占卜书和医书一类卷子 。至于这批写本的时代,我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就假设认为它们是8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期间的。它们可能是在吐蕃人于791—792年一度占领该城之后,在当地抄写或从外地带来的,或者是它们在较晚时代(晚到11—15世纪之久,即截至德国考古团到达吐鲁番之前为止)被带到吐鲁番的。在这一问题上,陶波(Matred Taube)是有道理的
。至于这批写本的时代,我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就假设认为它们是8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期间的。它们可能是在吐蕃人于791—792年一度占领该城之后,在当地抄写或从外地带来的,或者是它们在较晚时代(晚到11—15世纪之久,即截至德国考古团到达吐鲁番之前为止)被带到吐鲁番的。在这一问题上,陶波(Matred Taube)是有道理的 。至于那些直接由藏文文献译出或深受藏文文献影响的回鹘文佛教文书,我们应该认为它们是在西回鹘汗国建立之后很久才写成的。葛玛丽就曾正确地指出过这一点:“后来回鹘人忘记了他们过去与吐蕃的冲突。从10世纪中叶起,回鹘人再度与之建立了友好关系,因而得到了有关高昌历史的佛教内容的藏文手稿和木板印刷品。最后可能是由于与南部的新关系,喇嘛教思想也影响了回鹘佛教”
。至于那些直接由藏文文献译出或深受藏文文献影响的回鹘文佛教文书,我们应该认为它们是在西回鹘汗国建立之后很久才写成的。葛玛丽就曾正确地指出过这一点:“后来回鹘人忘记了他们过去与吐蕃的冲突。从10世纪中叶起,回鹘人再度与之建立了友好关系,因而得到了有关高昌历史的佛教内容的藏文手稿和木板印刷品。最后可能是由于与南部的新关系,喇嘛教思想也影响了回鹘佛教” 。另外。我们可以期待,有朝一日,在吐鲁番还会发现真正是西回鹘汗国(9世纪中叶到13世纪)时代的藏文文书。
。另外。我们可以期待,有朝一日,在吐鲁番还会发现真正是西回鹘汗国(9世纪中叶到13世纪)时代的藏文文书。
注释:
①马克拉斯:《从唐代史料看回鹘帝国(744—840页)》,1972年堪培拉版。
②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之研究》,1955年京都版;《唐代回鹘史研究》(羽田享遗作集)上册,历史研究,1957年京都版,第157—324页。
③伯希和:《吐蕃古代史》(伯希和遗作第5卷),196l年巴黎版。
④戴密微首次提出设想,认为敦煌是于787年最终陷蕃的,他不主张781年之说。这一论点后来逐渐被许多人接受或支持,如苏莹辉、饶宗颐、池田温和山口瑞凤等人。请参阅戴密微:《吐蕃僧诤记》,1952年巴黎版,第169—178页、359—360页;苏莹辉:《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降蕃最晚的原因》,载《大陆杂志》第41卷,第9期,1970年台北版,第23—25页;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载香港《东亚学报》第9卷,第1期,1970年号,第1—14页;池田温:《丑年十二月僧龙藏牒——介绍有关9世纪初敦煌家产分割的诉讼文书》,载《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72年东京版,第37页注⑥;山口瑞凤:《吐蕃佛教年代考》,载《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纪要》第3卷,1979年东京版,第9—10页。然而,藤枝晃先生却始终坚持认为敦煌陷落的时间为781年,虽然这一观点已不再为人所接受了。参阅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载《东方学报》,1941年京都版,第12卷,第3期,第84—85页和注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载《东方学报》,1961年京都版,第31卷,第209—210页和注⑦。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载《东方学报》,1961年京都版,第31卷,第209—210页和注⑦。
⑤森安孝夫:《论吐蕃人在唐代向中国西域的扩张史》(尚未出版的日文著作)。
⑥斯坦因:《古代于阗考》第1卷,1907年牛津大学版,第65页。
⑦田阪光道:《中唐的西北边界形势》,载1940年东京《东方学报》第11卷,第2期,第175—176页。
⑧霍夫曼:《西藏文献中的葛罗禄人》,载1950年《莱顿东方文献丛刊》第3卷,第199页。
⑨托玛斯:《新疆西藏资料集》第2卷,1951年伦敦版,第283—284页。
⑩估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第2卷,1959年京都版,第702页和注25。
 W.萨莫林:《12世纪的东突厥斯坦》,1964年海牙版,第69页。
W.萨莫林:《12世纪的东突厥斯坦》,1964年海牙版,第69页。
 埃塞迪:《790—791年北庭的回鹘和吐蕃人》,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第17卷,1964年布达佩斯版,第83—104页。
埃塞迪:《790—791年北庭的回鹘和吐蕃人》,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第17卷,1964年布达佩斯版,第83—104页。
 伊濑:《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1968年东京版,第469、475—476和481页。(www.zuozong.com)
伊濑:《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1968年东京版,第469、475—476和481页。(www.zuozong.com)
 葛玛丽:《859—1250年间高昌回鹘人的宫廷生活》,1973年威斯巴登版,第27页。
葛玛丽:《859—1250年间高昌回鹘人的宫廷生活》,1973年威斯巴登版,第27页。
 埃塞迪,上引文第83页。
埃塞迪,上引文第83页。
 安部健夫书,第3卷:《唐代东回鹘的宗教及其经典》第139—230页。
安部健夫书,第3卷:《唐代东回鹘的宗教及其经典》第139—230页。
 斯普勒:《突厥人在西域的扩张史》,1966年莱顿—科隆版,第156页。
斯普勒:《突厥人在西域的扩张史》,1966年莱顿—科隆版,第156页。
 哈密顿:《〈占卜书〉跋文》,载《突厥学报》第7卷,1975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版,第9页注
哈密顿:《〈占卜书〉跋文》,载《突厥学报》第7卷,1975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版,第9页注 。
。
 森安孝夫:《回鹘和吐蕃的北庭争夺战以及其后的西域形势》,载1973年《东方学报》第55卷,第4期,第60—87页以及该文第ii—iii页的英文摘要。
森安孝夫:《回鹘和吐蕃的北庭争夺战以及其后的西域形势》,载1973年《东方学报》第55卷,第4期,第60—87页以及该文第ii—iii页的英文摘要。
 森安孝夫:《回鹘和吐蕃的北庭争夺战以及其后的西域形势》摘要,载1979年东京《亚细亚文化史论丛》第3卷,第200—238页。
森安孝夫:《回鹘和吐蕃的北庭争夺战以及其后的西域形势》摘要,载1979年东京《亚细亚文化史论丛》第3卷,第200—238页。
 见《由芬兰考察团于1890年所搜集和由芬兰—鸟戈尔学会所发表的鄂尔浑河流域碑铭》,1892年赫尔克府版,前言第27—38页;第二、三通碑的汉文碑文片断的转写、分析和翻译,由德维利亚(Deveria)所发表,第24—25页和图表44—64;施古德(Gustav Schlegel):《喀喇巴勒哈逊的汉文和突厥文纪功碑》,载《芬兰—鸟戈尔学会论丛》第9卷,1869年赫尔辛克府版,第141页;汉森(Olaf Hansen):《喀喇巴勒哈逊3种文字纪功碑中的粟特文碑文》,载《芬兰—鸟戈尔学会论丛》第44卷,1930年赫尔辛克府版,第39页;奥尔昆(H.N. Orkun):《古代突厥碑铭集》第1卷,1936年伊斯坦布尔版,第85和96页;第2卷,1938年伊斯坦布尔版,第31—54页;羽田亨上引书,第303—324页。
见《由芬兰考察团于1890年所搜集和由芬兰—鸟戈尔学会所发表的鄂尔浑河流域碑铭》,1892年赫尔克府版,前言第27—38页;第二、三通碑的汉文碑文片断的转写、分析和翻译,由德维利亚(Deveria)所发表,第24—25页和图表44—64;施古德(Gustav Schlegel):《喀喇巴勒哈逊的汉文和突厥文纪功碑》,载《芬兰—鸟戈尔学会论丛》第9卷,1869年赫尔辛克府版,第141页;汉森(Olaf Hansen):《喀喇巴勒哈逊3种文字纪功碑中的粟特文碑文》,载《芬兰—鸟戈尔学会论丛》第44卷,1930年赫尔辛克府版,第39页;奥尔昆(H.N. Orkun):《古代突厥碑铭集》第1卷,1936年伊斯坦布尔版,第85和96页;第2卷,1938年伊斯坦布尔版,第31—54页;羽田亨上引书,第303—324页。
 喀喇巴勒哈逊碑,汉文部分第144—15行,粟特文部分第19行,突厥文部分已残缺。
喀喇巴勒哈逊碑,汉文部分第144—15行,粟特文部分第19行,突厥文部分已残缺。
 汉文部分第16行,粟特文部分已残缺,突厥文部分也残缺。
汉文部分第16行,粟特文部分已残缺,突厥文部分也残缺。
 汉文部分第20—21行,粟特文和突厥文部分巳残缺。
汉文部分第20—21行,粟特文和突厥文部分巳残缺。
 田阪兴道:《回鹘迫害摩尼教的运动》,载《东方学报》第2卷,第1期,1940年东京版,第223—232页。
田阪兴道:《回鹘迫害摩尼教的运动》,载《东方学报》第2卷,第1期,1940年东京版,第223—232页。
 森安孝夫:《蒙古回鹘人摩尼教史研究》(尚未公开发表的日文学位论文)。
森安孝夫:《蒙古回鹘人摩尼教史研究》(尚未公开发表的日文学位论文)。
 勒柯克:《高昌突厥摩尼教》,载《普鲁斯皇家科学院论丛》,语言—历史类,1912年柏林版,第11—12页。
勒柯克:《高昌突厥摩尼教》,载《普鲁斯皇家科学院论丛》,语言—历史类,1912年柏林版,第11—12页。
 森安孝夫上引1973年文第73—74页,1979年文第216页;巴赞:《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历法》(巴黎第3大学学位论文),1974年里尔版,第312—313页,
森安孝夫上引1973年文第73—74页,1979年文第216页;巴赞:《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历法》(巴黎第3大学学位论文),1974年里尔版,第312—313页,
 勒柯克,上引文,第3—4页。
勒柯克,上引文,第3—4页。
 勒柯克:《在高昌发现的摩尼教残经》,载《汤姆森纪念文集》,1912年莱比锡版,第147页。
勒柯克:《在高昌发现的摩尼教残经》,载《汤姆森纪念文集》,1912年莱比锡版,第147页。
 我不能接受勒柯克、班克、葛玛丽和田阪兴道等人的假设,他们认为牟羽可汗是于767年(羊年)到达高昌的。相反,笔者与哈密顿一样,在这一点上也同意安部健夫的观点。见勒柯克:《在高昌发现的摩尼教残经》第194页;班克与葛玛丽:《吐鲁番突厥文献》第2集,载《普鲁斯皇家科学院论丛》,语言历史类,1929年第22卷,柏林1929年版,第413页;葛玛丽:《突厥人中的草原和城市》,载《伊斯兰文献》第29卷,第l—2期,1949年号,第58—59页;《漠北时代回鹘诸城廓》,载《蒙古学报》第2卷,1941年东京版,第232页注
我不能接受勒柯克、班克、葛玛丽和田阪兴道等人的假设,他们认为牟羽可汗是于767年(羊年)到达高昌的。相反,笔者与哈密顿一样,在这一点上也同意安部健夫的观点。见勒柯克:《在高昌发现的摩尼教残经》第194页;班克与葛玛丽:《吐鲁番突厥文献》第2集,载《普鲁斯皇家科学院论丛》,语言历史类,1929年第22卷,柏林1929年版,第413页;葛玛丽:《突厥人中的草原和城市》,载《伊斯兰文献》第29卷,第l—2期,1949年号,第58—59页;《漠北时代回鹘诸城廓》,载《蒙古学报》第2卷,1941年东京版,第232页注 ;上引安部健夫书,第207—210页;上引森安孝夫1973年发表于《东方学报》的论文第73页注
;上引安部健夫书,第207—210页;上引森安孝夫1973年发表于《东方学报》的论文第73页注 和
和 ,1979年文第215页注
,1979年文第215页注 和
和 。
。
 对于Olurmaq一词,我不能接受亨宁先生的解释。参阅W.B.亨宁:《有关摩尼教史的新资料》,载《德国东方学报》,1936年,第90卷,第14—15页;上引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233页注
对于Olurmaq一词,我不能接受亨宁先生的解释。参阅W.B.亨宁:《有关摩尼教史的新资料》,载《德国东方学报》,1936年,第90卷,第14—15页;上引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233页注 。
。
 F.W.K.米勒:《一叶摩尼教赞美诗写本(Mabrn mag)》,载《普鲁斯皇家科学院论丛》,语言历史类,1912年号,1913年柏林版,第40页;葛玛丽:《回鹘人的草原和城市》,第60—61页;上引安部健夫书,第217—219页;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211—215页。
F.W.K.米勒:《一叶摩尼教赞美诗写本(Mabrn mag)》,载《普鲁斯皇家科学院论丛》,语言历史类,1912年号,1913年柏林版,第40页;葛玛丽:《回鹘人的草原和城市》,第60—61页;上引安部健夫书,第217—219页;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211—215页。
 此人并不是昭礼(823—832年执政)。我同意哈密顿的意见,见《五代回鹘史》,1955年巴黎版,第141页注⑨和
此人并不是昭礼(823—832年执政)。我同意哈密顿的意见,见《五代回鹘史》,1955年巴黎版,第141页注⑨和 ;参阅森安孝夫1973年文注
;参阅森安孝夫1973年文注 ;1979年文、第312页注
;1979年文、第312页注 。
。
 亨宁:《焉耆和吐火罗》,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9卷,第3期,1938年伦敦版。参阅第545—571页,尤其是第566—567页。
亨宁:《焉耆和吐火罗》,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9卷,第3期,1938年伦敦版。参阅第545—571页,尤其是第566—567页。
 米诺尔斯基:《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地区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12卷,第2期,伦敦1948年版,第275—305页。
米诺尔斯基:《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地区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12卷,第2期,伦敦1948年版,第275—305页。
 上引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217—218页。
上引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217—218页。
 同上。第219页。
同上。第219页。
 上引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219页。
上引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219页。
 伯希和:《吐蕃古代史》第132页。伯希和认为这一年为821年,但这是一种误解。
伯希和:《吐蕃古代史》第132页。伯希和认为这一年为821年,但这是一种误解。
 上引伊濑文,第474—475页。
上引伊濑文,第474—475页。
 上引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220—224页。
上引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220—224页。
 伯希和:《吐蕃古代史》第136页。
伯希和:《吐蕃古代史》第136页。
 同上引书,第139页。
同上引书,第139页。
 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下,载《东方学报》第12卷,第4期,1942年京都版,第45—46和54—55页;上引安部健夫书,第250—251页。
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下,载《东方学报》第12卷,第4期,1942年京都版,第45—46和54—55页;上引安部健夫书,第250—251页。
 森安孝夫于1977年在《东洋学报》第59卷,第2期中发表的文章。
森安孝夫于1977年在《东洋学报》第59卷,第2期中发表的文章。
 上山大峻:《8世纪安西的密传》,载《中世纪经典》第399页,1972年京都版。
上山大峻:《8世纪安西的密传》,载《中世纪经典》第399页,1972年京都版。
 上引森安孝夫,1973年文,第77—32页和注64;1977年文,第226—231页和注86。
上引森安孝夫,1973年文,第77—32页和注64;1977年文,第226—231页和注86。
 隋丽玫:(Marie-Rose Seguy):《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有年代的敦煌写本》,载《敦煌学》第1卷,1974年香港版,第44页。
隋丽玫:(Marie-Rose Seguy):《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有年代的敦煌写本》,载《敦煌学》第1卷,1974年香港版,第44页。
 弗兰格:《吐鲁番藏文写本》,载1924年《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第5—20页;《吐鲁番藏文写本续》,同上刊物,第110—118页;《关于吐鲁番藏文佚本的残卷》,同上刊物,1928年,第101—118页。
弗兰格:《吐鲁番藏文写本》,载1924年《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第5—20页;《吐鲁番藏文写本续》,同上刊物,第110—118页;《关于吐鲁番藏文佚本的残卷》,同上刊物,1928年,第101—118页。
 陶波:《柏林藏藏文文书中的人和称号》,载《纪念乔玛讨论会文集》,1978年布达佩斯版,第487—520页。
陶波:《柏林藏藏文文书中的人和称号》,载《纪念乔玛讨论会文集》,1978年布达佩斯版,第487—520页。
 葛玛丽:《回鹘王国史》第28页。
葛玛丽:《回鹘王国史》第28页。
(译自1981年《亚细亚学报》第269卷,第1—2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