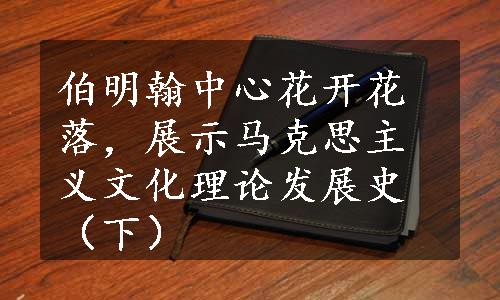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高等教育体制内部致力于考察工人阶级和边缘群体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有了一席立足之地。但是文化研究鲜明的跨学科性质,也使得它本身的学科定位,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中心一开始的三人小组团队编制,一直延续到霍尔出任第二任主任。当时霍尔麾下,也不过只有分别从历史系和英语系过来的两个助手。霍尔主掌CCCS的时期,是文化研究如日中天的时代。中心的工作人员大体保持在六至十人之间,研究的方式主要是在中心成员聚焦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亚文化等等话题提交论文,组织讨论。这些文章后来大都发表在中心自己简易印刷的内部刊物《屏幕》之上。中心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跨学科的方法。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来自文学的文本分析,以及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民族志研究这三大主要方法论,从霍尔开始,在方法上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文本分析主流,逐渐转移到法国理论的影响,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后结构主义,特别是拉康的理论方法,以及很快流行不衰的后现代传媒理论。其他如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也都是中心娴熟的研究方法。
中心在斯图亚特·霍尔主持下,经历了它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理论中心。霍尔和中心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安吉拉·麦克洛比、保罗·威里斯、理查·约翰逊、迪克·赫布迪基等人,继承了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兴趣。但是,70年代伯明翰中心面对的战后世界,已大不同于霍加特当年《识字的用途》中描写的50年代。这个世界见证了如火如荼的学生抗议和激进批判,还有妇女解放、同性恋解放、反种族歧视。这是《识字的用途》的世界闻所未闻的。但即便时代不同,伯明翰中心依然能感受到下层阶级文化生活中的抵制情绪,著名的例子有迪克·赫布迪基1979年的作品《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以及它给出的一系列与黑人宗教、时尚、颓废男孩、摇滚乐手、光头、朋克等等相关的问题。这一类亚文化诚如霍加特呼唤昔年的工人阶级文化,引发的是活生生的文本,便于作细致分析。但赫布迪基和伯明翰中心如今重视的是符号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将目光投向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和罗兰·巴特。赫布迪基认为这类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亚文化,总是受到市场化商业娱乐的威胁。商业主义吸收了抵制的模式和风格,在赫布迪基看来,它终究是稀释并且摧毁了亚文化的真正反抗抵制力量。
伯明翰中心声誉如日中天之际,它当仁不让是全球范围文化研究的精神源泉。但是伯明翰中心今已不存。80年代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改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在关心伯明翰中心的人看来,似乎已经是一个鼎盛期过后的衰退征兆。结果是重建了社会学也重建了文化研究的构架。伯明翰校方对新建的系有明确的要求,要求它招收本科生,它的研究方向,自然也得有所改变。同时新一代的教师充实进来,新的领域如技术、公民义务、环境科学等等,纷纷开辟出来。这是标新立异呢,还是与时俱进呢?似乎也难一言定断。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研究的领域,拓展下来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2002年6月27日,伯明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最终在暑假期间以学科重组的名义被伯明翰大学撤销了。这意味文化研究的发源地历经合并重组,在三十四年后,终于宣告关闭。学生们一开始反应激烈,8月1日,伯明翰大学学生就关闭事件召开大会,发表声明称他们正在经历的时刻,是支配人的意志变成被支配人命运的时刻。在经济需要和高效率研究的名义下,批判性质的社会科学面临市场化的逻辑,正危机重重,因为市场逻辑视批判思想为绊脚石,恨不能将它一脚踢开。比较在中国本土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恩怨交锋,或许伯明翰中心本身的关闭,可以显示传统人文学科面临上述市场逻辑的冲击,除了与时俱进,恐怕是别无选择。
但伯明翰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的撤销,对于文化研究本身,除了一个符号意义上的失落,应是无伤大体的。许多院别已经纷纷开设文化研究课程,所以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学生再是惊诧不解,对于学业倒也无妨,大多数课程可以继续开设下去。专业并没有取消,而是重组,这也是校方愿意强调的说法: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是经历了重组,因为它没有通过是年的研究考评。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教学上基本每年都是名列前茅。它所提供的课程,普遍认为是最优秀的。该系在上一年的教学评估中,就得了最高分24分。现在问题出在研究考评,我们不妨来看这个“研究考评”又是什么东西。
研究考评就是我们所说的科研考评。它或者可以显示科研第一的高等教育办学方针,在发达国家中,亦是被贯彻得多么无情无义。伯明翰中心的最终消失,与文化研究关注的政治权力其实关系不大,而是反映了英国高等教育机制内部的压力。这压力似乎是无所不在的,据称高等教育人工部长的迫切使命之一,就是要让英国50%的学生都可以上大学。与此同时,许多奖学金项目纷纷落马,导致学生的债务直线上升。牛津、剑桥这样的老牌名校可以理直气壮,不断拉涨学费,一些财力捉襟见肘的新校,就只有广开门路,多多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所以科研经费的竞争,说它已经关乎许多学校的生存问题也不为过。此外教工薪酬和工作条件持续滑坡,高等教育面临的就业危机则反过来与日俱增。这一切不稳定因素,足以显示伯明翰中心的关闭有许多无奈。不说其他高校类似的系多遭此同类命运,莱斯特(Leicester)大学关闭了它享有盛誉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一样叫人颇费猜测。这一股流行一时的关闭之风,被认为是标记了英国尝试高校重组的一个开端。重组的目标是提高财务状况良好的研究机构的竞争力,将之推向全球市场,同时使政府对高校事务的参与,可以惠及每一个国民。
但即便如此,关闭事件还是显得突兀。因为伯明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前不久还在政府的教学评估中得了最高分数。社会学的教学计划也经历了评估,从政府公布的数字来看,被认为是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最好的本科生教学。照市场逻辑来看,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率不断提高,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慕名纷至沓来,显然都是成功的标记。那么,问题为什么出在这个“科研”上面呢?关闭伯明翰中心的主要理由,是它在政府研究性评估方面表现不佳。评估本身是多有争议的,以至于有人说,由于一些系所擅长此道,导致评估优秀的单元数量急遽膨胀。此外同行评估,更是成为争议的焦点。评估小组逐系审读每一个教工的成果,根据业绩来分派预算。在这里,教学优秀是不起作用的。伯明翰中心校方的要求,是各系的考评不得低于4分,这是通行全国的优秀基准。而2001年的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恰恰是在这个基准之下,分数是3a。因此,不乏有人将中心的关闭归结为同道的妒忌。
伯明翰中心的撤除,可以说是它全盛时期突然遭此厄运,是不是意味着文化研究的气数已经耗尽?答案是否定的。在许多人看来,它更像是文化研究另起炉灶的一个新的开端。中心的薪火相传已经完成,仅就伯明翰大学来看,今日许多其他系所的专业和教师,也在潜心从事CCCS传统的文化研究。而随着此前霍尔等人移师开放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等等,文化研究早已经在全英国范围内扎根开花。而且,它的重镇总是在成人教育和传统工业城市区域,总而言之,文化研究我们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它委实是已经无所不在了。其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不衰标志着学术热点和专业的重组。这个重组已经不需要伯明翰中心的神话,中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伯明翰中心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它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景,又意味着什么呢?(www.zuozong.com)
理查·约翰逊后来接替霍尔担任伯明翰中心主任,鼓励社会和历史研究。当时中心的成员有莫林·麦克内尔、迈克尔·格林和安·格雷,三人均擅长文化理论和传媒研究。迈克尔·格林后来在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题的文章中,就伯明翰中心的早期研究成果,归纳过以下四个主题:
其一,强烈、复杂且持之以恒的文化差异。如E.P.汤普森论早期工人阶级是怎样自觉形成的;霍加特谈英国北方坚韧的工人阶级文化;威廉斯则着目于劳工运动,讲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成就。这里面话题都是工人阶级,但是文化各各不同。此种差异,甚至见于形形色色的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而青年亚文化普遍被认为是阶级或“父母”文化内部压力释放的集中宣泄路径。
其二,倡导文化是“普通平常的”,强调文化是从日常生活之中发现和汲取意义。这和战后英国的政治形势是背道而驰的。比如劳工党的英国“人民”节被吸引眼球的加冕礼取而代之,约翰·里斯麾下的BBC热衷走教育路线,轻视平民娱乐,以及40年代和50年代的英国出版界,也普遍抵制异端。
其三,强调形形色色的教育和传播新形式,从根本上说都是不民主的。例如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中,就提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将能动积极的求知过程,普及到所有民众,而不是局限在少数人集团。当年霍加特批评过英国独立电视台,威廉斯也对当代影像传播中的商业主义表示反感,呼吁关注民主的表征形式,促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模式。
其四,有关英国和“体面”的辩论。不仅否定大英帝国主义,同样不愿意效法颐指气使的美国商业文化,抑或悄然无言的瑞典式社会民主模态。反之有意预示一个充分重视地方乡土色彩的英国文化,甚至威尔士文化。[2]我们可以注意到,威尔士正是威廉斯的家乡。
从以上归纳的伯明翰中心文化研究的四个主题,可以看出英国新左派注目的政治生活的特点,即强调文化是社会生活中共享的意义生产和流通。中心不但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对于日常生活和本土文化,也都给予了充分重视。反之把大众传媒的语言和形象,看作特定阶级和集团假公济私的虚假表征。换言之,它们所表现的,并非“共享”的价值观念。所以这样来看,大众传媒一方面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一方面也是受众自觉不自觉的抵制场地。文化研究就在这一动态的抵制和协调过程中,书写着资本主义既定秩序的颠覆努力。
无疑,伯明翰中心的文化研究挑战了“二战”之后英国的主流文化。文化曾经是文学和艺术的一统天下,无论是文本还是行为思想,文化分析几乎是清一色的美学的标准。反之大众文化体现的就是商业趣味、低劣趣味,或者说纯粹就是没有趣味,是审美趣味的堕落。但是现在,趣味的天经地义的高雅和风雅,在文化研究的挑战之下,已经将变得摇摇欲坠了。文化研究虽然走的是外围路线,但是很显然,它已经在高等教育的体制中站稳了脚跟。或许今天它还是一门准学科、新兴学科,但是相信不用太久,它会像我们的其他传统学科一样,在不同的专业里牢固地确立它的地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