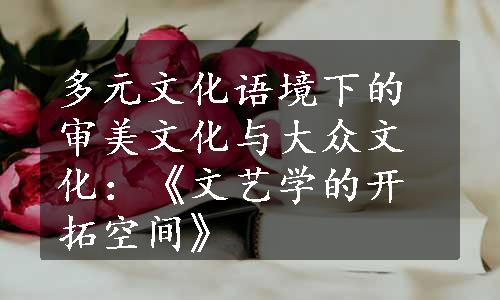
杜文娟
在西方世界,美学一度被视为艺术哲学,致力于在形而上层面考察艺术现象、艺术创作的审美价值与规律。审美文化,此概念本身便包含着跨学科的双重含义,既是美学范畴里的一个特定概念,是美学冲破其传统的形而上经典话语形式向现实生活迈出的一步,又是文化领域考察研究的对象。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一时间许多概念混存,尤其是对于传统“审美文化”、当代大众文化等概念,以及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有诸多的解释。
本文尝试考证“审美文化”的原始涵义及其延伸义,探讨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下如何定位审美文化,审美文化应承担怎样的价值功能,审美文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的关系等。
一、审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从语义学上讲,文化的原始意义是“耕作(husbandry)”,或者对农作物生长进行管理(“栽培”、“培养”)。后来语义得到进一步延伸,指称人的“教养”、“修养”等,因此从原始意义上讲文化本身包含了物质和精神双重内涵。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为文化所下的三个定义在西方颇具权威性,他认为,首先,文化可以用来指智慧、精神和美学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其次,文化是指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一个民族的,还是一个时期的,或者是一个群体的;最后,文化可以指智慧、特别是艺术活动的成果和实践(1)。这是对文化的社会性的整体描述,重在突出其精神层面。审美文化毋宁说是在文化和美学领域里的一种意义整合,本身便包孕着一个跨学科的语义机制,既背负了西方传统美学中的美育思想,又兼具文化的精神倾向性和实用性(体现一定的生活方式并对其加以适时指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审美与文化的整合,是以艺术为本位的自我培养、自我实现,也是一种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的文化形态。就其内涵而言,有狭义与广义之别。
据考证,“审美文化”最早见于德国美学家席勒笔下。“粗野统治着社会的下层,懒散和性格败坏统治着社会的上层。这两种弊病同时出现,是当今时代的特征”(2),其结果是,造成人的天性的和谐状态被破坏,人的性格丧失完整性。要改变现状必须致力于造就审美的人,建立审美的国家,“人必须开始他的道德生活……必须开始有它的自主性……必须开始有理性自由……必须学会有更高尚的欲求”(3),而这一切通过审美文化都会做到。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更高的艺术即审美教育来恢复他们天性中的这种完整性”(4),用审美来教养(cultivate)人。艺术创作本身的感性化、形式化色彩使其完成了对现实生活审美观照,也使得美学开始走下高高在上的纯粹理性的“圣坛”,转而面向现实。但也不难看出,席勒仍是在形而上的层面探讨审美文化问题,所期待的是超越阶级、政治经济、现代文明的精神自主性、独立性、形式之美(审美假象),更强调个体感性体验,通过感性提升道德感、理性感,其表达方式是通过艺术培养感觉功能、性格的高尚化,最终通过更高的艺术,审美教育实现审美文化。由此看来,席勒所谓的“审美文化”即审美教育、审美修养,或者说艺术修养(5),审美文化既是完善社会的手段和工具,又是一种实现人格完整的理想境界。
席勒观念中的“审美文化”的关照对象是传统的美的艺术,而他对艺术的认识源于康德。康德认为艺术的自律性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艺术是自由创造的产品;第二,艺术是非功利、无目的(以艺术品自身为目的)的创造;第三,艺术是艺术家(个人)的天才的产物——不可重复的原创品。席勒也主张,“艺术是人类理想的表现,它是由精神的必然而产生的,不是为了满足物质方面的需求。”(6)席勒所谓的审美教育、审美文化及其表达方式艺术强调人类审美活动的精神解放性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审美视点,这是感性与智性相融合而达到的一种人格境界,尽管内容涉及现实的因素,使审美与现实生活相关联,使审美承载一定的社会价值功能,但席勒对艺术的认识仍是充满德国狂飙突进时代的理想化、超现实色彩,因此也只是一种学理上的理想表达,并且席勒的“审美文化”实际上更多地定位于所谓的高雅艺术、精英文化、贵族文化,将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生活主要落实于所谓的高雅趣味,以精英文化为主体,而忽视了社会底层群体的文化。同样,英国历史上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一度大力推崇文化,而其主旨也无外乎贵族文化、精英文化,期待用高雅艺术的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精神境界,从而改造社会,消除阶级差别等。
打破审美惯有的自律性、超功利性,使其面向现实,向整个文化环境开放当归功于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在其论文《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以艺术为核心探讨审美的语义内涵、研究对象及其价值问题,系统地阐述了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提出“美是生活”观,首先将美定位于活生生的直观的生活现实;其次,又赋予审美理想化色彩,主张“生活就是美的本质”,并非所有的生活均为美,而是符合人的主观愿望的生活,即实用、具有生命力、活力的生活才是美的,“美是生活;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美包含着一种可爱的,为我们的心所宝贵的东西”。进而提出艺术包含两方面内容: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的第二目的是“说明生活”,“艺术的主要作用是再现现实中引起人的兴趣的事物。但是,人既然对生活现象发生兴趣,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出他对它们的判断;诗人或艺术家不能不是一般的人,因此对于他所描写的事物,他不能不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的新的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最后得出结论,艺术要“成为人的生活教科书”。这样以来车氏完全将艺术的内容定位于现实生活,“审美”也由形而上层面步入形而下层面,开始将审美与现实、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拉近,并切实地赋予人的审美活动以教育功能,承载一定价值规定、价值判断功能,这实际上也正是席勒的审美教育、审美文化所期待的。后来的研究者对审美文化的理解大体上没有脱离这一思路。
我们看到,席勒和车氏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让艺术承担起审美教育功能,他们两位的探索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车氏从理论上系统地阐释了审美与现实、艺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实现了二者的同一,引导人们从生活中寻找活生生的美,营造美,因此,审美本身的现实功能被强化。
相形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审美文化。中国人的兴趣素来“对于活的、直接而具体的、经验的个别情感方面则比较浓”(7),就对艺术的认识而言,中国传统艺术强调“艺术的日常情感感染和塑造作用”,如诗歌讲求“意境美”。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指出,中国美学的着眼点在于“功能、关系、韵律”、“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融合,“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着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审美活动也具有超功利性、内在性、精神性,重在感性体验、情感感受,或者说体悟。并且早在西周时期,就重视诗教与乐教,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游于艺”,即“六艺”,其中包括诗书礼乐射等。在此文化氛围之下中国传统文人也往往崇尚以“艺”为核心的知识修养和人文关怀,其中投射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底蕴。
一言以蔽之,尽管中西方文化传统、人文背景迥异,但均有悠长的审美文化传统,均致力于通过审美教育造就完整的人格、健康的人文精神。这显示出人类均有追求审美文化,以审美教育改造人心、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而在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社会,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文化研究热的兴起,以影视为主要媒介的当代大众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焦点。在实际研究中我们看到,大众文化与传统审美文化混存,审美文化概念大大地泛化,或者将现代社会分类越来越细化的诸多“文化”均简单化地包揽于“审美文化”这一大伞之下,将其直接等同于审美文化,认为当代大众文化是传统审美文化的变体;或者认为传统审美文化与当代大众文化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因此二者的关系、审美价值功能、身份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认,以寻求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二、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当下身份
膜拜自然,抵制现代文明是西方人内心久已持守的情结。身处启蒙运动之洪流的卢梭满怀对现代文明的厌弃感高唱“回归自然,寻找自我”,将孕育着人类童年时代淳朴善良天性、情感的自然与科技文明所造成的人性的异化、社会陋习、政治体制的压制等对立起来,同时也将艺术的描写对象定位于表达“自然”及其美好的情感,以此完成艺术的道德教化功能。同样处于启蒙时代的席勒针对“粗野”、“懒散”、“性格败坏”此类文明时代的弊病明确提出“审美教育”、审美文化的概念,试图用“美的艺术”培养感觉功能,完成性格的高尚化,实现救国理想。无独有偶,20世纪美籍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景况也表露了深深的忧虑:“工业社会具有一些工具,可以把形而上的东西转变成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变成外在的东西,把心灵的探索转化为技术的探索。‘灵魂工程师’、‘洗脑人’、‘科学的介入’、‘消费的科学’这些说法及其现实,以一种可怖的方式,表征着非理性的或‘精灵的’东西日复一日地被合理化,表征着对理想主义文化的否定。”(8)这里的理想主义文化与席勒的“审美文化”异质同构。马尔库塞的话并非危言耸听:现代工业社会机械文明、“技术本体化”造成人的异化,颠覆了自古希腊时代人类便始终追寻、恪守的人的生命意识、自由观念、独立性、独创性,现代文明造成非理性状态、非理性意识的泛滥。在斥责现实社会诸多弊病时他们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均为审美文化,认为只有以艺术、文学为中心的“审美之维”的革命才能从根本上造就崭新的人的心理—观念结构,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大发展,工人阶层、市民阶层等弱势群体力量的壮大,他们的话语日益凸显,从而形成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文化的多元化景观。英国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核心率先站在了文化研究热之潮头,形成“文化研究”的一些突出特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注重边缘文化、亚文化的研究,如工人阶级文化、女性文化、青少年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等的研究;以影视为主要媒介的当代大众文化是其研究核心。随着针对不同类型文化现象所进行的研究日益深入,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通俗文化诸如此类的概念应运而生,并形成以意识形态理论(如阿尔都塞文化政治、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阶级、种族、性别等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思路。文化学家更多地聚焦于身边的现实生活,如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针对新兴城市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如汤普森著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崛起》一书,而此前英国文化学家利维斯提出,现代社会的危机并非固守商品拜物教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存在于经济方面,而主要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主张借助于文学艺术作品恢复古老有机社会的价值观念,如“道德的严肃性”、“审美价值”。其他文化学家如霍加特等人尽管推崇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但仍持守传统审美文化的标准评价、“甄别”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等,认为一种堕落、时髦的文化正在取代健康、淳朴的文化。
如果追根溯源,这诸多文化现象分类、评价的共同源头当属审美文化。原因有二:就表现形式而言,均以“艺术”为审美理想,追求形式美,直接诉诸于感性体验,将艺术与生活同一,使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就表达方式而言,均为知识分子社会关怀意识、忧患意识的直接体现,上述学科性研究皆旨在对各种文化现象作出力求合理客观的诠释,引导社会健康发展。
审美文化在当今时代之重要价值不亚于席勒时代。那么审美文化与当下盛行的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的诸多文化分类,如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等处于怎样的关系链?平行?从属?必须认识到:首先,传统上提到的文化实际上以审美文化为主,其主体参照对象是高雅艺术、严肃艺术,当下的大众文化等是审美文化在当代现实语境下的一种表现形态,是文化多元化景观,是审美文化这棵古树上生发出的诸多新的枝干。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研究者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等不同角度介入文化研究领域,研究者的评价标准仍然是久已形成的“审美文化”。均以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均以“美的艺术”为核心,所持守的情结仍是对“自然”的眷恋,堪称均为“自然”与文明对立下的价值认同,只不过现代社会艺术创作、艺术品本身多样化、大众化,如以影视媒体等为主体的视频艺术日益普及,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接受更宽广、更包容,以致有学者认为现代生活有泛审美化、泛艺术化倾向。
现代艺术领域出现的一个独特景观是:艺术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只供一部分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的知识人士、上流社会人士欣赏的纯粹“美的艺术”,而是日益大众化。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往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有能力接受教育,文化水准愈来愈高;另一方面,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也涉足艺术领域,以他们的生活圈为背景创作,更加生活化的内容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此外,传统高雅艺术为了赢得更多的观众读者也一改往日清高的面孔,开始吸纳一些大众化的表现手段,这样以来,所谓高雅艺术、严肃艺术与大众艺术、通俗艺术等的界限被打破,审美文化也因此拥有了大众化品格。所谓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等便是在当下此种文化语境中产生并繁荣的。(www.zuozong.com)
其次,审美文化研究是对当下文化的批判性介入,审美文化提供了一种正面的价值评判准则。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等并没有否定、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审美文化,学者们在对当下文化做了上述划分之后对诸多文化现象予以细化解读。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诸多类型文化的出现表明社会文明极大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多样化、文化的现实表现形态的多样化,但并不代表文化内在精神的消解。
在文化研究领域研究者们或是让审美文化高高在上,恪守传统精英文化、贵族文化标准,鄙视新起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等,认为后者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代表着“文化衰落和潜在的政治混乱”(9),或是将审美文化直接等同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如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审美文化大加否定,认为“审美文化就是生活的审美化,它标志或意味着艺术与文化的商业化以及人的内在性的消解”(10)。还有一些学者则过多地渲染大众文化即现代文化的核心,渲染其所谓的后工业、后现代之消极因素。当今时代人们的文化生活的确充斥着太多“非理性”的成分,所谓高雅艺术、通俗艺术不再界限分明,而机械复制更消解了艺术品、美本身的独创性、自主性,削弱了艺术品本身的审美品格、审美精神,也使观众或读者丧失了“自由观赏”的怡然。当代高明的技术手段,影视、网络等传播工具和媒介使得艺术得到最大限度的普及,日益大众化、潮流化,人们的欣赏品味更趋于时尚化。此外,“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11)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更有甚者,影视、大众传媒、网络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范式,颠覆了传统价值观念,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当下社会有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时代之称,文化艺术品被大范围地市场化、商品化,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烈地被一种充满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复制性、平面性的感性文化引领。而当代艺术的感性化趋势也使得艺术丧失了历史感、思想的深邃,也造就了一代盲目追逐时尚,追逐平面化、感性化“审美假象”的观众和读者,被直观感受、趣味牵引的文化因此失却了“审美”的本质性特征、审美文化固有的审美教育功能,目前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均深陷于如此的困扰之中。
尽管当下文化面对着上述挑战,存在种种弊端,但也有其合理因素,那就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今天的艺术由于大众媒介的作用与观众、读者的距离很近,参与性、互动性更强,作为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艺术与生活,与生活的主人观众、读者的依赖性更强,人们也更能充分地“享受艺术”。在此纷繁态势下,如何评价、定位上述诸多文化现象,如何在对“审美文化”的理论诠释走向现实观照过程中审视传统审美文化、审美教育及其正面的影响力与社会功效,诸如此类的问题重新浮现于知识分子的研究视野。重新张扬、深化审美文化研究,以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等诸多文化“点”为切入点,以审美文化为“面”解读时代的各种文化现象,透视各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内涵,就是对当代文化的批判性介入。
(作者杜文娟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注释】
(1)参见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第2—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4页“内容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20页。
(4)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7页“内容提要”。
(5)我国学者冯至、范大灿在翻译《审美教育书简》时将“审美文化”译作“审美修养”,见该书第二十三封信,第120页。
(6)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2页“内容提要”。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17—218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8)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第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第55页。
(10)转引自李西建《审美文化》,主编张晶、副主编周雪梅:《论审美文化》,第3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第156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