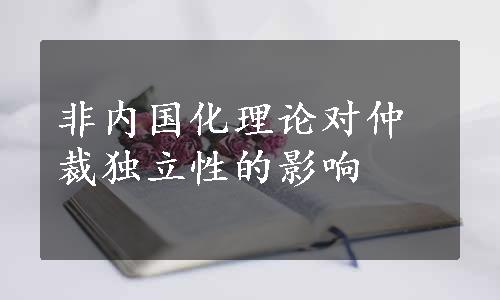
仲裁(Arbitration)作为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中最重要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出了多种具体的形式,比如国际争端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商事仲裁等等。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商事仲裁更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深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成为国际商事合同纠纷解决的重要选择。
当事人通过签订仲裁协议的方式来选择仲裁,一般体现为专门制作的仲裁协议书和主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仲裁协议书是在争议发生之后当事人就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而专门订立的,是一项独立的协议,形式上不受主合同的影响。而仲裁条款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订立的将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协议。”[3]一般表现为合同中的单独条款,与主合同在形式上联系密切。一般情况下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争议,当事人就可以通过制定仲裁协议书或者援引仲裁条款进行仲裁,并且是“一裁终局”。
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争议涉及主合同是否有效,以及合同无效和失效的情况下,仲裁条款因作为主合同的一部分能否继续有效就成为研究的重点。现在学界流行的观点是仲裁条款在此种情况下仍然具有独立性,被称之为“仲裁条款的独立原则”[4](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Arbitration Clause)。
有学者认为仲裁条款独立原则的具体含义是:“尽管仲裁条款是合同中的一个条款,但此条款与它所属的主合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如果争议涉及主合同是否存在及其有效性问题,或者主合同无效或者失效,仲裁条款作为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解决合同争议的条款,仍可独立存在,并不因主合同无效或失效而当然无效或失效,除非该仲裁条款本身依据应当适用的法律为无效协议。”[5]
仲裁条款独立原则已成为国际仲裁界理论的重要基石,不但各国的仲裁立法予以承认,在国际层面亦有仲裁案例和公约的认可。虽然我国《仲裁法》也有关于仲裁条款独立性的规定,但是在我国学术界对于独立性的理论研究尚有不足,司法界对于独立性的适用仍有待进步。
(1)仲裁条款独立性的成因探讨。首先,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是国际商事仲裁本身的特征,是商事活动的内在要求。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多数国家对于提交仲裁的合同都有商事的要求,只有商事合同才能提交仲裁解决,但是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文化的差异,对于何为“商事”分歧很大,难以在国际层面形成统一的认识,所以即使是有关国际仲裁的国际公约和示范法也多采用保留的态度对待此问题。
《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中对商事采取的是宽泛的定义。《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是目前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影响最广泛的一部示范法,对于商事,采用的是“commercial”这个词,规定为“对‘商事’一词应作广义解释,使其包括不论是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一切商事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商事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供应或交换货物或服务的任何贸易交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代理;保理;租赁;建造工厂;咨询;工程;使用许可;投资;筹资;银行;保险;开发协议或特许;合营和其他形式的工业或商业合作;空中、海上、铁路或公路的客货载运。”[6]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中对商事也采取了宽泛的定义。《通则》的目标是要制定一套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均衡的规则体系,而不论在它们被适用的国家的法律传统和政治经济条件如何。这一目标在《通则》正式文本中和这些规则所反映出的总的指导方针中都能得到体现。[7]其对于商事,采用的英文表述依然是“commercial”,规定为“对‘商事’合同的限定,并非照搬某些法律体系中对‘民事’和‘商事’、当事人和/或这两种交易的传统界定,即《通则》的适用仅依赖于当事人是否有正式的‘商人’身份,和/或交易是否具有商业性质。……《通则》对‘商事’合同并没有给予任何明确的定义,只是假定对‘商事’合同这一概念应在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以使它不仅包括提供或交换商品或服务的一般贸易交易,还可包括其他类型的经济交易,如投资和/或特许协议、专业服务合同,等等。”[8]除了将消费者合同排除在外,依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采用的是宽泛的解释。
在我国,大多学者援引《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中的定义[9],并在著作中或翻译为business或commercial[10];同样我国的国内立法中也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或者解释,只是我国在1996年加入纽约《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时提出了商事保留,即中国仅对按照中国法律属于契约性或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所谓“契约性或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具体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货物买卖、财产租赁、工程承包、加工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勘探开发自然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海上事故和所有权争议等,但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11]由此可见,我国关于“商事”的解释也是一种较为广义的解释。
笔者认为,之所以“商事”一词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没有确定的定义和范围,与国际商事活动的自身特性是密切相关的。
商业是伴随人类文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从原始的以物易物到金属货币、纸币,人类的商业活动始终在探索中前进。并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形成了不同的交易习惯,特别是当今国际商事交易更体现出广泛性和复杂性,这就使得对其下定义非常困难。商事内涵的广泛决定了商事合同类型的多样化,在当今国家间司法裁判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的情况下,国际仲裁的裁决因《纽约公约》众多加入国的事实,使得国际仲裁裁决较容易得到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正如英国退休法官Michael Kerr先生比喻,即便是太空人仲裁员在月球上做出的裁决,也可以在英国得到执行。[12]
而商事交易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和交换行为”[13],故追求效率、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商事交易的特征,故客观上要求若发生争议当事人愿以更加经济、更加快捷的方式来解决,在这方面仲裁相对诉讼来讲,更显优势。同时仲裁更以其专业性和友好性更加符合商事争议的解决,这就使得商事合同中当事人对仲裁更加青睐。
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就表明了当事人希望若发生争议希望通过仲裁的方式,而不是诉讼的方式解决,且如今多数国际间的买卖合同都是采用仲裁条款的形式来解决争议,[14]在这种情况只有保持仲裁条款的独立才可以更好保证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愿得到实现。
其次,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是国际商事仲裁本身的特征,也是国际性商事交易的客观要求。
商事仲裁一般区分国内商事仲裁和国际商事仲裁,从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来看,后者在受案范围、受国内法院影响和仲裁裁决的执行等方面受到的限制都比较小,之所以有此区别,是由国际商事合同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在第一章第1条第3款就指出了国际仲裁,“仲裁如有下列情况即为国际仲裁:(A)仲裁协议的当事各方在缔结协议时,他们的营业地点位于不同的国家;或(B)下列地点之一位于当事各方营业地点所在国以外:(a)仲裁协议中确定的或根据仲裁协议而确定的仲裁地点;(b)履行商事关系的大部分义务的任何地点或与争议标的关系最密切的地点;或(C)当事各方明确地同意,仲裁协议的标的与一个以上的国家有关。”可见,这个定义使得符合条件的仲裁是非常宽泛的。
在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7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65条、2005年《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来看,我国对“国际”或者“涉外”的商事仲裁的认定基本采取争议性质标准,即以争议的国际性或者涉外性来确定有关的仲裁是国际(涉外)仲裁还是国内仲裁。同时对于何种争议具有国际性或涉外性,则做广义的理解,“即只要民商事争议的主体、客体、内容三个因素中至少一个与中国内地之外的法域相联系,就构成所谓的国际性或涉外性。并且考虑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属于实行独特法律制度的与内地平行的三个法域,有关涉及这三个法域的仲裁可归为涉外仲裁或区际仲裁,并可参照适用有关国际或涉外仲裁的法律规定。”[15]
对于国际的定义坚持广泛性的标准,从客观上增加了符合国际仲裁的合同的数量,使得更多的合同可以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同时由于世界上已经有140多个国家加入《纽约公约》,也就意味着一国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可以在这140多个国家执行判决,可执行的范围远远大于诉讼判决,这也是大多数涉外合同选择仲裁的根本原因。
故商事交易的特性和国际的宽泛定义客观上要求更广泛的适用仲裁解决国际商事争议,而仲裁条款独立性的存在能够更大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实现。
(2)仲裁条款独立性理论发展脉络也通过案例的形式体现出来。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通常认为仲裁条款的独立性研究是按照如下脉络发展的,首先,1942年英国法院审理了荷曼诉达文斯(Heyman v.Darwins Ltd.)一案,在本案中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在合同落空的情况下,仲裁条款可以独立存在;其次,1963年,法国最高法院在高赛特(Societe Gosset v.Societe Carapelli)案中,确立了主合同因不能履行而无效时,仲裁条款独立的原则;接着,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马里兰州的首家涂料公司诉新泽西州弗拉德与康克林制造公司(Prima Paint Co.v.Flood&Conklin manufacturing Co.)案中确立了在主合同因欺诈而无效时,仲裁条款仍具有独立性;最后,1993年,英国法院通过海港公司案(Habour Assurance Co.v.Kansa General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Co.),确立了在主合同因违法而无效时,仲裁条款仍具有独立性。
研究仲裁条款的独立性问题,起源于西方的商事仲裁案例,那么我们就重新审视这几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1942年英国上议院审理的Heyman v.Darwins Ltd.一案,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被称为仲裁条款独立性的理论起源。本案涉及一个包含有广泛仲裁协议的合同有效签订之后,因Darwins公司没有实际履行双方产生争议,原告Heyman等人诉至法院,被告英国Darwins公司申请仲裁。
但是最终上议院西蒙大法官(Viscount Simon)提出如下意见:“If,however,the parties are at one in asserting that they entered into a binding contract,but a difference has arisen between them as to whether there has been a breach by one side or the other,or as to whether circumstances have arisen which have discharged one or both parties from further performance,such differenc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differences which have arisen‘in respect of’,or‘with regard to’or‘under’the contract,and an arbitration clause which uses there,or similar,expressions should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意为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坚持认为他们已经签署了有拘束力的合同,但是他们之间的争议是关于其中一方当事人是否违约,或者是否存在着一方当事人不再继续履行或者双方当事人都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这样的争议应被视为是与合同有关的争议。
另一段话“I do not agree that an arbitration clause expressed in such terms as above ceases to have any possible application merely because the contract has‘come to an end’,as,for example,by frustration.In such cases it 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that has come to an end….There is a previous decision of this House which establishes this precise proposition.I refer to Scott&Sons v.De;Sel(1923),where sellers of jute contended that a contract to export from Calcutta 2,800 bales to Buenos Aires was brought to an end,after a portion has been dispatched,by a government prohibition of further export,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contract contained an express term exempting the sellers from liability for late delivery due to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The arbitration clause ran:‘Any dispute that may arise under this contract to be settled by arbitration.’”这一段话西蒙大法官反对仅仅由于合同终结就导致措辞广泛的仲裁条款不能适用的观点,并通过援引先前案例的形式来进一步阐明即使合同“终止”,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仍应被适用。这样上议院就得出了在本案中仲裁条款可以适用的结论。
但是判词中还有一段话“If the dispute is as to whether the contract which contains the clause has ever been entered into as all,that issue cannot go to arbitration under the clause,for the party who denies that he has ever entered into the contract is thereby denying that he has ever joined in the submission.Similarly,if one party to the alleged contract is contending that it is void ab initio(because,for example,the making of such a contract is illegal),the arbitration clause cannot operate,for on this view this clause itself is also void.”在这段话中,西蒙法官明确表达了如果争议是关于合同是否有效签订,或者合同因违法而无效,那么在此种情况下仲裁条款是不具有独立性的,因为仲裁条款应随着自始无效或违法合同而无效。
故本案例只是说明了一个有效成立的合同,在履行过程发生争议时仲裁条款能否有效的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仲裁条款是当然发生效力的,这也正是案件中法官说到“the case was‘a very simple one’”,根本不涉及仲裁条款的独立性问题。同时西蒙法官在判词中明确表示了在主合同是否有效签订和自始违法的情况下,仲裁条款是当然不具有独立性的,语言中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对仲裁条款的独立性的反对,所以把本案例作为仲裁条款具有独立性的理论起源是不恰当的。
第二个案例,在1963年,法国最高法院在高赛特案中确立了仲裁条款独立的原则。本案涉及法国公司(Gosset,买方)与意大利公司(Carapelli,卖方)订立的含有仲裁条款的粮食买卖合同,后因关于仲裁产生争议法国当事人上诉到法国最高法院,主张主合同及其所包含的仲裁条款由于不能履行而无效,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在国际仲裁中,国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完全独立的,即使主合同无效时亦然。[16]
第三个案例,在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Prima Paint co.v.Flood&Conklin manufacturing co.一案,确立了仲裁条款可独立存在于自始无效的欺诈合同。本案涉及马里兰州的Prima Paint买下了新泽西州F&C生产涂料的生意,并签订咨询协议,规定由F&C向Prima Paint提供相关的业务咨询,该协议中含有措辞广泛的仲裁条款,后因F&C宣告破产双方就费用支付问题产生争议,Prima Paint主张F&C在订立协议时有欺诈行为,因此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而诉诸法院。美国最高法院最后确认:即使合同自始无效,通过仲裁解决合同争议的仲裁条款,同样也是一项可以独立实施的协议。[17]
第四个案例,1993年,英国上诉法院审理了海港公司案,即Habour Assurance Co.v.Kansa General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Co.一案。本案涉及芬兰一些保险公司为了打入英国的保险市场,与英国海港公司订立了在英国从事保险和再保险活动的保险协议,合同中含有仲裁条款。后因根据英国国内法规定,在英国从事保险活动,必须取得英国工商局的认可,而本协议未取得英国工商局的认可,英国海港公司主张由于违反英国的法律,该协议无效,而提交诉讼。最后上诉法院民事庭审理后认为:即使合同因违反法律而无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依然可以独立实施。[18]
通过对以上法、美、英等国的司法判例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主合同因不能履行而无效,因欺诈而无效,因违反法律而无效都不能影响合同中有效成立的仲裁条款的效力,仲裁条款具有独立性。(www.zuozong.com)
(3)国际商事合同仲裁条款独立性的学理解读。从学理角度分析国际商事合同仲裁条款独立性:仲裁条款之所以具有独立性,除了现实的需要外,从学理上也可找到依据。
首先,仲裁本身具有“合同性”的特征,商事仲裁亦不例外,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仲裁协议的签订意味着双方同意把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因此即使在合同无效或失效时,仲裁条款具有独立性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
其次,我们通过研究可发现,从合同内容的构成角度上分析,一个国际商事合同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实体性部分和程序性部分,这两本部分规定的内容和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英国Macmillan法官曾明确指出,仲裁协议与商事合同其它条款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商事合同其它条款规定的都是当事人之间相互承担的义务,而仲裁协议规定的不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义务,它是双方当事人的协议,即如果产生了有关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承当的义务的争议,则这些争议将由他们自己成立的法庭解决。”[19]实体部分解决实体问题,不同的合同是基本不同的;仲裁条款属于程序性部分,特别是仲裁条款在争议发生之前制定,一般比较宽泛,具有形式基本一致的特征,正因为如此,这部分实质上具有独立性。
(4)仲裁条款独立性的精确表述及其相关的跟随性问题。仲裁条款独立性的理解:仲裁条款作为主合同相对对立的一部分,应该有其自身的成立要件,笔者认为应当包括:A、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B、当事人意思表示明确。只要符合这两点,我们就认为当事人就仲裁条款达成合意,仲裁条款就有效成立了。
有效成立的仲裁条款的效力表现为:A、当事人可直接依此仲裁协议提交仲裁,而排除法院的管辖;B、仲裁员可直接依据仲裁协议的规定对合同的争议作出裁决,当事人必须遵守。
故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可表述为:在不涉及影响公共秩序问题时,作为主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符合其构成要件即成立,其有效性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
首先,仲裁条款独立性的立法现状研究。随着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被各国法律吸收和在仲裁中的广泛运用,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国际公约的方式认可此原则。首先是《纽约公约》,虽未就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作出专门规定,但公约第2条(1)款则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应承认当事人之间书面达成的将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争议交由仲裁解决的协议(即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其次,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1985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1款对仲裁条款独立原则作了表述:“仲裁庭可以对它自己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出裁定。为此目的,构成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视为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以外的一项协议。仲裁庭作出的关于合同无效的裁定,不应在法律上导致仲裁条款无效。”最后,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体现在了许多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修改了他们的仲裁规则,比如国际商会仲裁院1988年仲裁规则第8条(4)款,1985年1月1日起实施的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4条(1)款,美国仲裁协会1991年3月1日起实施的国际仲裁规则第15条(2)款,俄罗斯国际商事仲裁院1988年仲裁规则第1条(3)款,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1991年仲裁规则第25条1款,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仲裁与调解程序规则第15条(1)款等。[20]
我国《仲裁法》第19条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同时,我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第5条第4点规定:“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视为与合同其他条款分离地、独立地存在的条款,附属于合同的仲裁协议也应视为与合同其他条款分离地、独立地存在的一个部分;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转让、失效、无效、未生效、被撤销以及成立与否,均不影响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效力。”
综上所述,仲裁条款独立原则已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普遍接受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
其次,仲裁条款具有独立性而导致的跟随性(subsequence of arbitration clause)问题。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将其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第三人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如果合同中有仲裁条款,当合同向第三当事人转让后,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也向该第三人转让?并且在特定情况下,仲裁条款的效力出现了扩展的情形和趋势,不少国家的立法、司法和仲裁实践、仲裁理论逐步承认仲裁协议对未签字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仲裁协议的“胳膊”正在“伸长”。[21]
当今世界范围内关于仲裁协议转让的问题,分为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仲裁条款与主合同可以同时转让,除非受让人在接受该合同时对此提出异议,在美国、法国、瑞典、瑞士等国有相关的法律明文规定或判例。此意见的主要依据是:“仲裁协议作为主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属于合同的附属权利。这种权利类似于合同中对法院的选择条款,是从属于合同项下的权利,在随主合同转让时,同样具有合同的后果。因此,仲裁条款项下的权利应当与合同其他条款项下的权利处于相同的法律地位,受附属权利转让规则的支配。”[2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仲裁条款与其所依据的主合同不能同时转让,除非当事人同意此项转让,在纽约州、意大利等国有相关的法律明文规定或判例。此意见的主要依据是:“第一,仲裁条款项下的权利是程序上的权利,而不是合同的实体权利,因而不能受支配合同权利的规则的约束。第二,在一些国家法院的判例中,尽管对仲裁协议的实体或程序上的权利不作区分,但认为仲裁条款项下的权利属于个人的权利,因而不能适用于一般的转让原则。第三,仲裁协议不仅包括当事人的权利,还同时包括相关的义务,即不得将协议项下的争议提交法院解决的义务,因此当事人在转让合同的实体权利时,对于仲裁条款项下的义务,如果没有受让人的明示同意,则不能转让。”[23]
正是由于在仲裁协议转让的问题上,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立法并没有涉及,所以各国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都依据各国的国内法律去处理,往往会依据不同的理论导致不同的结果。
仲裁协议具有的独立性的特征,已经被各国的仲裁法吸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仲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发现,仲裁协议在主合同涉及权利义务转让时的情况下,展现出与独立性相对应的、能够归纳总结的另一种特征。我们将这种特征,用“仲裁条款的跟随性”予以表述。
所谓“仲裁条款的跟随性”,是指仲裁条款作为主合同的从属,在主合同因一定的原因发生权利义务转移或效力扩展后,仲裁协议作为解决主合同争议的条款,也发生转移或扩展,并继续存在法律效力的情形。
其逻辑思路是这样的,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已经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国际公约的认可,认为仲裁条款有其自身的构成要件,主合同的效力变化不会影响到仲裁条款的效力,只要合同当事人符合仲裁条款的构成要件,仲裁条款就在相关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效力。
而仲裁条款是作为主合同的一部分而体现的,是主合同中关于解决问题的程序性规定,在形式上包含在主合同当中。那么当主合同转让时,受让人必定是要关注合同的,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理性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连合同内容都不去看的国际商事交易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事人不可能不知道合同中所包含的仲裁条款的存在,如果当事人在明确知晓仲裁条款存在的情况下,同意主合同的转让,就表示当事人不但同意权利义务的转让,也符合仲裁条款的构成要件,从而成为新的合同的当事人,即为转让后仲裁条款的当事人。故可以总结为,除非当事人明确表示反对主合同中存在的仲裁条款,当主合同权利义务发生转移时,仲裁条款跟随转让,适用于新的当事人之间,此可称之为仲裁条款的跟随性。
在明确了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和跟随性之后,我们发现其实现实中很多理论和实践是此理论的佐证的。
第一,合同转让。根据合同转让的权利义务不同,合同转让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合同的承受、债务承担和债权让与。在合同承受的情况下,普遍认可的一个规则是仲裁条款“自动移转规则”[24]。根据该规则,合同的转让人经合同另一方或者其他方当事人的同意,将其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概括移转给受让人,如果原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该仲裁条款对合同的受让人与合同的其他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除非受让人或债务人在合同转让得到合同通知时明确反对仲裁条款继续适用。
在债务承担的情况下,各国民法一般都规定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前提条件是债权人的同意。因此,只要债务承担有效成立,即可以表明债权人已充分权衡过其与受让人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情形并同意继续使用仲裁协议。对受让人而言,只要实际履行了主合同项下的义务,则受让人就必须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25],即受让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说明了他自愿接受仲裁协议。仲裁协议在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继续有效。
在债权让与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着债权让与生效自由主义和折中主义的立法例,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采用这样的立法,即债权人转让债权给受让人时,不需要经过债务人的同意,而只需要将债权转让情况通知债务人(折中主义),甚至不必通知债务人(自由主义)。那么仲裁条款在债务人无权发表意见的情况下,能否跟随债权的转移而转移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数的国家和地区确定和认可了在债权让与的情况下,仲裁条款可以将其效力延于原合同债务人和合同受让人。
第二,代理。仲裁条款的跟随性于代理制度中的主要表现为,当英美法系中未披露本人代理的情况下,存在着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当委托人或第三人在法定的条件下行使这样的权利并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时候,仲裁条款随着主合同中权利的转移而转移约束非签字方。在英美法系披露本人的代理、大陆法系直接代理及表见代理的情况下,代理制度本身的特征决定了非签字方,即被代理人受到仲裁协议的约束。
第三,代位。在代位的情形下,仲裁条款的跟随性体现在代位权人和原债权人之间权利义务转让后,仲裁条款也随之发生转移。在因主合同发生争议的情形下,对原债务人而言,其面对的代位仲裁请求并不会发生实质变化,因为争议的范围还是原来的范围,内容也还是原来的内容。反过来说,原债务人在签订仲裁协议的时候,就放弃了通过以仲裁方式之外解决争议的权利,代位人行使仲裁权,恰恰不会对原债务人的上述权利造成实质影响。仲裁协议的跟随性在代位理论下得到了较好的支持。
第四,揭开公司面纱。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是公司人格独立性的例外情形,在适用这一制度时,需要严格把握,不能轻易使用,更不能滥用,否则将动摇整个法人制度的确定性。推及至仲裁领域,仲裁协议因揭开公司面纱而产生跟随性的效果也是例外规则,而不是要去动摇仲裁制度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根本原则。另外,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中关于滥用公司人格的标准,没有也无法划出是和非的具体界线,目前只能由法院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和具体掌握。因此要通过仲裁真正“揭开公司面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从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降低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乃至维护法律的尊严等方面来说,仲裁协议在公司人格否定的情况下跟随主合同将效力延及幕后的第三人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五,禁反言。《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一般法律原则”作为法院裁判案件应该适用的法律依据,学理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的这一条表明了国际法的渊源。而对于“一般法律原则”的理解中占有说服力的是将其理解为:世界各大法系共有之原则。即公平原则,还有这里的禁反言原则等等。即世界各主要法系都普遍承认禁反言原则。一般认为,仲裁协议因禁反言原则体现跟随性的情形属于特例,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美国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对禁止反言原则的运用仍存在争议,主要的观点包括:禁反言原则违背合同法中关于当事人合意的要求,将未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强行拉入仲裁中,无视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法院有将禁反言原则作为万金油的嫌疑;禁反言原则的适用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即原告必须放弃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且与从未同意仲裁的人就争议进行仲裁。[26]因此,就像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一样,对禁止反言原则在仲裁中的运用要严格考量,谨慎判定,以真正实现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价值。
除了前文中介绍的五种理论,还有一些理论学说支持和解释着仲裁协议的跟随性,而且随着仲裁制度和司法实践的发展而随之变化着,比如提单的转让,第三方受益人,公司人格混同、公司集团,法人的合并与分立等不同程度体现了仲裁条条款的跟随性的特征。
在仲裁制度高速发展的今天,仲裁协议体现出跟随性的特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越来越多地在仲裁和司法实践中运用。对于此,欧美一些仲裁制度发达的国家走在了前列,他们运用实体法中创设的一些理论来解释仲裁协议在特定的情形下跟随主合同权利义务转移或扩展而转移和扩展,并通过一系列判例的形式加以确认。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传统的仲裁理论坚持者对仲裁协议跟随性表示否定的态度,但是我们需要透过这些传统的理论去探求仲裁的本质,去追求仲裁制度诞生的目的和至今具有不懈生命力的原因。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仲裁协议的跟随性并不是为了否定传统,相反是为了适应现代民商事发展中仲裁协议当事人越来越大的需求,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坚守仲裁制度诞生的目的和延续其不懈的生命力。
(5)对我国国内商事仲裁的启示。我国现行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真正建立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27],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主要表现为涉外商事仲裁案件的增多和对国际商事仲裁理论的吸收和影响增强。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了我国商事仲裁的主要目的,这就使其具有“中国商事仲裁制度不以盈利为目的,其宗旨是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28]的特征,区别于中介机构的律师事务所等。所以研究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就要立足我国的实际,借鉴国际的先进经验,从而促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
我国的国内商事仲裁因为受到国内司法的更多的限制,在仲裁条款独立性及跟随性方面实践的还不够,但是国际商事仲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理论前景,是国内商事仲裁发展的引导方向,同时对国内司法对仲裁的让渡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6)该理论受“非内国化”理论的影响。笔者认为,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和跟随性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国际商事仲裁一体化的形成。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和跟随性与“非内国化”理论在效力根源上有相同之处,都部分来源于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私权利的处分,并且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和跟随性可以从客观上促进“非内国化”理论的实现,更进一步的促进国际商事仲裁一体化的实现。同时,在“非内国化”理论的影响下,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和跟随性更容易在仲裁实践中被践行,两者可以认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非内国化”理论强调当事人的自主意思,选择自己信赖的仲裁员来处理纠纷,且许多国家的仲裁法对仲裁员规定了较高的准入门槛,水平相对较高;纠纷的处理程序,包括程序性和实体性法律都是由当事人自己选择;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员能独立做出判断,受到法院等外部因素的干扰较小,在这样的前提下,笔者认为所得的仲裁裁决对当事人是公正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