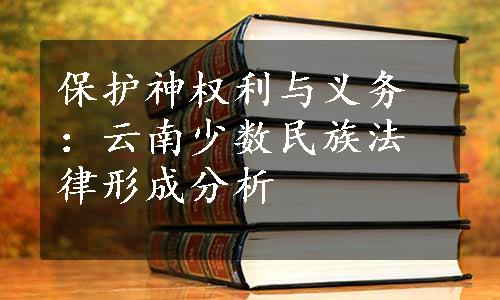
一般认为,宗教保护神的观念及由此规定的当事人双方的主观权益和义务要求,是最古老的私法类型的源头,因为建立在宗教保护神基础之上的任何特别的法律制度,例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土耳其的法,规定了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事实。
我们发现,云南各少数民族神话故事、史诗歌谣、民间传说等文本里的神话人格就是宗教精神影响法律思想形成的最好证据。例如神秘的、超自然的人格神在哈尼族神话《三个神蛋》里被提到过:先祖莫元时代,人们还不会栽田种地,人世间很乱,没有人管事。天神摩咪就叫神鸟下了三个神蛋,有一只大黑母鸡来孵这三个神蛋,孵出了三个男人,他们是咪谷、贝玛、工匠三种能人。从此,他们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使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311]另外一个神话故事《三个能人》谈到太阳和月亮共同下了三个巨大的蛋,它们是白色的、花色的和红色的。之后,由天地来孵,他们就是哈尼族社会中的咪谷(头人)、贝玛(摩匹)、工匠三种能人。[312]实际上,今天我们所见由咪谷发展而来的寨神,即是哈尼族村寨共同祭奉的神灵,咪谷死后自然成为本家庭内被供奉的神灵,同时也将成为村寨的神灵,[313]也承担了保护神的职能。此外,神龛是元阳县一带的哈尼族家庭供奉祭品和祭祀祖灵的神圣所在,作为同一个祖先神的后代,人们在这儿祈求神灵庇佑全家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跟汉族传统家庭里供桌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傣族人家普遍把祖先的亡灵作为家神崇拜,建神柱、设神龛祭献,并且相信家神能保佑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家畜平安、庄稼丰收。“寨神”“勐神”是傣族村民的更高层级的祖先,傣语通称为“帝娃拉曼”“帝娃拉勐”。有一句俗话说:“家长死后当家神,寨子首领死后当寨神,勐的首领死后当勐神。”所以,没有家神、寨神、勐神,则家不成家,寨不成寨,勐不成勐。这些神灵都有各自的神话起源,常与傣族的建寨和建勐历史相关。由于勐神与寨神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能体现神位尊卑的还是各地敬神用的蜡条数量。例如敬寨神用4对蜡条,敬勐神用8对蜡条(最多献12对)。在彝族《苍蝇的金顶和老牛的粗心》的神话故事里,事实上,天神“格兹”(作为最高等级的大神)只是《虎公虎母造万物》中造天地、造日月、造人类的老虎,以及《修天补地》里的大力士牛牛依和牛牛慈哈,《神主头的来历》中的神主头、《尼苏夺节》中的“祖母树”(动植物图腾神)、《开天辟地(一)》中的俄罗布、《少数民族分支》中的白胡子老人、《三月三》中的摩根生老人、《木甸罗土主的传说》中的木甸落、《天子庙》中的段思平、《玉峰寺》中的阿玉和玉花、《正月初六祭土主》中的罗黑公公和塔凹奶奶、《兴修水利泽润民生》里的彝族头人,还有《姑奶奶的传说》里的“松川雄威土主”和他的妻子“土主阿婆”等今日我们所知彝族社会里各种人格祖先神的综合体,或者说是各种祖先神综合体人格化的产物。
我们知道,相较于较低等级受到祭拜的祖先神,大神虽然是较高等级的神,但是他们的力量和功能毕竟更强更大,有时甚至他们中的某几位还具有族际神的性质。哈尼族神话《四个民族是怎样分家的》提到汉、傣、哈尼、拉祜四个民族都是折妈赞所生,哈尼族是老大,汉族是老二,拉祜族是老三,傣族是老四;折妈赞领着四个儿子,早出晚归,辛勤劳动,日子过得很清苦。[314]这儿的折妈赞正是跨越汉、傣、哈尼、拉祜四个民族的族际神。《分地皮的传说》讲傣族和哈尼族在划分河中的鱼、山中的兽、水田、山地以前,祭拜相同的神,因为观念相同,彼此相处得十分和睦。[315]《僾尼上山的传说》告诉我们今日住在坝子里的僾尼人跟傣族因为宗教观念相同,也曾经像一家人一样生活着,傣族像大哥,僾尼人像弟弟。兄弟俩一个爱山,一个爱水,早出晚归,和和气气地住在一起。[316]此外,前面提到过的彝族的天神格兹、哈尼族的莫咪或称烟沙天神、傈僳族的天神木布帕,今天多少还保留着族际神的影子。而这些族际神不同于普通的大神,因为他们的地位、力量和能力比大神还要高得多,哈尼族神话《佐罗和佐卑》叙述天、地、人诞生后,世间成了天上、地上和地下三层世界。那时候许多较低等级的大神天天到人间游玩,有的违反天规地律,久居人间。例如天神不归天庭,地神不回地府,还相互争夺管理人间的特权,以至于天天争吵打斗,使大地无宁日,最后惹恼了最大的天神烟沙和色拉,而对他们做出处分的决定。[317]所以,作为特别重要的祖先神灵,彝族的“格兹”和哈尼族的天神“莫米”、傈僳族的天神“木布帕”,以及傣族的天神“桑嘎西和桑嘎赛”等最高等级的大神都有着相类似的特点,他们像今天我们熟知的某些高级宗教里那些神秘的、超自然的人格神一样。例如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真主。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神话故事、史诗歌谣、民间传说等文本里的这些最高等级的大神正是村寨等地区司法审判中头人、祭师们依据的合法性来源和法律最高权威的终极理性象征,因为这些大神常常给司法审判中的这些“法官”们作出“神谕”或“指示”。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各少数民族神话里的这些神圣人格在活着的时候往往就具有了某些不同寻常的力量。彝族神话《少数民族分支》讲起初生下来的人都不会说话,后来在一位白胡子老人(代表神圣人格)的指点下,老三(代表“法官”)用山竹抽打他们,这些孩子就神奇地学会了彝语、汉语等语言,并成为现今各民族的祖先。《三月三》讲很久以前紫云峰下发生了一场大瘟疫,人畜死了无数。此时,从紫云峰顶上下来一位名叫摩根生的老人(代表神圣人格),他在山脚建起房子,一边修行一边为人畜治病;灾难过去后,为了缅怀报答摩根生老人,人们就在这里修了一座庙供奉他,形成要过“三月三”的宗教节日习俗。[318]《木甸罗土主的传说》讲被人们供奉的上河甸土主叫 罗(代表神圣人格),他是南诏第五代君主阁罗凤的长子凤伽异,此人生前能征善战、有威望、屡建战功,但死于其父前,没能在金殿上落位,故称“没殿落”,后人音译为“木甸罗”。[319]《天子庙》讲述天上派来的天子段思平(代表神圣人格)除大蟒有功,人们在其死后为他在年景村后天寿山建殿塑身,殿宇被命名为天子庙。此后,每年六月十三日,西乡坝子的乡亲都要来朝拜,并杀猪宰羊纪念。[320]《玉峰寺》讲述穷汉子阿玉得到白发老人的咒语和长剑,与妻子玉花一起除掉巨蟒后,化为两座高山;后人为怀念这对青年(代表神圣人格),就把两座山分别称为玉山和玉峰,还建了庙,塑了他们的像,世代供奉,以他们除蟒的三月初一作为庙会日。[321]《正月初六祭土主》讲述峨碌甸的罗黑公公和塔凹奶奶(代表神圣人格)是寨中长者,曾经组织大家英勇抵抗南诏王的进攻,战死后,成了峨碌甸彝族的土主,塔凹奶奶后被清朝雍正皇帝加封为“西灵圣母”。[322]《兴修水利泽润民生》讲有一年新兴(今玉溪)坝子连下大雨,积水成灾。有个姓普的彝族头人(代表神圣人格)亲自到处游说宣讲,安定民心,并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避免灾难和混乱,疏浚河堤,最后累死了。后人把他封为土主神,专管水利,并在其土主庙执事牌上写下“兴修水利”“泽润民生”的字样。至今,每逢米线节迎土主时,两块执事牌必定作为前导。[323]《姑奶奶的传说》叙述吕合附近土官村的土官家有一位猎人(代表神圣人格)因杀死金牛怪为民除害,自己也壮烈牺牲,被人们尊为“松川雄威土主”;他的妻子被称为“土主阿婆”(也代表神圣人格),后来“土主阿婆”教会大家采药治病,扑灭瘟疫,她死后,吕合一带的彝族也在土主庙里为她塑像,让她接受供奉。[324]白族神话《牟伽陀开辟鹤庆》提到牟伽陀(代表神圣人格)活着的时候是西藏王父派遣前往大理与白王结盟的使者,路上他见鹤庆汪洋一片,就想为民排水开田。后来,他到鹤庆金斗山上修炼,练就了擒龙治水的本领,终于制伏了穷凶极恶的蝌蚪龙,开辟了鹤庆坝子。[325]傈僳族神话《王鄂的故事》讲大力士王鄂(代表神圣人格)凭着一身好力气,能把一块三四个人才抬得动的石板夹在腋下从容行走,可以用手指头弹死老虎、勒死石牛,还能用双手把大树撕开,乡亲们都很崇拜他,他死后变成了神。[326]哈尼族神话《惹罗大寨的五个能人》讲建立惹罗大寨的第一个能人是女首领朝者阿玛,她教会哈尼人用绳子拉成四方形,顺着四方形挖沟砌石脚盖房子;第二个能人是阿烟首领的姑爷佐斗,他发明了打铁、拉风箱、炼银子;第三个能人是把裤脚卷得高高的咪督,他教会哈尼人栽田种地;第四个能人是果都阿玛,她是第一个教会哈尼人种水稻的人;第五个能人是牙依,他开沟引水浇灌大田,保证田里一年四季水源充足。[327]《田四浪造反》提到,田四浪是清咸丰年间率众起义的哈尼族领袖(代表神圣人格),自幼就臂力过人,武艺超群,而且锄强扶弱,深得民心,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英雄事迹的传说。[328]类似的神话故事还有《策打》[329],等等。
罗(代表神圣人格),他是南诏第五代君主阁罗凤的长子凤伽异,此人生前能征善战、有威望、屡建战功,但死于其父前,没能在金殿上落位,故称“没殿落”,后人音译为“木甸罗”。[319]《天子庙》讲述天上派来的天子段思平(代表神圣人格)除大蟒有功,人们在其死后为他在年景村后天寿山建殿塑身,殿宇被命名为天子庙。此后,每年六月十三日,西乡坝子的乡亲都要来朝拜,并杀猪宰羊纪念。[320]《玉峰寺》讲述穷汉子阿玉得到白发老人的咒语和长剑,与妻子玉花一起除掉巨蟒后,化为两座高山;后人为怀念这对青年(代表神圣人格),就把两座山分别称为玉山和玉峰,还建了庙,塑了他们的像,世代供奉,以他们除蟒的三月初一作为庙会日。[321]《正月初六祭土主》讲述峨碌甸的罗黑公公和塔凹奶奶(代表神圣人格)是寨中长者,曾经组织大家英勇抵抗南诏王的进攻,战死后,成了峨碌甸彝族的土主,塔凹奶奶后被清朝雍正皇帝加封为“西灵圣母”。[322]《兴修水利泽润民生》讲有一年新兴(今玉溪)坝子连下大雨,积水成灾。有个姓普的彝族头人(代表神圣人格)亲自到处游说宣讲,安定民心,并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避免灾难和混乱,疏浚河堤,最后累死了。后人把他封为土主神,专管水利,并在其土主庙执事牌上写下“兴修水利”“泽润民生”的字样。至今,每逢米线节迎土主时,两块执事牌必定作为前导。[323]《姑奶奶的传说》叙述吕合附近土官村的土官家有一位猎人(代表神圣人格)因杀死金牛怪为民除害,自己也壮烈牺牲,被人们尊为“松川雄威土主”;他的妻子被称为“土主阿婆”(也代表神圣人格),后来“土主阿婆”教会大家采药治病,扑灭瘟疫,她死后,吕合一带的彝族也在土主庙里为她塑像,让她接受供奉。[324]白族神话《牟伽陀开辟鹤庆》提到牟伽陀(代表神圣人格)活着的时候是西藏王父派遣前往大理与白王结盟的使者,路上他见鹤庆汪洋一片,就想为民排水开田。后来,他到鹤庆金斗山上修炼,练就了擒龙治水的本领,终于制伏了穷凶极恶的蝌蚪龙,开辟了鹤庆坝子。[325]傈僳族神话《王鄂的故事》讲大力士王鄂(代表神圣人格)凭着一身好力气,能把一块三四个人才抬得动的石板夹在腋下从容行走,可以用手指头弹死老虎、勒死石牛,还能用双手把大树撕开,乡亲们都很崇拜他,他死后变成了神。[326]哈尼族神话《惹罗大寨的五个能人》讲建立惹罗大寨的第一个能人是女首领朝者阿玛,她教会哈尼人用绳子拉成四方形,顺着四方形挖沟砌石脚盖房子;第二个能人是阿烟首领的姑爷佐斗,他发明了打铁、拉风箱、炼银子;第三个能人是把裤脚卷得高高的咪督,他教会哈尼人栽田种地;第四个能人是果都阿玛,她是第一个教会哈尼人种水稻的人;第五个能人是牙依,他开沟引水浇灌大田,保证田里一年四季水源充足。[327]《田四浪造反》提到,田四浪是清咸丰年间率众起义的哈尼族领袖(代表神圣人格),自幼就臂力过人,武艺超群,而且锄强扶弱,深得民心,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英雄事迹的传说。[328]类似的神话故事还有《策打》[329],等等。
需要提及的是,作为婚姻制度早期的立法者和裁判者,这些神圣人格也是人间早期婚姻生活的道德来源和最早婚姻法制定的依据。哈尼族神话《哈巴卡的传说》讲到天神摩咪派仙女下凡,教人们唱规矩歌,使人们知道了男婚女嫁,知道人与人要和睦相处的道理。[330]《点云》讲述,有个仙人托梦告诉洛奇洛耶,要想娶到扎斯扎依,就要去布竜大悬崖子砍来马桑果树做成牛腿似的“点云”乐器,唱歌给她听。[331]傣族神话《人类果》中讲有个天神如何变成一条绿蛇,引诱守护果园的贡神和曼神偷吃人类果,失去神性,变成凡人。又教他俩吃生殖果,使之有了生殖器,结为夫妻、生儿育女。[332]《布桑戛西与雅桑戛赛》提到,开创天地的英叭神王很后悔没有开创人类,就命令布桑戛西与雅桑戛赛说:“你们俩下到大地上,在那里开创人类。”[333]显然,在这些故事里,彝族的天神、白胡子老头、观音老母等神圣人格,哈尼族的天神摩咪、神话中的仙人等人格神,傣族变成绿蛇的天神、英叭神王,都是早期婚姻法制度的订立者。而在许多云南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例如彝族的《独眼人、直眼人和横眼人》《创世纪》《葫芦里出来的人》《复先(伏羲)兄妹配人烟》《阿霹刹、洪水和人的传说》[334]《浑水湮天》[335]《洪水冲天》[336]《两兄妹造人烟》[337]《兄妹成亲》[338]《人类的起源》[339]《洪水淹天的故事》[340]《兄妹传人》[341]《兄妹创人烟》[342]《兄妹成婚》《金龟老人传人类》[343]等等,虽然故事叙述的细节多有不同,但是讲述的共同之处几乎都是:上天用洪水毁灭人间后,有俩兄妹根据“神谕”结婚,这些“神谕”或来自天神、或来自白胡子老头、或来自观音老母等神圣人格,他们繁衍人类,成为人类始祖。
显然,这些决定人间婚姻关系的祖先神,他们最初的职责是确保人间的繁衍和人种的延续。彝族神话《格兹嫁女儿》讲述人间第二次洪水后,世上只有笃阿慕一家,长子达方成人后,因世间无女子无法婚配,天神格兹不得不忍痛割爱把闺女生杜嫁至人间与笃阿慕长子达方成亲。之后,人间才有儿有女,格兹才断了天地成婚之事。[344]《十格子找人种》讲洪灾之后,天帝专门派神仙十格子(即天神彻更资)下凡寻找人种的过程。[345]《三兄弟和洪水淹天》记叙太白神仙帮助好心的老三取得火种,使他有资格与仙女成婚。[346]《继世阿根》讲述有位老人教会老三如何留下天上的仙女,二人成婚后,一起生下八男八女十六个孩子,他们还教这些孩子如何滚磨盘来配对成婚繁衍人类的故事。[347]二人又成了确保人种延续的祖先神。《少数民族分支》提到白胡子老人教人如何支磨秋,与姑娘配对,繁衍人类。[348]《天地津梁断》提到天上的仙女们羡慕人间的生活,就贿赂蜘蛛偷偷抽经纬,到人间与人结成夫妇做人家。[349]傣族神话《布桑嘎与雅桑嘎》讲在洪荒时候,世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男人布桑嘎,一个是女人雅桑嘎;他们都是傣族先民的始祖,但布桑嘎曾经向雅桑嘎求婚两次,遭拒绝;后在天神英叭的干涉下,二人终于结为夫妻。[350]傈僳族神话《米斯和水神》讲水神后来变成美男子,与人成了亲,人成了水神的舅舅,没有水喝就找水神借泉水。[351]
此外,这些神圣人格还特别负有保证妇女怀孕以及新生儿健康顺利成长的职责。彝族神话《水漫山》讲洪水过后,在天神的授意下,一对男女结为夫妻,数载后女的就怀孕生下牛肚一样大的怪物。[352]《天蛋》讲繁衍神如何帮助天上的仙女怀孕生下天蛋给人间的查决使用继续繁衍人类。[353]哈尼族神话《刚背阿利和刚背阿布》讲远古的时候,刚背阿利和刚背阿布兄妹二人听一位神仙的话常到河里洗澡,哥哥在上游,妹妹在下游,各洗各的,谁也不看谁;洗过几次澡之后,妹妹刚背阿布发现自己的肚子竟然渐渐大了起来,过了不久,就生下两个肉葫芦,那肉葫芦就是人种。[354]彝族神话《咒鬼词》是彝族小孩生病时为其叫魂,使之康复时的唱词。[355]《苗族古歌》记载为保证新生儿健康成长要采取的保护措施:儿子的胎盘要埋在房柱脚,女儿的胎盘埋在灶房;要杀鸡(祭祀神灵)庆生,并用鸡肉抹婴儿的嘴唇;孩子出生,舅舅要送一只鸭,舅妈要送一段布,还要提一罐酒来庆贺。[356]
值得注意的是,神话故事、史诗歌谣、民间传说等文本里提到的那些宗教保护神,他们规定的法律权益只严格属于个人的品格,并与一个人出生以来所依附的家庭、族群、村寨、社区等社会团体紧密相关。这是因为人们崇拜自己的保护神,就会遵守“自然而来”的法律传统或法律式箴言。彝族神话《雨神龙踏恣》讲天神尼多命令人间的龙踏恣司职降雨,并订下“寨中无水喝倒一滴,包谷、高梁、荞子地缺水倒二滴,水田秧苗缺水倒三滴,栽插季节倒三滴,水田里倒七滴”的法则;虽然后来发生恶神假传尼多神旨的事情,但龙踏恣仍然严格按照天神的号令行事。[357]《灯笼山上石老虎》中的石老虎自从立下“愿男男女女(都像我们一样)相亲相爱”的爱情箴言后,凡是父母不同意自由恋爱的青年到石老虎面前祈祷,父母就会同意。[358]这种情形令我们想到在伊斯兰教的法律生活中,由先知穆罕默德的预言创立的“书面文字宗教”《古兰经》《逊奈》等,其中也包含着一系列先知的模范行为和格言警句,它们正是穆斯林圣徒必须遵循的神圣法则,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来自各种保护神的“法”确有很多相似处。其实,类似这样的法律状况,其形成的原因跟人类早期生活的社会实况密不可分,因为在那个时期,个人离开了集体的帮助,连生存的权利和资格甚至都不具有。而在社会团体里,每一个个体成员被认为来自同一个祖先,是在同样祖先神的保护下才拥有成为成员资格条件的,才拥有个人的权益。因而,在这样的历史年代,个体成员必须与他所依附的血缘或拟血缘团体紧密相连,必须遵守“社会的法”。
同时,村寨等社会团体也要集体地拥有相同的名字或护身符,才能得到同一位祖先神的保护。彝族神话《石蚌普与四芽菜普》提到新平、峨山各地的彝族“石蚌普”家族皆以石蚌做保护神,“四芽菜普”家族都以四芽菜为保护神。《守寨虎》讲尼苏寨崇虎敬虎,视虎为护寨神,为求平安,立石虎护寨。[359]也可以看到,由于此时人间的整个法律体系几乎都建立在“神谕”的基础之上,在“决疑论证”[360]的司法审判中,“法官”往往把来自宗教保护神的所谓“公平”“合理”的标准同“良心”之实质要求结合起来,如果在诉讼中,“法官”的判决与以上标准不相契合,会被社会舆论指责违背了神的指示,没有依照“神谕”判决。这个时候,由于不具备“合法性”,违反判决的人不用担心将受到什么惩罚。因为如此,那些根据“神谕”确立起来的习惯法准则不会轻易被推翻,尊崇神灵的旨意成为社会的一种“迷信”。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司法判决一定要以神的旨意为依据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执行。(www.zuozong.com)
由此可见,早期的法律多依据“神谕”制定,“神谕”正是所谓人间各种规范和规则“合法性”的来源,其积极性特殊地表现为:人们不但把“神谕”作为法律的客观依据来看待,而且恰恰是正因为这些“神谕”也具有实用性,个人主观的法律权益也要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所以,任何人都以尊重和实现它们的目的为目的,“神谕”就是最高的法,类似于今天一个国家里的根本大法。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家庭法或家族法,甚至村寨法里,相比较而言,那些直接来自祖先神、大神们的神圣规定要比宗教仪式里的准则更有效些,更能得到人们确实地遵守和实行。建立在“神谕”的基础之上,从一定意义上说,由祖先神、大神们制定的“家规”“族规”“村规”以维护集体的利益为目的,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质法”。这里的所谓“实质法”是相对于“形式法”而言的,如果说宗教仪式的准则具有“形式法”特征,那么,种种“家规”“族规”“村规”不但具有逻辑及措辞上较为严格的特点,还具有形式上较严格的规定,它们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正是靠那些高高在上的神灵力量的支撑,所以人们才会更严格地遵守之。这些较为严格的“实质法”,例如有祭祀祖先神时供奉和牺牲的种类和数量、祭祀的时间和地点、牺牲的宰杀与食用禁忌、参加者的资格,甚至欢腾的仪式和舞蹈,等等。彝族史诗歌谣《阿赫西尼摩》就强调彝族的丧葬规则,每一家、每一户都要严格遵守——人死要埋葬,人亡要祭奠;老人死去了,要把丧幡做,还要做咯补,要把牺牲杀,热闹来发丧;舅家有人丧,吊丧要带牛;亲戚亡故了,吊丧带猪羊;家族有人故,吊丧带公鸡;丧者的女儿,吊丧带熟饭,还要带咯补,还要带糯粑。[361]《咒鬼词》里的“叫魂仪式”,规定小孩生病时,父母要在天黑以后,须抱一个石盐臼、带一条裤子,爬上屋顶,裤子须担在左臂上,石盐臼抱在怀中,一边舂盐臼一边吟唱,还要连唱三遍。[362]《送“白虎”和鸡“接气”》讲洪水退后,只有老三一个人活在世上,太白金星就出来教他支一架磨担秋,天黑后,把磨秋转三转(祭磨秋),龙王的七个女儿便会来跟他转本命。又因为鸡是从人的胳肢窝里孵出来的,所以人快落气时,规定要拿一只鸡来“接气”。[363]《哭》中讲述,按彝族老规矩,丧家举行丧礼火化死者时,黑彝、娃子人人都必须得哭出声来。[364]《跳十二属神》是香通(端公)在祭祀活动中的诵词:祭祀时,由挑选出来的众人化装成十二属相动物来跳神,以十二月为序,从正月属虎来跳,依序唱到腊月属牛来跳,跳到哪一种动物便学哪一种动物的动作和叫声,并随端公唱诵有关那种动物的祭词。[365]《浑水湮天》讲述祭祀时要吹唢呐的由来:曾经有一个白胡子神仙授意人们烧竹竿,竹竿炸开,小孩子们学会了说话,人间因此受益。[366]《敲牛》提到撒营盘常土司到四川做祭祀烧纸,按四川土司那边的规矩和要求,参与烧纸的宾客中必须有壮士随行。[367]《忌虫节》讲述因为祭祀是在田地里由女人们举行的,所以规定男人不准到田地里去,只能在家中做家务。[368]
傣族神话故事《贡纳堤娃降临人间》提到八个勐的国王决定去请仙界天宫第五世佛祖贡纳堤娃来教化黎民,贡纳堤娃告诉八位国王,祭请时候要在人间准备好宫室房屋、蔬菜、薯、果、波蒂果等。[369]苗族神话故事《王姓祭祖的传说》讲到现在滇南一带苗族各支系祭祖的日子和方式都不同,就祭品而言,有的须用狗祭、有的要用猪祭。[370]《早世朗与阿麻榜穆》提到苗家宰门槛猪祭献时,需用一头小猪,外加五节树枝,三节直挡、两节横挡穿好挂在门后。[371]哈尼族神话《祭田神》告诉我们西摩落人每逢农历三月属猴日或马日“祭田神”时须一户一人,用花猪、花鸭、公鸡、母鸡等祭品,并焚香、烧纸钱,扣头作揖,将沾有鸡血、鸡毛的蔑牌插在田中央,才能挡住妖魔入侵。[372]《猎神》讲哈尼人去打猎时必须杀一只白公鸡祭献三位猎神,这是烟沙神为人间定下的规矩。[373]《供四马和二马》提到传说禄劝哈尼族马、李二姓是从南京应天府的高石坎柳树湾迁来的,为了纪念四位始祖,每逢春节就要进行祭拜,并须以四匹马献供;入赘他姓的人家,则要以两匹马和马的祖先图像献供。[374]《绿蓬渡的传说》提到阿撮人(傣族的分支)为了感谢哈尼人的恩惠,每到六月年,要按哈尼人的规矩杀一头白牛和一头黑牛,供奉哈尼祖先,还要用哈尼话念诵颂扬哈尼人丰功伟绩的祭词。[375]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吊丧老人、为小孩子“叫魂”、为死者“接气”、举行丧礼、“跳神”、吹唢呐、烧纸等,都具有宗教礼仪的性质,具有我们今天说的“形式法”的特征。也就是说,无论它们表现为祭献的形式,还是表现为禳解的形式,或是表现为模拟的形式以及欢腾的形式等,皆有着来自祖先神、大神们制定的较为严格的程序规定,这些规定也都以实现村寨集体或个体家庭实实在在的利益为目的。(民族学学者指出:哈尼族大型祭典中祭品的功用是“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祭祀目的,祭祀活动中杀白鸡的话,必须把它献给银神享受。银神居住在天上,其名为‘普通阿都’。接受鹅的神灵是‘咳约阿都’,居住于地上;接受麻花母鸡的神灵是‘玛尼阿建’,居住于地上;接受红公鸡的神灵是‘批摸承建’;接受公鸭的神灵是‘萨拉阿沙’,居住于地下;接受黑母鸡的神灵是‘咳通阿都’;接受白鸭的神灵属于银神,其名为‘普博居窝’;接受阉鸡的神灵是约义阿三,属龙王系统,居住于地下;接受鸽子的神灵是‘回扎仰营’,居住于天上;接受狗的神灵是‘萨同民理’,居住于地上;接受猪的神灵叫‘剑玛阿美’,居住于地下;接受山羊的神灵是‘玉通阿都’,它属于玉神,居住于天上;接受雏鸡的神灵是‘煞沃克玛’;接受雏鸭的神灵是‘煞罗阿建’,居住于地上;接受黄牛的神灵是‘威嘴、石匹’,居住于天上;接受蛋的神灵是一个‘没有牙齿用舌舔,没有双脚跪着走’的神;接受饭团的是一个懒得不想挖田,饿了就讨吃的男神;接受棉线的神灵是一个懒得不想拿针线,冷了讨穿的女神。”)[376]
也正由于此,家庭法中祭祖和敬老爱老这些“实质法”规范有着深刻的宗教道德之源:哈尼族神话史诗《扭动舞》[377]《木雀舞》[378],彝族神话史诗《神桩》[379]《灵牌》[380]《拉码争》[381]《丁郎刻木》[382]《祭祖节的来历》[383]《神主头的起因》《神主头的来历》《背老子箐》[384]等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老人神圣,要遵循敬老爱老的道德规范。例如哈尼族的《格朗和的由来》就说勐海县的格朗和以前叫“南互”的时候,庄稼经常颗粒无收,人们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一天,阿散夫妇接待了一位化了装的神仙老爷爷,他留下来的烟盒给南互寨带来了福气,后来人们就把南互改成了格朗和(意即福气大)。[385]正是由于家庭里的老人如此神圣,人们才在相关的家庭法中对日常生活中如何敬老爱老做出了很多详细的规定:彝族史诗歌谣《十劝君》里的“第一劝”教育世人要孝敬父母长辈,例如“乐善好施行阴功,老天永佑积善人。”[386]《渔鼓调》中有“劝孝顺”的具体规范:人不孝,有灾殃,从来孝顺召嘉祥。天感格,福昭彰,也养个孝儿郎。劝大众家庭和让,怪连枝骨肉参商。世间难得同胞养,须久共忌分张……谈不尽,做来香,这些趣味要全尝。[387]《十丑歌》是彝族聂苏支系的生活调,歌中有“世上有十丑,儿不敬父母,此为最丑行”的告诫。[388]《十好歌》中有“无病人长寿,这是第一好;父母都健在,这是第二好”的劝诫。[389]《十德歌》中进一步强调:“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390]因此,在神圣人格及其“神谕”作为法律标准的情况下,实现法律的理想具有不同的途径,在行为人“似乎”具有正常意志力与理解力的特定情境下,哪些行为会被视为道德与理性的,哪些不是,“神谕”显然都是人类早期道德理想的法律模型。
我们还看到,受父权制思维的限制和神圣男性众神的影响,在“家庭法”中,一家之长对子女人身和财产的专制控制权从来没有被彻底取消过,父亲甚至对子女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父母亲还有包办子女婚姻、强迫成年子女与其自由恋爱对象分开的权力。一家之长对子女人身和财产的专制控制权的案例在彝族神话《昆明的来历》中提到,古时候有个公主,由于继母进谗言,就被父亲赶出了皇宫。[391]《守寨虎》讲述一个普姓人家生下个虎头虎脑的儿子,把年青的母亲吓死了,其父就用血写了“生死由命”的字条,即把字条和娃娃一起放在路旁丢弃。[392]《伙嫫姑娘》讲有户人家的阿妈图财为女儿订下了一门婚事,要女儿嫁给一大富人家的瘫子,尽管姑娘不愿意。[393]《姑娘心孤山》讲常土司在三江口为儿子找到一女,托媒婆去说亲,姑娘的父母答应,尽管姑娘死活不肯,爹娘还是强行把她嫁到了常土司家。[394]《偏心的父亲》说在一个农民家,一天,其女儿顶撞了父亲几句,气急败坏的父亲立即把她嫁给上门要饭的叫花子。[395]《杀鸡祭灶的故事》提到有个叫额博的人,想杀死顶撞他的女儿。[396]《普拉未莫》讲有个贪婪的寡妇要女儿嫁给富人家,遭到拒绝后,认为千年铁树不会发芽,祖宗规矩不能更改,就把女儿捆起,决定杀了祭祖。[397]《姑娘坟》讲有个叫“黑良心”的父亲因女儿跑出去对歌跳弦就扎死了她。[398]《彝族节日二月八》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彝族祖先父子俩常被人们请去做阿闭咱底(祭祀)。有一年二月,父子俩走到中午时分,父亲说这里有水有柴,在这里做午饭吃,儿子却说再走一段路。父子俩又翻过一座山,父亲说在这里歇息,儿子说不行。这样折腾几回,父亲气了,认为哪有老子服从儿子的事,就把儿子打死了。[399]《花口索塔》讲到坡龙山巴鲁大寨善良的德洁王子,被父亲视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而处死。[400]
而“法律”也规定父母亲对子女的婚姻具有包办的权利。彝族神话故事《踩轻棚的故事》讲彝山有一位能歌善舞的美丽姑娘和一位勤劳勇敢的小伙子相爱了。可是,姑娘的父亲嫌小伙子是一个放羊的穷孩子,就把姑娘许配给一户有钱人家,虽然这位富人子弟奇丑无比。[401]《花边衣裳的来历》和《花腰带的来历》都讲述类似的故事:很早以前,在今红河县宝华(红河县、元阳县)一带,有位善良美丽的姑娘,爱上了一个勤劳勇敢的伙子,可父母却决定要把姑娘嫁给富人家的儿子。[402]《龙门姑娘》讲石碑山脚下有一个彝族村寨,寨里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叫依娜,与另一寨子的小伙罗宝相爱。但罗宝家境贫寒,依娜父母将女儿关在家中,不准两人见面,后来把她许配给了一李姓财主家。[403]《彩凤吴郎石》讲到锁梅寨里有一对情人,男的称吴郎,女的叫彩凤,他们非常相爱,彩凤爹却逼着她嫁给县太爷的舅子“丧天良”。[404]《怀珠村》讲嶍峨县太平乡有个村子叫喜家珠,村中一位美丽的姑娘叫扎西。但扎西的父母不愿将女儿嫁在穷苦的本村,就把痴情小伙子们撵走,并决定把女儿嫁给县城里一个瘸腿的修补匠。[405]彝族史诗歌谣《逃婚调》甚至控诉这种受“家庭法”约束,真情人不能结成伴侣,只好用逃婚或以殉情方式结束生命的悲惨结局,其中有“事到如今没奈何,再在村里是非多,如今生米成熟饭,苦劝爹妈也枉然。背着爹妈出门坎,眼泪汪汪脚打战”。[406]《媳妇调》讲姑娘被迫成为别人家媳妇后的痛苦生活,其中有“爹妈嫁我不商量,活人丢在死人坑,还说小儿命不长。嫁女讨媳由爹娘,不问女儿愿不愿,只管银钱进钱箱”。[407]《哭嫁歌》唱出了姑娘对包办婚姻的苦情,唱道:“阿妈和阿爹,专听媒人这只狗。女儿才十五,就用肉体去换酒。”[408]“不愿进水的小鸡,被人赶进了水里,我不喜欢的人家,爹妈逼着要我去”。[409]《爹爹和妈妈》则哭诉了在父权、夫权社会里姑娘对包办婚姻的愤懑和不满。[41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