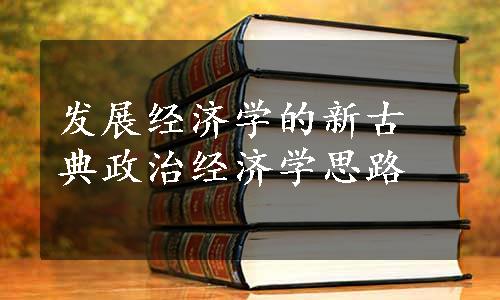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兴起的这股新思潮之所以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因为这股思潮中的经济学家一方面充分吸取和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另一方面又充分重视对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背景的分析。发展经济学这一新阶段在思路上的特点是:结合制度分析观念和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探索经济发展源泉,考察经济发展历程,揭示经济发展规律,把制度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实质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也是发展经济学通过运用新制度经济理论工具而获得发展的新阶段。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经济学的进展已不是新古典复兴,而更像古典经济学复兴,因为古典经济学比新古典经济学不但更加注重经济自由和价格机制,强调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而且更加关注制度和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和效率的影响。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Lewis,1988;Hagen,1980;Sen,1988),而新古典经济学则不太看重发展本身,更多注意的是既定资源的配置。换句话说,古典经济学重视的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新古典经济学注重的是如何合理分配一个既定的蛋糕。再说,古典经济学对制度、交易成本、产权等对经济发展意义的关注要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强烈,科斯、威廉姆森、诺思、布坎南、贝克尔、克鲁格曼等人试图构建的新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其实不过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形式化。
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的最重要特点是,结合制度分析观念和新古典方法论,探索经济发展源泉。这里所谓的制度分析,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而这种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新古典方法论基础上的,因此,经济发展研究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的实质,就是用制度分析探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储蓄率高、教育发达、技术创新活跃等都是发展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现象,它们是经济发展理论所要解释的事实,而不是发展的原因。比方说,经济发展要快,必须有高储蓄,才会有资本的高积累,但问题是造成高积累或低积累的原因又是什么?再如技术创新,它确是经济高增长所必需,然而,技术创新的动力又在哪里?这些都要从制度上寻根求源。每一项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激励。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社会所需要的活动,为此,就要求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从该活动中得到的收益和私人从该活动中得到的收益相符合。从事经济活动有收益,也有代价或者说成本。但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可能不一致,这就是所谓外部性。一项好的制度设计,就是要能诱致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以及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一致,这样才能推动经济发展。拿技术创新来说,如果一项创新成果的收益不能为创新者所获,尽管它对社会经济增长贡献极大,又有谁肯付出那么多代价来搞这种创新?显然,这不是一个技术创新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
制度究竟怎样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进程?为什么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差不多的两个国家或地区,一个发展迅速,一个发展缓慢?为什么同样一个国家,一个历史时期发展很快,另一个历史时期发展很慢?这不是用技术、人口、资本、自然环境等本身所能回答的,只有从制度分析中才能找到答案。制度可以通过确定的规则,提高信息透明度,使每个人都能对其他人的行为反应作出准确预见;制度可以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来塑造发展的动力,促使人们的个别努力转化为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活动;制度可以通过正规的法令规章和非正规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社会习俗等来影响市场运作,决定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制度可以通过对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提供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和风险创业。总之,有效的组织机制和制度安排会造成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经济发展的实践,使经济发展的愿望成为现实。这样,在新制度主义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不管是哪个国家,影响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制度选择。
后发优势论是关于经济上后来发展的国家在发展中存在一种由后发国地位带来的特殊利益的理论,应当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发优势论的创立者是俄裔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Gerschenkron,1904—1978)。他在1962年出版的《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落后》一书中,通过对19世纪德、意、俄等当时欧洲较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验分析,提出相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的显著不同,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会影响发展进程,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后来增长速度会越快,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这是一种来自落后本身的优势,也可称“后发性优势”“落后优势”“落后的有利性”。后发优势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对落后会造成紧张状态,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并激发制度创新;二是可以在吸收先进国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三是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在一个较高起点上推进工业化。
在格申克龙之后,有不少经济学家对后发优势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例如,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列维(M.Levy)从现代化角度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作了具体化,总结归纳出后发式现代化的一些利弊,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M.Abramovitz,1912—2000)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追赶假说”,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会呈反向关系,即越落后其增长会越快——当然,这是指“潜在”或“可能”,而要把这种“潜在”转化为“现实”,还要有一系列限制条件。在他之后,美国学者鲍莫尔(W.J.Baumol)又对这一“追赶假说”作了发展和补充。
如果说上述学者的思想标志着后发优势创立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高速增长,一些学者通过对拉美、东亚经济发展政策与路径的比较,对东亚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促进了后发优势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学者有美国经济史学家罗索夫斯基(H.Rosovsky,1927—)、日本学者南亮进和大川一司等。他们认为,拉美国家从初始条件(如自然资源、人口压力、人均收入和资本、人力资源等)看,都比东亚各国强,而东亚各国能取得快速经济增长而拉美则没有,关键在于东亚较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通过后来的增长努力和正确的路径选择,超越了初始条件限制。美国学者希尔曼(J.Hellman)和韩国学者金泳镐也对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作了深入研究。美国学者伯利兹和克鲁格曼(E.Brezis and P.Krugman)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基础上还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蛙跳”(Leap-frogging)模型,认为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技术创新能力前提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产业领域实施技术超越,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与先进国竞争,而先发国家由于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及技术转换的高成本,可能反而被锁定于原技术水平上。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新形势下,后发优势论进一步得到拓展。对此,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M.Grossman and E.Helpman)、巴罗和萨拉-依-马丁(R.J.Barro and Sala-i-Martin)以及范艾肯(R.Van Elkan)等都有所分析论述。总的说来,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会使后发优势表现更加突出,影响更加深远:一是资本会更快从丰裕国家流向短缺国家(那里报酬率较高);二是技术扩散加速,技术溢出效应日益突出;三是信息技术发达,不但使科技扩散更快、要素跨地区流动更活跃,也使后进国对先进国各方面经验教训的借鉴吸收更加全面、及时。(www.zuozong.com)
与后发优势论相反,一些学者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学者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发达国家当年工业化初期情况大不相同。今天,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面对经济强大的发达国家,后者对前者的不利影响无处不在,使当今发展中国家在以下多个方面处于劣势。
资本积累的后发劣势,主要指发展中国家资本匮乏、收入低下。这种低收入状况使储蓄能力低下,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而资本形成不足又导致低生产率,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形成纳克斯所讲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纳尔逊(R.Nelson,1930—)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也持类似观点。
技术进步的后发劣势,指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难以有效消化,也无力形成自主研究与开发能力,从而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日益扩大。
产业发展的后发劣势,指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强化了后发国家的低水平产业结构。
结构转换的后发劣势,指后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明显的二元性,传统化和现代化的二元结构存在于经济、政治等各领域,贯穿和渗透于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整个经济体系。
制度创新的后发劣势,指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必需的制度基础很薄弱,有严重缺陷,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除了上述劣势,后发国家还有国际贸易的后发劣势和国际关系的后发劣势。这主要反映在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上。中心—外围论由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提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国际经济关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中心;另一部分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这种国际经济关系的外围,从而形成中心—外围格局。中心国家利用旧的国际分工,从事附加值高的工业品生产,外围国家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在双方贸易中,由于工业品需求弹性大,初级产品需求弹性小,于是工业品价格不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下降,从而使外围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依附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多索(F.Cardoso)、桑托斯(M.Santos)、弗兰克(A.Frank)、伊曼纽尔(A.Emanuel)和阿明(S.Amin)等。他们大多是拉美经济学家,故又称“拉美学派”。他们同样是中心—外围论者,并认为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对中心国存在依附关系,在贸易、资本、技术等方面依附于发达国家,受发达国家控制,使这些外围国家得不到应有发展。中心与外围间的贸易是不平等交换,外围国家生产的大量剩余被转移到中心国家,使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越来越大。
可见,上述这些后发劣势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后发劣势论着眼于从发展中国家内部寻找不发达的原因,从资本、技术、产业、结构和制度的不利影响中探索后发劣势;另一类就是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着眼于从发展中国家外部寻找不发达的因素,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等不利影响中探求后发劣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