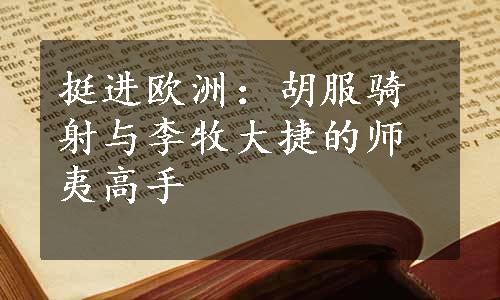
匈奴的突然出现,打得秦、赵、燕三国措手不及,纷纷修葺长城,作消极抵抗状。赵武灵王不干了,我们的祖先曾经就是“夷人”,干吗要受这些蛮夷欺负?恢复当年的“夷风”有点困难,还是直接向这些落后于自己几百年的匈奴人直接学习来得快。于是乎,丛台的美酒窖边出现了胡服骑士的矫健身影,塞外边关出现了弓箭在手的赵国勇士。
匈奴古称鬼方、猃狁,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政权发生过冲突。《周易·既济》中记载,商王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西周以后,以上两个名字逐渐消失,开始出现犬戎等少数民族。犬戎是否就是匈奴,尚有争议。西周穆王曾经征讨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国语·周语上》),白鹿、白狼,显然是犬戎战败后进献的礼品。狼是草原民族最尊敬的动物之一,很多民族的起源传说都与狼有关,联系到匈奴人喜爱白色,至少可以说犬戎与匈奴有密切的联系。
周穆王打败犬戎之后,为便于控制,把一部分犬戎迁徙到临近周朝中心地带的太原居住,即现在的宁夏固原、甘肃平凉一带。不料此举给后世埋下了祸根。周幽王为了讨冷美人褒姒的欢喜,烽火戏诸侯,惹怒天下。申侯趁机联合犬戎进攻西周国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幽王被杀,褒姒也被掳走。即位的周平王无奈,只好东迁至洛邑(今洛阳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的时候,匈奴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汉文史籍当中。匈奴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漠南黄河河套地区(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黄河沿岸的地区)和阴山(狼山、大青山等)一带。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无论对于畜牧还是狩猎,都十分有利,游牧经济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邻近的燕国、赵国、秦国的心腹大患。三国先后在边界修筑了长城,以阻止匈奴铁骑长驱南下。为了在七国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燕、赵等国还曾拉拢匈奴一起进攻敌国。匈奴人继承了犬戎的“外交”政策,有意在中原各国之间纵横捭阖,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不过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匈奴人在后勤补给匮乏时仍然不时发兵南下侵扰,掠夺人口、财物。大青山——河套一线是匈奴部众生活的中心区域,南面正对着秦国、赵国,秦国国力强盛,赵国相对软弱,因此赵国受到的侵扰最为严重。不过匈奴的幸福时光并不长远,赵国的武灵王进行了大胆的“胡服骑射”改革,“师夷长技以制夷”,很快瓦解了匈奴骑兵的优势,实现了长城两侧的第一次攻防转换。
胡服骑射为什么会在赵国发生?我们还得从那位“桐叶封弟”的周成王说起。
相传周成王姬诵有一天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宫中玩耍。姬诵随手捡起了一片落在地上的梧桐叶,把它剪成玉圭形,送给了叔虞,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个玉圭封给你吧。”史官们听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辅政的周公。周公见到姬诵,问道:“你要分封叔虞吗?”姬诵说:“怎么会呢?那是我跟弟弟说着玩的。”周公却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啊!”
姬诵想了想,决定把叔虞封为唐国的国君,史称唐叔虞。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便改国号为“晋国”。为了祭奠唐叔虞,姬燮在晋水源头、悬瓮山下修建了一座祠堂来祀奉他,这就是著名的“晋祠”。
“桐叶封弟”只是美丽的传说,周王封叔虞为唐国的国君,其实有明显的战略目的。晋国西靠吕梁山,东临太行山,南面是中条山,整个国家被紧锁在三座大山之中。更要命的是,他的四邻都是“戎狄之民”。当时黄河中游流域基本上是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些少数民族不时南下西进进攻周王朝,是周朝的大患。在他们当中设一个封国,等于在少数民族活动的核心地带钉进一个楔子。对异己的唐(晋)国,戎狄之民当然要除之而后快。这样,一个小小的唐国就转移了戎狄大量的注意力,减轻了宗周的压力。
晋国的统治者还确实不含糊,他们没有依靠大山之险单纯地龟缩其中,而是主动向外出击,开疆拓土,当时称“启土”。“启土”的对象当然是戎狄领地。在晋国的臣民中,有一支特殊的部众,即周王封给他们的“怀姓九宗”。这“怀姓九宗”其实就是周王俘虏的鬼方奴隶。换言之,即一帮匈奴人。外有戎狄,内有“九宗”,晋国统治者的处境可谓糟糕透顶。不过压力越大,动力越大,晋国统治者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一套独特的统治术,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所谓“启以夏政”,即按照华夏族政权的统治模式来控制整个国家和新占领的戎狄领地;“疆以戎索”则是要在不干扰“夏政”的基础上,尽可能适应戎狄的旧有制度。这样,晋国统治者不仅扩大了领土,而且传播了周代文化。不过,晋国因此也染上了很多的胡气。比如著名的晋文公,每次上朝时都是穿一身羊皮衣服,俨然一副胡人酋长的气派!
不仅如此,晋国还是“和亲”政策的始作俑者。向戎狄要土地,未必每次都能得手。公元前569年,晋悼公为恢复晋文公时的霸业,在魏庄子的建议下,决定“和戎”,缓解背后的压力,以便腾出手来,专心对付南方的楚国。其和戎办法大致如下:(1)互通有无,用中原的美酒佳肴女乐换取对方的马匹、毛皮;(2)定期盟会,解决近期出现的矛盾;(3)互相通婚,建立统治者之间的亲戚关系;等等。对比一下可以发现,汉朝的“和亲”政策和晋国的“和戎”政策区别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汉朝只向外嫁宗室女,从来没有从匈奴娶个妻子回来。
《孔丛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www.zuozong.com)
魏国使者子顺出使赵国,赵王向他请教拉拢北狄的办法。子顺回答:“给它好处,和它互市,北狄自己就会过来。”赵王很奇怪:“寡人的目的是削弱它,如果与它互市,把我国的好东西卖给他们,不是让它更强了吗?”子顺大笑,随即作了一番精辟的阐述:
“和北狄互市,只是用我们没用的东西换取他们的宝贝而已。衣服、丝织品、美酒佳肴都是他们喜欢的。牛马、毛皮、弓箭,等等,他们有的是,可以很随便地给我们。牛马、弓箭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战略物资,平时求之不得;服装布匹、美酒佳肴我们有的是。宽袍大袖的服装并不适合马上穿着,美酒佳肴吃完就没了,这些对他们其实都没什么大用。相反,他们会日渐沉迷于我们的锦衣玉食,逐渐丧失自己的优势,到时候可以一举歼之,何止是削弱他们呀!”
看了子顺的分析,不禁让人钦佩中行说的远见。晋国人发明的“和戎”,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融合和汉民族的形成。中行说坚决反对匈奴贵族穿着汉朝赠送的衣物、食用汉朝的美酒佳肴,维护匈奴自己的民族特点,尽管阻碍了汉匈两大民族的交流,但维护了匈奴的军力。
公元前369年,三家分晋,赵国分得的领地最多,但也因此和匈奴成了邻居。大青山以南的沃野是匈奴人的乐土,同时也是南下的跳板。为了控制住这块要地,赵国和匈奴进行过多次较量,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不过祖先的胡气给了赵国人以智慧和变革的勇气。
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这位有着胡、汉双重血统的圣王英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赵国军队的武器其实比匈奴精良,但多为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加上官兵都身穿长袍,甲胄笨重,反应不灵活。武灵王抓住要害,在大臣肥义等人的支持下,首先改革服装,要求所有人都要穿着匈奴人那样的短衣、长裤。
改革服装在古代不是一件小事。从周初开始,周王朝的政权设计者们就为后世设计了一套严格的礼乐制度。服饰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服装即可辨别某人的身份地位。改穿胡服,大家都一个样,直接破坏了原有的等级秩序,肯定会有很大阻力。
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首先反对。为了说服公子成,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做工作,用大量的事例说明胡服的好处,终于使公子成同意改革胡服,并表示愿意带头穿上胡服。公子成的工作做通之后,仍有一些王族公子和大臣极力反对。他们指责武灵王说:“衣服习俗,古之礼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武灵王批驳他们说:“古今不同俗,有什么古法?帝王都不是承袭的,有什么礼可循?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制定礼仪。礼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衣服、器械只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代那一套。”
在服装改革成功之后,武灵王下令改革军队,向匈奴人学习骑射技术。经过反复训练,终于训练出了一支堪与匈奴铁骑媲美的精锐骑兵。
改革成功后,赵国开始反击了。反击首先从邻近的匈奴别部林胡、楼烦开始。林胡、楼烦实力弱小,而且犯了轻敌的毛病,很快被击垮。赵国的土地因此向北延伸了千余里。赵国原来建了内、外两道长城,林胡、楼烦长期在内长城附近活动。击败两部后,赵国先后在这里设立了云中、雁门、代三郡,与匈奴本部开始隔着外长城相望。
对于赵国的反击,匈奴不甘示弱,开始频繁地往来于长城之下,使赵国边境的农业、畜牧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由于南方和秦国的战事不断,赵国无力北顾,只好采取守势。大将李牧奉命守边。李牧分析形势后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他一面广建烽火台,派出大批间谍,及时掌握匈奴骑兵的动向;一面严加防备,以逸待劳,尽可能不战而屈敌之兵。后来李牧内调,新的将领改弦更张,主动出击,结果屡遭败绩。赵王无奈,只好再派李牧镇边。
李牧认为匈奴此时正是骄兵,骄兵必败,有机可乘。于是集中战车1300乘,骑兵13000人,步兵5万人,弓箭手10万人,采用了匈奴人惯用的诱敌深入之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始,李牧命令“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引诱匈奴进攻,然后又诈败后退。匈奴屡战屡胜,不假思索地紧追,结果陷入赵军的重重包围,损失十余万骑。李牧趁机大规模北进,破东胡,降林胡,逼得单于四处奔走,十余年不敢再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