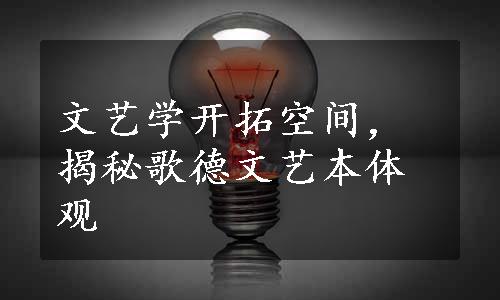
李贵森
歌德,1749年8月25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市,1832年3月22日卒于魏玛,享年83岁。他的一生跨越两个世纪,而且正值欧洲大动荡和变革的时代。耳濡目染的一切,促使他不断接受了哲学思想和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与冲击,其思想几经变化发展,并反映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来。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歌德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美好理想,追求完善的艺术与精神。他除了在文学艺术领域任意畅游,随笔挥洒,成就斐然,更在哲学、美学、历史学、造型艺术及自然科学等领域执著努力,永不放弃,成绩卓著。
人们谈起歌德,常挂在嘴边的除了说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之外,还誉他为思想家、自然科学家。的确,我们纵观他的整体思想和全部活动,“身兼数职”的他应该是绝非徒得虚名的,因为不论是从思想家的角度,还是从自然科学家的角度,亦或是从文学家的角度,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并成为支配其所有活动中心内容的是其文艺本体观。而深入研习歌德的结果,我们也不难发现他的一切活动,包括其所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实际都是在为其文艺本体观寻找立论和阐释的依据。正因为此,我们也就更易理解歌德那建立在哲学思想与科学理念基础之上的文艺观之所以能被大家认同的根本原因了,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文艺观的本质所在了。
说歌德是位思想家,其实他是一生都没有写过什么哲学专著或思想文化著作的,他那些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方面的丰富言论和主张都不过是散见于他那大量而又零散的、片断的感想、谈话和通信里,最集中的还是体现在了他与艾克曼的谈话录及其杰出的文学作品当中。也就是说,歌德虽为有理论思想、有创作实践的一代文化大家,可他本人对其文艺观却没有作一个系统明确的概念性论述,因而我们今天在试图把握其文艺观之时,也只能从他那一百四十几卷之多的全集中去发现,从他那与创作密切相关的实际生活与实践中去寻找。探求的结果告知我们:歌德的理论思想、哲学认识、文学创作、自然科学研究以及一切活动,无一例外地都是由他那文艺观这个本体而生发出来的,然后又反作用于它们,从而使它们得以光大。
那么,歌德的文艺观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先打开他的文学巨著《浮士德》读一读,在全书的开篇之处,他就安排了“舞台的序剧”这样一个部分,其中所展现的是三个既对立又相互补充的角色——“剧团经理”、“剧作家”、“丑角演员”发表对诗的各自见解。他们的观点与主张依其角色不同而各持一方。“剧团经理”作为剧团的代表,他主张剧本应给观众以满足,既要吸引观众,又要追求整体效果,追求票房经济价值;“剧作家”则提倡一种艺术至上的观点,追求作品的永恒价值;“丑角演员”着重讲的则是趣味性和作品的意义,他主张作品既要讲求含义深刻,又要能吸引人。显而易见,三个角色都是从各自的角度谈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自然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如果将这些观点和主张综合起来便会发现歌德实际上以非常巧妙的方式为我们梳理出了一个十分清晰而又完整的文艺思想观念,那就是:文艺创作既要有素材的积累与提炼,又要有哲理的思考和理性的认知;既要有生活的真实与摹仿,又要有文艺的独特和艺术的趣味。歌德在《浮士德》中借“剧团经理”“剧作家”“丑角演员”之间的辩论,实际表现的是自己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而已。《浮士德》一部作品如此,其它作品如此,随着其外延的扩展,当然关涉到整个文学艺术亦当如此。
青年时代的歌德主要接受的是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和泛神论思想的影响。斯宾诺莎的功绩在于,他在同宗教和经院哲学的斗争中,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唯物论原则,在批判法国古典主义思想家笛卡尔的二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元论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这对18世纪欧洲各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对歌德走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道路当然也有极大的启发作用。不过,歌德在哲学思想上受康德的二元论的影响更大,难以摆脱上帝理性化观念,进而决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不彻底的无神论者。一方面他主张“三教合一”,认为神是最后的立法者,一方面他又否定神的“绝对价值”。在《浮士德》中,他借魔鬼靡菲斯特菲勒司之口指出,“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是常青的”,这种对神学认识理性上的超越,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升华,进而成就了其世界观中的唯物倾向。歌德认为宇宙就是现实的世界,一切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什么现实世界、未来世界之分,于是乎他迈入了无神论者的讲坛。然而,尽管他是否认来世,肯定现实的,却又由于其人神共存的宇宙观而成为无神论讲坛上无法走到底的演讲者。尽管这讲演里充满着唯物的、辩证的因素,却又自觉不自觉地与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因素相交织。这显然是歌德那进步与保守、崇高与平庸的对立统一思想在其世界观中显现的结果。
歌德在美学观点和文艺思想上可以说受狄德罗和莱辛的影响最深。狄德罗这位18世纪法国坚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感觉和思想是外界的物体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他肯定认识来源于感觉,但认识不能停止在感觉上面,而必须在经验的事实上加以思考,然后,经实验加以证明。作为18世纪欧洲最杰出的美学理论家,狄德罗提出了真善美统一的理论和艺术摹仿自然的启蒙主义美学纲领。他认为艺术的美在于它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因而强调艺术创作“要真实”,“要自然”。其艺术理论和主张贯穿着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精神,它对歌德文艺观的形成,尤其是在艺术表现的客观性、真实性上影响作用非同一般。而莱辛这位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和文艺理论的创始人,他在美学理论、戏剧理论、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方面对德国文化新时代的开拓性意义,更对歌德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启示与推动。莱辛提出的必须克服脱离现实的倾向,发挥各种艺术形式的特性,真实而生动地反映现实的美学思想,为启蒙主义者建立资产阶级新文艺扫清了道路。他在《汉堡剧评》中的理论建树,更为德国把戏剧创作从法国古典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民族戏剧的建立和发展树立了典范。可以说莱辛的理论观点和认识,以及其实践活动等对包括歌德在内的一代青年在思想解放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为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开辟了道路。青年时代的歌德就曾积极参加到这场运动当中去,并表现出了对当时丑恶现实的憎恨、鄙视和强烈的叛逆精神。从当时的作家群来看,最有成就的就是歌德。
歌德能够成为一个思想家的根本原因,关键还是他的思想观念与认识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同时代人,而上升到了对整个宇宙、整个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的层面。歌德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把自然看成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并遵循着一定规律运动的整体,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是任谁也不能动摇的,就如他在《我研究植物学的经过》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当中,它们的运行由客观世界中存在的那普遍规律所支配。显然,这实际上正是歌德经过多年的探索所找到的结论。即: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必然的,世界上不仅不存在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而且整个世界完全是处于永恒的可变性当中的。歌德所说的“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生活和整个大自然界,他是把自己置身在现实中去认识和表现这个“自然”的。如果我们记住了他在《自然颂》里的箴言:“自然界就是一切,我信赖自然,就让自然来支配我吧!”那么,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他的哲学会以文艺观作为其本体了。可以说歌德以其文艺观为本体派生出了哲学认识及各种论点,而这些思想又反作用于其文艺观,融汇并显现于其创作实践中,成就了其事业。如前所言,既然歌德认为客观世界存在发展的前提是其实在性,于是反映到实践中,他是既强调思辩,更注重行动;既然歌德认识到了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于是这唯物辩证的观念便突出地体现在了《浮士德》的主人公那善与恶的关系中。也就是说,从方法论的角度,歌德是不赞成单纯地思辩,而主张思辩与行动的结合,它们就像人的呼与吸一样是不能分开的。由此衍生出的文艺本体观化之于其文学作品,便显现出人物形象犹如浮士德所体现着的基本精神,既有那将《圣经》中的“太初有道”译成“太初有为”的变通,又有那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更有那努力向上、自强不息地对真理的追求。(www.zuozong.com)
在歌德看来,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是由对立而趋于统一,因而主张艺术提取事物本质时会反映至高无上的自然,而艺术也就完全被自然主宰,成为自然的奴仆。在《意大利游记》中他说:“古代崇高的艺术品,同时也是自然的最崇高的作品。在必然和上帝面前,人们一切随心所欲的、任意的、幻想的东西全部崩溃了。”从歌德的文艺思想来看,其早期属于解放个性、抒发情感的浪漫主义,之后因受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和精神领袖赫尔德尔的影响,转而表现狂飙突进精神。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深入,对包括德国思想家在内的作家们震动极大,他们眼见人道主义理想和启蒙思想家们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没能实现,于是开始逃避现实,逃避革命,转到精神领域去探索实现其理想的途径,表现在理念上就体现为:主张用古典艺术的美来教育人、改造人,培养完美和谐的人,即通过个性教育、美的教育来实现理想。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的古典主义不同于法国的古典主义,思想上它继承的是人文主义的传统,变相否定了封建制。它宣扬感情和理性、理想与现实、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和谐统一,要求实现的是人道主义的理想。作为德国古典派文学代表的歌德,当他感到德国浪漫主义脱离现实,表现出消极、反动倾向时,他便主张增强古典主义理论的现实主义因素。而实际上歌德所理解的古典主义,已经很接近后来19世纪中期才出现的那个现实主义了。歌德曾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性质进行比照,指出浪漫主义从属于主观,是病态的、软弱的;古典主义从属于客观,是健康的、强壮的。不过在创作实践中,歌德并没有将表达必然的古典主义与表达幻想的浪漫主义对立起来,就像他在《浮士德》中那样,用浪漫主义写虚,现实主义写实,用虚实纵横、交相辉映来表现主题,突出作品的思想意义。而这恰恰是歌德理想的文艺观的真实写照。
歌德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形成于18世纪80年代旅居意大利的那段岁月。1786—1788年,在意大利的歌德接触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并接受到了本国同时代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观点和艺术思想的影响。温克尔曼是最早研究古希腊造型艺术的,他的《古代希腊艺术》及其关于“庄严静穆”美的论说促使歌德的文艺思想开始由浪漫主义和狂飙突进转向古典主义,其诗剧《伊菲格尼亚在陶里斯》所表现出来的典型古典风格就是这一转变实现的标志。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原因就在于此时的歌德认为只有古代艺术体现了纯朴、宁静、和谐的美,才是真正的艺术,这促使他必然要从“狂飙式”的热情和狂想中转回头去,重新审视,进而崇拜和追求那纯朴、和谐的人道主义理想。于是歌德开始把古代艺术的美看作理想,幻想用古希腊艺术作为典范,用道德感化来教育人,将其培养成完美的人,用古代艺术陶冶人,形成和谐发展的人道主义理想。正是意大利丰富的古代文化和优美大自然的抚慰,他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适时适地而形成了。这时不仅他自己的活动从理论的探索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更多地向创作实践回归,其颂扬道德感化和完善,抒写田园风情,追求宁静、和谐的风格渐渐形成,而且他还在一定意义上帮助席勒克服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影响,当然最恰如其分的还是体现了其以自然为中心的文艺本体现。歌德的美学观点和文艺思想尽管并没有全然克服泛神论,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唯物与唯心就像他那进步与保守、伟大与平庸的对立统一的一生一样,但是比起启蒙时期的思想家、美学家,比起同时代的作家们,他却具有更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他的美学及文艺思想在同时代人中,的确达到并代表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这一切也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所从事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事业。
歌德去钻研自然科学,与其生活的那个时代密切相关。18世纪的欧洲自然科学处于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化学、植物学、电学等发展迅速,尤其是蒸汽机的发明,氢汽球的试制成功,这一切都标志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而随着自然科学成果的涌现,在思想领域也引起了各种大变化。就当时德国的思想界来看,最具代表性的有康德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系统建立起的主观唯心论体系以及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系统阐述的唯心辩证法,创立起的欧洲思想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论体系。这些哲学思想显然与歌德的哲学与美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或可名状的关系。而莱辛、赫尔德尔的美学及文艺思想则扩大了歌德的视野,英法启蒙主义者的进步思想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及业绩则深深地鼓舞了他。这一方面表明,身处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高度发达时代的歌德,不可能摆脱时代氛围的熏染与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歌德对自然科学关注的兴趣程度与其所从事的研究不是偶然的,而是取决于他的追求与时代背景的。纵览歌德的一生活动,他一直注重自然科学领域发展及成果的本身,似乎指明了他是要找寻一种改变那时代观念的思想意识,并为自己的创作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于是由此取得的他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自然也就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上有了特殊的意义与价值,更在文艺思想的确立与创作实践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歌德早年就曾对医学、炼丹术等发生过兴趣,并亲自练丹制药。后来他相继对骨络学、植物学、地质学、生物学、颜色学等发生兴趣,并付诸精力去研究,产生了包括生物、物理、地质、天文、气象等方面,诸如,《植物的变态》、《颜色学》、《比较解剖学引论》等论文或著作,而且获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无机化学方面,尤以原始模式说和变态观念为最。歌德认为任何动物或植物都有统一的模式,偏离原始模式的现象都是通过变态形成的,这就是他的原始模式说。这一学说应该说是歌德关于生物进化理论研究的基础。而变态学说的价值在于歌德通过研究认为在动物或植物体内存在一种质液,因为它们的不同才有了各种动植物发展的不同。就植物来说,歌德认为都是由一种发展而来的,叶子的各种变态成为花,花的各种变态有了种子,种子促成了各种植物的繁衍生长。至于动物则认为是由脊椎的某一部分演变而来的。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歌德的这种原始模式学说和变态的观念贯穿着一种发展的观点和进化论的意识。纵观歌德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成果和贡献,可以说他并不亚于当时的一些科学家。对于他本人来讲,这一方面增强了他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和文艺观中的现实主义,为他超越同时代人提供了条件,更为他成为思想家、文学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展示了他对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生、自然与创作的看法和态度,并为其文艺观的建构和显现搭建了坚固的平台。
歌德的文艺观为本体的思想理念和自然科学研究,以及一切活动,都是以实实在在的客观世界的存在为前提的,因之这个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客观世界便与其文艺观和创作有了一种相辅相承的关系。这也就是说,歌德的哲学观念、美学思想、文艺理论、自然科学认识等是相融在一起,互相依托,互为作用的。其哲学观点渗透在自然科学的认知和美学、文艺思想当中;其文艺思想中则体现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等哲学因素。尤其是歌德这样一位没有哲学、美学及文艺学专著,却又有大量间接论述这些思想的杰出的文学家;这位有大量自然科学研究实践和成果、并扬名于世的唯物论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文艺观在理念上的建立与创作中的展现是他的最终追求。就此也证明了歌德的一切思想的构建与其所有的活动都是以文艺观为本体的。在这种相互依托的关系中,哲学思想与理念显然是歌德文艺观的立足点,客观世界与现实生活则是其文艺观产生的基础,而自然科学研究与成果更奠定了其文艺精神与态度。由此也就确定了歌德的艺术实践是建立在对客观世界与社会自然认知的条件下,是以其文艺观为指导的创作原则。歌德在以散文形式发表的重要文章《自然颂》中,就明确提出了自然的规律性,而在《<希腊神庙的门楼>的发刊词》中,他更对艺术家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应该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在这里,歌德对艺术家、艺术作品与自然之间的论述中,将对自然的研究放到了与摹仿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为我们辨明其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与文艺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佐证。当然这一切均又最终取决于他思想中那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至此我们完全可以明确地讲,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之基础,文艺作品来自于现实生活,这个基本准则显然是源于歌德的哲学及文艺思想,源于他植根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践活动本身。不过歌德的超越他人处在于他并没有仅仅将目光停留于此,而是又进一步去强调了艺术创作受现实生活的制约,艺术要忠于自然,但要高于自然的观点,“艺术家努力创造的并不是一件自然作品,而是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歌德语)。因此,艺术家应该像歌德所说的那样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正是这种双重的身份,使艺术家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歌德的这种唯物、辩证的认识显然阐明了文艺既要从现实出发,服从自然,又要超越自然的本质属性。
歌德从自身的艺术实践中找到了符合其哲学理念和文艺思想的基本规律,那就是从现实出发,掌握和描述个别特殊的事物,在特别中表现一般,通过创造一个显示出特征的有生命的整体,来反映世界。这个整体虽然来自于现实,但又不是现实中所能找到的,它是艺术家自我心智的显现,是艺术家借助于艺术手段,融入自由大胆的思想与精神打造出来的成果。这样的艺术才可称之为惟一真正的艺术。在歌德的理念中,客观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具体的、各具特征的、可感知的事物,那么艺术家想要认识生活、反映自然,就必须从认识和把握具体的、感性的、个别的东西入手,而掌握和描述了那个别、特殊的事物,也就找到了艺术的真正表现。而通过特殊显示出了一般,也就体现出了艺术的本质,达到了美的境界。在这个反映时代的、显示出特征的、生气灌注的活的整体创作过程中,面向现实世界,投身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不断实践、研究、创作和探索、追求,才是诞生真正艺术美的途径,也是决定艺术能忠于自然、又能高于自然的关键。歌德的《浮士德》无疑是以可感知的形式为我们诠释了他的美学理念和文艺思想。
我们返观歌德的以文艺为本体的思想观念及一切理论认知,就会发现它们是从哲学的层面上,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点上,从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升华出来的。当它们定型成熟之后,又作用于其思想观念与认识的更新,作用于其文学创作的推陈出新,以及对一切活动的指导。然后再借助其所有实践活动的成果,实现其理想中的研究与发掘、创作与追求、表现与完善的回归。歌德借《浮士德》主人公之言便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份执著与追求。“我要跳身进时代的奔波,我要跳身进事变的车轮!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面对着歌德的此等豪迈,我们已是无话可再说。
(作者李贵森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